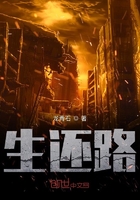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傍晚,远在北方的三湖市,早已银装素裹,比之赤霞山脉,不知更寒冷了多少。
今天是个罕见的晴天,尽管太阳低悬于地平线之上,仍发挥着余热、余光,将大地也映成耀眼的橘红色。
原本的柳荫湖营地中,早遍布了无数厚实的帐篷,大多以树木与枝叶层层加固填充,哪怕已是二九天气,其中仍自温暖,众幸存者早就适应了严酷的环境,又辅以棉服和皮装等冬衣,更不觉寒冷,还有心思闲聊。
在一顶最不起眼儿的帐篷中,正拥挤着三人,头脸都蒙在泛着油光的肮脏棉被中,几乎看不见头脸,只从说话声中才能得知,这是三名年纪不大的男女少年。
在三人中间,正摆放着三枚赤红色的长柄蘑菇,看样子新鲜饱满,大约是新近采摘的。
其中一个略带外地口音的男声道:“预言家说只要吃了这蘑菇,就能像方蕈那样强大,你们信吗?”
另一个女声道:“谁知到呢?不过我听说只要吃了,就能成为他的心腹,再也不用挤在这里受罪了。”
最后一个女声道:“别想那么多了,管他是真是假,先吃了再说呗,他们总不会毒死我们的!”
帐篷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三人互视了一眼,都不约而同的取了蘑菇,一齐塞进口中。
帐篷之外,不远处就是早已冰封的柳荫湖,一道道黑漆漆的巨大阴影隐现于冰面之下,湖面上正有一队怀抱木段的幸存者快步穿行,为首一人身材并不健硕,却光着上身,肩上扛着一把黑漆漆的大斧,在胸口处还镶嵌着一枚火红色的水晶状物,其中隐有流光转动,直似有生命一般。
其后众幸存者显然畏惧于为首那人,虽然担负着极重的负担,却不敢有丝毫懈怠,都尽力跟着那人飞快的脚步。
正行走间,天空中忽然大放光明,将傍晚的天空映得如正午十分,甚至于有些刺目。
众幸存者能活到现在,什么大场面没见过?只这些许异象,尚不足以引发什么慌乱,只那有闲心的才左顾右盼,寻找这怪象的源头,随意往西面一撇,透过已被砍伐得极为稀疏的树木,望见天边即将落山的太阳时,才咧开大嘴,既不发声,也不走路,直到后面人不小心撞上后背,才大呼道:“快看!太阳变形了!”
众幸存者循声望去,也全都如那人般目瞪口呆,下巴连同木段掉了一地。
只见挂在天边的橘红色太阳,似被某种力量牵扯,整个拉成椭圆形,一端更有一道蛇般火线,蜿蜒着窜射出去,以此为牵引,整个太阳都不断被拉伸,从椭圆,渐变为柳叶状,之后只余一条亮线,最终消失无踪,只在天边留下一个暗红色的光圈。
至此,世界也彻底黑了下来,无云的天空中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星斗,只是不见了月亮的踪影。
越过柳荫湖,原湖滨家园小区营地,建筑物早被大地震摧毁,光秃秃的广场中,正矗立着一座高约二十米的庞大建筑,貌似一朵放大无数倍的蘑菇,黑漆漆泛着金属光泽,其上无数大小孔洞错落排列,小的不及针孔,大的直径近一米,像极了天然生成,全不似人工制造。
蘑菇下方,仍一身大花袍服的预言家正与聂荪对立,眼见光线转暗,轻笑道:“朱骁成事了,我们也开始吧。”
聂荪尚不确定,问道:“方蕈还没回来,我们是不是再等等?”
预言家摆手道:“时间紧迫,等不了了。”
聂荪不再发言,冲预言家重重点了点头,转身钻进那巨大蘑菇下方的一个孔洞中,眨眼就不见了踪影,又过了不久,便有无数火红光点,从那大蘑菇遍布的孔洞中放射出来,逐渐转亮,几乎将半个柳荫湖都照亮,更散发着恐怖的高温,早已冰冻三尺的柳荫湖边缘处,也有了融化的迹象。
琼博士早在聂荪钻进蘑菇时,就已退到极远处,同时俯下身去,将双手虚按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
与此同时,以柳荫湖为中心,数公里外的地面上,徒然升起道道白色细丝,就在冰天雪地中纠缠生长,很快就组成一道一米来高、毛茸茸的白色围墙,并仍自快速向上生长,若是按照这一速度发展下去,相信要不了多久,整个柳荫湖都会被笼于其中。
远在洪涛的老家剑城市,教师组合汪壁书、付新月二人,带领着小学生高涵,加上天眼闵志豪这一组合,同样目睹了太阳消亡的一幕。
震惊之余,几人都将目光投向年纪最小的高涵,求助之意几乎溢于言表,高涵也不怯场,只皱着眉头,将下巴高高撅起,刻意压低了声音:“反正已经世界末日了,再发生什么也不会更糟,我们只要做好最坏打算就行了。”
付新月忙问道:“那我们该怎么做?”
高涵道:“从现在开始,咱们除了多寻找食物以外,还要尽量搜刮衣服、棉被,书本和木柴也绝不能少了,我怀疑接下来,我们要度过一个难熬的冬季了。”
赤霞山军方驻地,地面上的人员全都撤入地下空间,只剩下空荡荡的帐篷,在无边的黑暗中显得异常萧条。
偌大的核心帐篷内,李芝芳点起一盏酒精灯,接着昏暗的光线,与远道而来的方蕈隔着办公桌对坐。
李芝芳面带笑容,轻声道:“按照约定,我已经尽最大力量帮助朱骁成事,接下来也该预言家兑现成诺,将潜伏在军方的势力全部撤出了。”
方蕈道:“预言家向来说一不二,这点你我心知肚明,你根本无需担心,另外预言家曾告诉过我,朱骁会把他的日记放在你这里,这话没错吧?”
李芝芳揉了揉额角,答道:“确实如此,可惜你来晚了一步,之前我特意确定了一次,日记已经不见了。”
方蕈尚不甘心,追问道:“朱骁回来取的?”
李芝芳苦笑道:“我不确定,从那天他们离开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