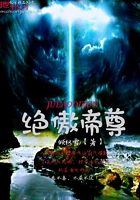方圆百里内,一个生物都没有存留。当然,这句话成立的条件是除了站在冰晶层上的内瑟斯,以及他抬头仰望,在其视野内冰封于高高的晶碑中,那只庞然狰狞的巨兽。
他迟迟不肯迈出那一步,而这一步他等了千年,终于在他面前掀开帷幕时,他反倒心生退却。他无非在想自己会释放出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来,是那一个文质彬彬,勇敢睿智的飞升者,还是一头沾满了鲜血的野兽。
他不得不确定是后者。哪怕有一层晶体阻隔,他也能够清晰的感知到雷克顿身上的气息。那来自地狱之门后的炙热火焰,还有侵蚀灵魂的暴戾之气,他仿佛见到这几千年来雷克顿在地狱之门后经受的折磨,以及随之日益剧增的力量。
“如果你是以前的你,那个未曾走进帝皇陵墓的你,肯定也会同意我的做法吧。”内瑟斯抬头喃喃说,“这或许是我的臆想,但我只能够这么做,我的弟弟。我为了肩上的责任,而放弃了你,后悔了数千年,看来我不得不继续懊悔下去。”
他惨然,无不寂寥地说:“有所得,便有所失,既然我获得了飞升者的力量,就必定有所失去,而你也一样,你失去了你的理智。看来这是我不得不背负到永恒的诅咒。”
他怒吼一声,身形涨大拔高,上升到如同晶碑中的巨兽一样的高度。他的长柄巨斧像是顶天之柱般立于地表,灰烬般的能量在地面上刻下灰色纹路,在这一圈区域内所有生者的活力都要被剥夺。长柄巨斧被内瑟斯肃然举起,斧刃点在雷克顿的额头位置,隔着一层厚厚的蓝色晶体,肉眼可见的赤红能量传递到巨斧上,沿着长柄,侵入了内瑟斯的身躯中。
神明的躯体内旧伤未愈,被奥术能量灼烧过的伤口刺痛难忍,而这股赤红色的灼热能量沿着内瑟斯的血脉传递到身体各处,将沿途的肌肉血管一并灼痛。内瑟斯痛苦地吼叫,头上一对长长的尖角蓦然伸出,浑身的皮肤渐渐化为暗红,喷涌出刺眼的焰光。火红色的能量蔓延到了地上的死亡之力,如同在水中化开的墨色,将地上的纹路区域化成了一滩暗红色的旋云。
被侵蚀的还有内瑟斯的金黄铠甲,它们被覆盖上了一层黑色,如同在地狱中打造的漆黑铁器。胸前一根长长的铁链,连接着左右双肩的护肩,随着四散的热浪发出难听的声音。
在茫茫然的平原中心,幽蓝区域的晶体高碑前,高大的人形巍然昂立,三只头颅朝天嘶吼。
“我似乎错过了什么东西。”劫如是说。他坐在枯井上,翘着二郎腿,当然有人见到他装束奇特上来盘问。不过三言两语过去,劫就轻易把那些人打发掉了,毕竟穿得怪异的人不止他一个。
在村庄里,唯一一条笔直的大路上,整齐站着一队奇特的队伍。他们穿着类似,身穿最东边风格的甲胄,身上披着一条宽大的血红色长巾,并且在腰间缠起。最引人瞩目的是他们的头上,全都整齐戴着狰狞的面具,那种东方恶鬼风格的面具。
这一堆人大概十多个,训练有素的队列着,所有人都笔直看向前方,没有哪一个人有额外的动作,以及不应该存在的目光。
劫躲在村庄角落,窥视这一队人已经很久了。就像这一队人如同木头雕像般站立许久,劫也牢牢盯紧着他们,既然劫是坐着的,那就更没理由比他们先一步坚持不住。
“那一队人,大概已经站了多久了?”劫问。他提问的对象坐在他背后,毕竟枯井归所有人公有,劫也没有独享它的权利,因此劫背后惬意地坐着另一个人,一个枯瘦如柴的中年男人。
“不知道,谁知道呢?”男人说:“自从那个鸟人在恕瑞玛翻天搅地以后,恕瑞玛的怪人就多了起来,前几天我还见过一个带着翅膀的怪人呢,一脸谁都欠他钱的模样,我只看了他一样就觉得晦气。”
“哦?”劫忍住笑。
男人接着说:“不过嘛,我记得从早上开始他们就一直站在那里了,他们的头领去找村长,不知道为什么至今未归,所以这一堆木头就从早上等到了吃饭的时间。”很应景的,男人肚子里想起了一阵怪响,仿佛在提醒着男人需要进食。
劫低声自语:“也难怪,恕瑞玛闹出了这么多大事,那些自称要维护均衡的人,总要来这里露露脸,免得被别人背后私议他们只说不做。”
“你认识那群人吗?”男人问出口后,就连忙澄清道:“抱歉,我不是想试探你,这是人的好奇心,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剂品,当然,你不愿说就别说。”
“认识倒是认识,而且还有仇怨未解呢。”
男人听了这句话,心里疑惑,回头悄悄瞥了眼,结果他大吃一惊。他背后的枯井没人坐着,而且他环视一周,也找不到任何人影,仿佛刚才在他背后坐下,并且闲聊了许久的那个人,只是他臆想的幻影。
“抽烟抽多了?”男人自言自语。
劫从村庄的另一处阴影,那棵枯树可有可无的树荫下,慢慢走了出来。这个位置比刚才的枯井离那条大路更近了一些,那些装束奇特的陌生人也更清晰的呈现在劫的眼中。打量了那群人许久,劫终于确信了自己的判断,同时身形后退,融入到枯树和土墙之间的那段阴影中。他仿佛从未出现过一样。
村长家,是村子里最大的一座石头房屋,如同混入鸡群中的丹顶鹤。村长俨然擅长谈笑风生,哪怕对坐的那人看不见其表情,村长也被自己刚才所说的笑话逗得哈哈大笑,几乎快要把屋顶的尘埃全都震落下来。
同样带着狰狞恶鬼的面具,以及身缠着血红色的长巾,对座的那人开口,声音低沉:“你是说前不久,有个带翅膀的怪人经过了村子?”
“怪人很多,不过带翅膀的就只有一个。”村长说:“想当初他想从我们村子悄悄溜过,但别人看见他带着这么臃肿的斗篷,于是大伙们狠狠地围住他,把他的斗篷掀开了。”
沉默片刻,戴面具的人问:“难道他没有发怒?或者他身上应该有武器,他没有试图用武器反抗?”
村长把腿抬到凳子上,挠着痒痒的小腿:“当然没有,那个人自己把斗篷拉开以后,见到那人长这样,大伙们害怕得一散而开,之后就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到底是你们把他的斗篷拉开,还是他自己把斗篷弄开?”
“当然是他自己拉开的。”村长笑道:“我刚才就是大嘴巴,大伙哪有这么大胆量,每次经过村庄的各种奇怪的人,我们巴不得让他们早点离开呢,哪会特地多挑几桩事。”
从面具下传来低低的笑声,随后那人说:“这么说来,你们根本就没有围住那个人,更没有挑衅他了?”
村长有些尴尬,也笑不起来了,说:“那个人问路而已,结果没多少人搭理他,所以他拉开斗篷,那就更没有人愿意面对他了。“
“好,看来你知道的大概也就只有这些了,我们会快些离开村庄的。”戴面具的人站起来。村长暗自高兴,但表面上他挤出几句皱巴巴的挽留话语,将戴面具的人送到门外。他没注意到,而且戴面具的那人也没注意到,一滩阴影自墙角滑落,仿佛融入了湖泊中的水滴。
那人回到队伍前,那个队列整齐的队伍没有人出声询问,十余双眼睛齐齐注目着他。这人显然是这支队伍的领队,背上交叉负着两把长刀,站姿挺拔如同枪杆。
“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