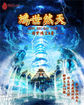“好。”我答应你,但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时间有精力去照顾成姨,我还要做好多事,不能只是耗在这儿,但我真的答应你了。我答应过你太多的事情,在我还太年轻的时候,我说过没有你我会孤独死去,我说过我会照顾你一辈子,可是我真的可以吗。
怀疑自己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我开始怀疑我是否有能力爱你的时候,我只想静静地躲开你,想一想我该干什么。我唯一确定的事情是我要考研,我要考上导演系的研究生,这样也许我可以离那个圈子近一点,离理想近一点,再近一点。
过去没有理由,我就爱上你了。
你吻我的时候嘴唇都是冰凉的。我想我是爱你的,你站在屋檐下对我说你怕死的那天,我发觉我是那么爱你,我也一样害怕失去你。我对你说的所有话都是真心的,是我在当时的激情和冲动之下说的真心话。
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我把那些暂时飞舞在空中的秋千当作永恒的翅膀,我以为我可以带着你一起飞,飞到你幻想的那个无忧乡。
你现在还会问我后悔娶你吗,我嘴上硬着说不会,其实心里在发颤。小雨,也许你该找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男人,一个已经有自己的事业的男人照顾你,而不是我。我注定不是一个安定的男人,我的梦想会让我日夜不得安宁,我可以吃苦,但你不行,你不行我知道。
我距离你最遥远的时候就是我最爱你的时候,那时候我拿着摄影机每天跟拍你,那是我对你充满憧憬的时刻,你像另一个世界的公主一样出现在我的镜头里,我忘不了那些时刻。所以你怎么能跟我一起吃苦。
你总说这是座冷漠的城市,属于另一些人,我知道,我们都知道,要在这座冷漠的城市站住脚不能依靠眼泪。可我们还年轻,我们需要奋斗!我不在乎为了照顾你我没有好好准备考试的事情,我不怕我自己耽误了自己一整年。但我相信我还年轻,我还有机会。
有时候我甚至想握着你的肩膀告诉你:“季雨!我连毕业电影都没有完成,我连学位证都没有拿到。如果你爱我,你就应该鼓励我,而不是像现在担忧这个担忧那个,为了我你要学会坚强起来。”
然后你就会说:“何铮!成姨对我来说不是别人,她病了,我们把她丢在那儿,我对不起爸爸,你明白吗?”
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小雨,我跟你是一样的,我们都只在乎自己的事情。你在乎成姨,我在乎理想,我们都是一个德行,谁也改变不了我们。
白晓
季雨转给我闻佳的来信,我坐在一片狼藉的宿舍里念给自己听,然后放进行李箱的最内层。这次走出国门,再回来的时候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回属于我们的小青春、小情绪。
再见了419宿舍。也许只有坐在这儿,才能轻易回忆起我们这群人刚认识的日子。
那时候季雨总是对我说:“做很多事都是需要冲动的,结婚也是。你知道吗,当年我妈妈就是这样,为了爱我爸爸,为了跟我爸结婚,她甚至不怕死,跑到乡下生了我……”
我说:“哎,你妈真勇敢,能为别人牺牲自己,也许我们都是不适合恋爱的人,我们都太自我。”
她却对我说:“不,我不是。我会为爱情做很多事,得到快乐,也得到伤害。我喜欢那种一辈子就一次的爱情,谈一次恋爱就结婚,我不愿意在爱情游戏里打滚太久。”
那是9月末,我们刚入学不久。初秋的大运河畔,是我们非常眷恋的地方,离北辰大学非常近。天色黯淡时,我们常常牵着手坐在运河的围栏下,看着窄窄的河面反射着两岸建筑物璀璨的灯光,流水潺潺,附近的房子非常矮小。那时八通线尚未通车,东郊的这一带安静得像个夜游园。
我喜欢和季雨坐在运河的河堤上,光着小腿吹着阵阵凉风。她的话远没有我多,但我们总是畅谈甚欢,我说我总是不太相信现实,她说她和太多人说话时感觉不自在。
女人经一夜畅谈就能成为知己,这么说来,我与她对于彼此来说,已然是互相了解透彻的人。事到如今我仍能记起她的眼睛,那是干净而清澈的眸子,我从未见过眼神如此纯真的女子,那是她爸爸的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为她筑就的纯真。
她曾说类似运河那样的宁静是我们彼此的归属。但那些宁静总有被打破的时候,而且划破这宁静的人也是我们。
我们这群人总是闹在一起,这是我们的规矩。
只要男生二十二岁过生日的那天,我们必定会大肆庆祝,一群人在运河畔野餐,看着天色渐渐黑起来,在蛋糕上点起蜡烛,然后起着哄说:“嘿,哥们儿满婚龄了啊!赶紧跟老婆去领个证吧。”
被开玩笑的男生往往就会特别豪爽地说一句:“成啊,明儿大家一起喝喜酒去。”
大家就会说:“好啊好啊,就这么定了啊,去领证!”然后闹成一团,觥筹交错、烟雾缭绕之间看着一对小男女甜甜蜜蜜的样子。
谁都知道这话不能当真。大家凑在一起,尽情说着自己华丽忧伤的小理想、为国为民的小忧伤,几乎没有人说自己的理想是结婚、嫁人、讨老婆。
所以我才深刻地觉得“哥们儿满婚龄了啊!赶紧跟老婆去领个证吧”那句话真是好笑,甚至还带着些讽刺的意味,谁会这么早结婚啊。
想到这儿的时候我瞄了一眼我的签证,我就要离开这座透着恋爱的心酸味的城市了。要出国的这件事不是很匆忙的决定,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何铮的二十二岁生日。何铮是走在哪儿都引人注目的男生,个子很高,很有才气,从小到大他周围都围绕着不同的女孩。
他的二十二岁生日来了好多人,在大运河畔我们围坐在一起,在那个热闹的夜晚,大家同样起哄着说:“何大帅哥满婚龄了,是不是要结婚啊?”
这是让我害怕的一句话。我在昏暗的烛光中看见何铮穿过人群走向季雨,当时他们已经在一起了。在大家的注视下,何铮缓缓地张开双臂把季雨搂入怀中,然后他说:“好啊,我们明天真的去领证。”
那句话像含苞待放的花朵一样吐露着浓烈的芬芳,我隐约地觉得这个世界疯了。
后来他们真的结婚了,其实他们都很单纯。
电话里季雨的声音还是很低沉,我告诉她我要出国了,听得出来她很替我开心,她就是个那么单纯的女孩子,永远不会怨恨别人的好事。
也许我要努力爱上另一个人了。
我常常想,遇到天牧会是一件好事吗?他叫我小白,自从我们在ICQ上初识以后他就一直这么叫我。我叫他天马行空,与他畅谈的时间总是过得非常快,半年仿佛一瞬间就这么过去了,我对季雨说起我和他之间的谈话,我告诉季雨他是一个吸引我的男人。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掠过一丝的颤抖,我害怕季雨发现其实我只是为了掩饰我对何铮的那份感情。
也许这是最初我选择自己沉溺于这段看起来虚无的感情的原因,如果我不能主动忘掉何铮,那就让另一段感情去冲淡我的感伤吧。
令我意外的是,天牧比我想象中要优秀多了,我最喜欢听他说俄罗斯的森林,他说那里的路都是修在森林中间的,开着车在路上跑,偶尔能看到梅花鹿从路中间穿过;在高寒地区,狐狸母子多在路旁的草丛里睁着眼睛看着你;有时会看见被车撞上的动物,他就会赶紧下车通知森林医院……
我想,也许爱上另一个人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只是从前我不愿意,我一直不愿意放弃何铮罢了。在初秋的校园里,季雨歪着头用她那一贯的语气说:“白晓,你不是说过你不近男色的吗?”
对,我从小就是那种不太与男生交往的女孩,如果不是因为何铮与我是发小,也许我这辈子都不会和男生熟悉。
我埋头学业,非常用功。小说里的女主角大概也有我的这种特质,不近男色,她们总是能博得冷美人的美誉,招惹来更多的男生虎视眈眈。
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这样默默地,没有任何人注意地过了二十三年。成长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我不是美女,很普通,脸胖,头发自来卷。但我很努力,每日晨读俄语,大学四年只有我坚持了下来,不论刮风下雨。专业英语、高级口译、俄语听说、综合测评,我都是全班第一名,可是这有什么用呢,我还是一样地找不到我的爱情,甚至连工作都找不到。
我发觉我们都错了,我就是太听话了,一直沉醉于好好学习、心无杂念的教诲中,从不抬头寻觅那一个爱我的和我爱的人,我爱何铮,但我从来没有去争取过。
而季雨呢,她都已经结婚了,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和马天牧的相识非常意外,但我感激这样一个在恰当时机到来的男人。
“简直了!”这是天牧最喜欢说的话,我告诉过他这三个字构不成一个感叹句,不合语法,但他还是自以为是地这么用。我想,如果天牧见到季雨,他一定会说:“漂亮得简直了!”
季雨真的是我们系里最漂亮的女孩,我永远记得开学第一天她走进教室时大家的眼神,那是永远不会属于我的礼遇。
大四最后的这一段时间,是我最痛苦的时候。参加各种各样的面试,看着一个又一个不如我的人获得令人眼馋的工作机会,而我却只有站在后面羡慕的份,就连季雨这样英语六级都没过的人都找到了翻译公司的工作。
女孩长得漂亮就是没错,像季雨这样漂亮得叫人嫉妒的人,运气更是不可思议的好。不好看的女孩绝对混不开,这是学外语的金科玉律。
与何铮在一起之后,季雨就已经不在宿舍里住了,虽然我们的感情还是很要好。
在那段颓废的日子里,我认识了马天牧。渐渐地,我觉得爱情不再是伤感的,我开始喜欢听他说他在海上的故事,那几乎成了我每天快乐的源泉。我想他真的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他说他长期处在蔚蓝的颜色中,我想他的心一直是很纯净的,没有杂质。
跟那些长期与熟悉的人相处的人不同,他去过很多国家,习惯了对一个地方由陌生到熟悉的感觉。我喜欢他说话的方式,他说他喜欢在船上临海眺望大陆,看着海港里停泊的轮船和拥挤的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像野兽派画家笔下大块大块的油画色彩。偶尔他还会在临海的公路上小跑,短暂呼吸着异国的空气,然后继续回到大海的怀抱中。
他告诉我他喜欢安徒生的童话。热爱童话的男人是可爱的,所以听他说起他曾经的风流韵事,我感觉不到任何的虚假。他说他在故乡莫斯科的时候,就常常受到不同女孩子的欢迎,有金发碧眼的欧洲美女,也有豪放激情的拉丁辣妹。他第一个女朋友是莫斯科女孩,一个长相上有点类似霍尔金娜的女子,那个女孩常说:“马天牧,我喜欢你黑色的眼睛,里面有神秘的东方色彩。”他的第二段恋情是与一个漂亮的乌克兰女孩,据说女孩的爸爸在乌克兰驻俄大使馆工作,于是他蠢蠢欲动的热情被这个漂亮的女孩点燃,在拥抱、亲吻的激情退去之后,他们和平地分手,直至他在莫斯科大学毕业时,身边的女孩仍然无数。
我真的觉得我爱上他了,这样的男人是非常吸引人的,像何铮一样,爱上他们都是危险的,但我已经无路可退。
我决定去考他妈妈的东亚文学研究生,这是爱情的力量,也是逃避的力量。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季雨的时候,她似乎显得有些疲惫,她美丽的脸上掠过一丝彷徨和沧桑,甚至有些魂不守舍。
“又和何铮闹别扭了?”
“没有,”她倔强地否认,“但是,你爱那个人吗,真的爱吗?”
这句话我非常熟悉,这句话曾经无数次地在我耳鬓厮缠。季雨说这句话的语调像极了闻佳,我记得当时季雨决定冒着被大家惊讶的目光杀得九死一生的危险和何铮结婚时,闻佳就是这样没日没夜忧心忡忡地说:“季雨,你爱他吗,真的爱吗?”
“你别后悔啊,结什么婚啊,昏了头吧你,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爱情?”
“天啊,我才不要去你们的婚礼,你会后悔的。”
于是我像当初季雨回答闻佳那样,睁大了眼睛看着她说:“我爱他,非常爱,我觉得我从未这么爱过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