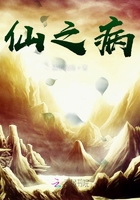我曾经想过,要保护她的梦。我曾经给过她承诺,我的承诺就是我的忏悔,而我的承诺有多深,我的忏悔就有多深。我知道,她现在一定在等我回去,等我回到她身边,然后与她共同生活。那些被标注未来两个字的日子,应该是我和她一起度过的日子,我知道那会很美好。
但是我做不到了,我再也做不到了,我做不到让我的父母独自留在这里生活。我常常想起季雨对我诉说过的所有故事,还有她的爸爸,我很害怕我像她一样只能用怀念去祭奠。
我想问季雨还好吗,能跟我来俄罗斯吗?我知道她一定不会来,成姨怎么办,爸爸和闻佳又该怎么办?她一定不愿意离开他们那么遥远,一定不会愿意。
我突然间觉得,不管我当时怎样深爱过她,我都没有设想过结局,这就是我们最初的爱情,像最初的梦想一样永远都无法实现。我像一个荡秋千的少年,把那些飞在高空中的力量错误地当作了像鸟儿一样的飞翔,那些本身没有那么伟大的力量,让我错误地想象成了自己的力量,我知道我错了。
突然间,我不那么憎恨何铮了,这个我无数次猜疑和鄙视的男人蓦地在我心里变得高大起来。我知道,他跟我一样,我们只是平凡而普通的男人,我们心底都有着敏感而弱小的情绪。我们不是英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打破任何东西。
这就是男人吧,永远都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海跃不在了,我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现在就是我必须承担责任的时刻。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都是海跃的脸,我的弟弟,在我离开家以后,承担了替我赡养父母、维系家庭的责任,我却不知道,我只是那样自私地想要去寻找我自己的感觉,想要满世界地走。我想起以前每次出海时,妈妈都会千叮咛万嘱咐,每次她都会一找到机会就让我换工作,每次……
他们都老了。在医院的病房里,我看着年迈的爸爸心里涌起一阵悲哀,现在他们依赖我,他们离不开我。
好几个晚上,我梦到了季雨……我梦到她一遍一遍地对我诉说她对爸爸的想念,她哭着抱着我说她不愿意离开爸爸……我想起这个春天,我还陪她去墓园探望了她爸爸,她在冰凉的地面上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仍然是泪眼婆娑……没有人可以阻止父母的老去,没人可以阻止他们一天天地衰老,他们需要我……
妈妈常常拉着我的手,一边捏着一边看电视,怎么也不愿意放开……偶尔她会在海跃的房间里,一遍一遍地走,默默念着:“海跃啊,海跃啊……”
好几次,小白都看不下去了,红着眼睛对我说:“你别走了……他们真的离不开你,有什么比中年丧子还痛呢?”
然后我的眼睛就湿了……我什么也想不起来,至少我知道,我不能再离开家了。
昨天晚上,我突然那么不可遏制地想起季雨,想起我们一起去琉璃厂的日子。我想起那本《翡冷翠的一夜》还在北京,我想起我第一次在发布会上看见她的样子……然后我终于忍不住给她打电话,我说:“季雨,到俄罗斯来吧,到我家来吧,我们把家安在这里。”
她在电话的那一头,很冷静地说:“不,我要照顾成姨,她走不了,我能丢下她吗?”
她就这么问了我一句,我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她又问我:“你要结婚了,是吗?”
“对,我要结婚了。”我说,心里特别堵。
电话就这样挂了,挂电话前季雨说:“天牧,相信我,你会幸福的,很幸福。”
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变得如此陌生。也许曾经相爱的两个人,注定会变成陌生人,不是老死在地狱或天堂里互不相见,就是在人世间互不来往……
终于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我决定和小白结婚。
一切都因为这件喜事而变得生机勃勃,爸爸在一夜之间变得有了精神,不久之后就可以下床了。妈妈开始张罗着给我们的新房子添置物品,白晓每天承担着买菜做饭的差事,周围的所有人见到我,都会对我说“恭喜”,而这个华人区的大多数人都是我爸爸的朋友,于是我走在路上,就会不停地接收着祝福。
我始终不敢再想起季雨。我和白晓去拍婚纱照的那个清晨,我在影楼的沙发上等着小白,模糊又疲倦地睡着了,醒过来的那一刻,我恍惚地觉得那个穿着婚纱的美艳新娘就是季雨,而当我靠近她时,却发现那只是梦境,现实中我的新娘是白晓……
当一件事情被所有人默认的时候,我也只能理所当然地接受。
周末的时候,爸爸请在俄罗斯的所有亲朋好友吃饭。我和白晓坐在一起,花园里扎着各种各样粉色的气球,大厅里放着欢快的音乐,爸爸站在那儿,脸色红润,不停对所有人说:“我们家好福气啊……”白晓的父母也来了,看起来都是健康善良的人。我突然间觉得也许人总会有理想,但最终理想与现实都会有差距。这句话适用于一切,特别是爱情。
那一天我喝了许多酒,半夜的时候,大家扶我回房间,我已经完全丧失了意识。白晓抱着我,我们激烈地接吻,我觉得自己好累,不想再去想其他任何事,我曾想过这辈子不会再碰其他女人,但这一次我和白晓上了床……
天快亮的时候,下面传来嘈杂的声音把我吵醒,我醒过来看着身边熟睡的女孩,她甜蜜地躺在我的怀抱里。后悔吗?我问自己,却得不出答案。
我迷迷糊糊地听见外面的声响:“海跃啊!怎么会是你……”是妈妈的声音,“你没有死……天啊……天牧……海跃回来了!”楼下大厅里传来妈妈的声音,紧接着是爸爸的号啕大哭,一片嘈杂的声音,似乎家里所有的人都在哭……是幻觉吗?我爬起来,白晓也醒了,惊恐地看着我的眼睛,眼角带着一滴眼泪。
我穿好衣服奔到楼下,看见衣衫褴褛、瘦骨伶仃的海跃被大家抱着。“哥……”他一把抱住我,“哥……我差点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我逃出来,躲在森林里找不到路,受了伤……我以为自己要死了,没想到还能回来!从今以后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
“对,再也不要分开了……”我的眼泪哗地下来了,爸爸老泪纵横地在沙发上痛哭,妈妈抹着眼泪问我:“白晓呢,快让她下来……”
我抬起头,看见白晓站在二楼的楼梯上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见底的哀怨。
“这是你嫂子……”妈妈对海跃说。
“是吗?哥你结婚了?”
“我……还没登记……”我说,不敢再抬头看白晓的眼睛。
“快去拉嫂子下来……”海跃叫我。我跑上二楼,站在她的面前,她咬着嘴唇对我说:“天牧……我爱你……不比任何人少……”我怔住了,久久地望着她,她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知道她在害怕,她害怕受到伤害,害怕失去我。我走近她,把她搂进怀里:“白晓……我也会的。”
季雨
凌晨三点的时候,我终于完成了积压许多天的工作,赤脚走出书房。成姨在熟睡,我听见她孩子般恣意翻身的声音。我在睡前喝了杯热牛奶,滚烫的奶香熏在眼睛上缓解了麻木。躺在床上,失眠仍旧是难以摆脱的感觉,于是我一个人看着天亮起来。小睡一会儿后,我在清晨刺眼的光线中醒来,拉开窗帘看见春日骄阳。
在料峭的寒风中出门,仍旧是拥挤的地铁,一成不变。
明天天牧就要结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