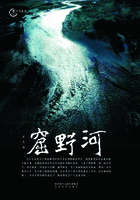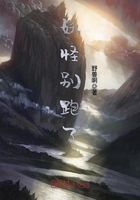“跑步回去告诉任司令员,急行军朝我们这边撤退,避开窄口子直插农坝东口子,那里有人接应你们,我们在这里阻击追兵,掩护你们撤退。快去!
“是!”
龚云东见联络员走了,马上对通讯员说:“告诉三中队长,把部队拉到坝子东口子,掩护巴支队往山里撤退!”
“是!”
龚云东对二中队长说你带着一、二小队去和任重云会合在坝子西边修筑简易工事,阻击巴支队后面的追兵,待巴支队退进口子里,派人带领他们开往城口方向去,找好地方住下后再与纵队联系。你们同时撤进森林,返回我们大队营地,记住只有那条独路,不要走错了。留下三小队,随我在这里阻击开县增援之敌,我也给他来个空城计!”
二中队长:“大队长,你这里力量太弱!”
龚云东:“开县方向增援之敌至今未到,恐怕他们来了我们早已撤出战斗。那边追兵众多,不要轻敌恋战。巴支队一旦进人口子,你们必须迅速撤进林子返回,并打出两发红色信号弹,我见信号撤出战斗,返岩水坝与你们会合!明白吗?”
二中队长:“明白!”
龚云东:“快去!”
“是!”二中队长依依不舍地带着一、二小队跑步离开了。
龚云东把三小队队长叫来耳语了几句,自己带着通讯员上了碉楼。他站在敌人丢下的重机枪前,笑着对警卫员说:“这家伙可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呀!”
三小队队长带着队员们跑步到碉楼后埋伏起来,告诉队员们:“听我的枪声,我打你打!我停你停!”
两个小时后,农坝西口子方向升起两发红色信号弹。
“大队长,巴支队顺利摆脱了敌人追击!”通讯员高兴地对龚云。
“通知三小队撤出!”龚云东下令。
“喂!楼里的兄弟!请你们送点开水出来,我们渴死了!”
通讯员正要下楼,听见喊声忙朝窗夕卜一看,倒退了两步小声说大队长!楼下发现敌军!”
“看见了!”龚云东说,“他后面跟来一队人哩!你赶快换上那套黄皮皮,告诉那个讨水的国军,你去后面井里为他们取水,趁机溜到三小队,命令他们马上和你一起从包谷林里迅速撤出,我掩护你们!”
“你怎么办?我不去!”
“没看见吗?我们已被敌人包围了!不这样大家都走不了!我一个人目标小,好突围。”
通讯员岿然不动。
“快走!”龚云东板着脸说,“你敢违抗命令?”
通讯员被大队长的威严慑服,赶紧换了国军服跑下楼去了。
龚云东看见通讯员骗过敌人,顺禾儿绕到后面去了,正要套绳子从后窗梭下去,那个要水喝的敌军朝碉楼走来了,接着跟来一大队敌军。龚云东立即思了绳子,握着重机枪瞄准先头敌人由前向后一“哒哒哒”一阵猛射!
国军军官听到枪声,才发现碉楼被游击队端了。忙叫:“撤!”
重机枪又一阵猛射,撤退的国军又被打倒无数……
“营长,不救一连了?”国军二连长听到撤退命令急问。
“妈的蠢猪!”营长大骂,“那明明是共军的口袋!你敢去钻?”
碉楼上的枪声停下了,龚云东一脚踢翻了空子3单箱,马上发出一颗红色信号弹,通讯员高兴地喊着:“大家看呀!大队长撤出了!”
三小队队长看了急令:“赶快朝林子里跑,去追大队长!”
龚云东打完信号弹,把重机枪的枪机拆散,扔出后窗。再套上绳子往下梭,快着地时绳子断了,“咚”的一声掉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双手一摸才知自己的右腿摔断了。那个等着“勤务兵”取水的国军,一听到机枪响就马上冲到碉楼脚下,紧靠着墙没敢动。枪声停了又听到响声才过来看,见是一个国军坐在那里,便问龚云东:“你为什么打自己人?”
龚云东二话没说,手起一枪将问话人击毙。
冲到碉楼前的国军二连,听到枪声一齐包抄过来。
龚云东见自己被团团围住,大声对国军喊道:“你们听着我是中国共产党川东游击纵队高梁山支队的大队长龚云东!腿摔断了,不能和你们打了!只好请你们陪我一起去见马克思!”随即拉响手榴弹……当时被炸伤、后来成了高梁山游击队俘虏的一个国军士兵,交代完那个情景后,发了很长时间的呆……
中共七曜山特支委员会,在川鄂旅馆司仲包房召开工作汇报会。
田向东首先汇报说:“乡公所的四十名保安乡丁,有三十一名掌握在我们手中。有九名顽固分子,站在乡队副一边。”
“打起仗来,这三十一名都能调得动吗?”司仲问。
“没问题。”
“各保的自卫队呢?”司仲说,“要通过各支部把他们掌握起来,这些由国民政府供养、为我所用的寄生武装,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我们必须牢牢地掌握住。”
统战委员田向东继续汇报说我通过整编,把那九个编成一个小队,由乡队副兼小队长,平时警卫乡公所,执行特殊任务时由我带队。”
司仲笑着说田乡长,你切不可因此暴露了自己。执行特殊任务时,那三十一个人,交给支队的寄生大队管理吧?当然,不到万不得已时,不会动用他们的。”
组织委员祝方平发言:“芳草坪、脚不干、军田三个支部已经建立起来,共有党员十六人。麻山支部正在筹建中,现有五个党员。”
司仲问:“他们的组成情况?”
祝方平:“这二十一名党员中,五个保长、四个保队副,余下十二人都是下力的挑夫出身,他们都是山区最穷的地方的保长和保队副。这些挑夫都是出去帮人衫过盐、茶、药材,算是见过世面,说得出几句话的本地人。”
军事委员古林森接着汇报一号来后开办的秘密工、农夜校,给我们选拔积极分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场所。厚朴和当归生产基地的夜校里共有五十多名青年农工,全是有进步要求的人。太阳河那边,荣成煤厂的工人夜校里,本厂有四十名青工,其他厂来参加的不少,共七十多青工,政治和文化进步都很快。我想,一个矿工大队、一个农工大队和一个寄生大队的架子就无形中搭好。
古林森松了口气说:“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军事干部,譬如大队长派谁去当?打起仗来他得会指挥!”
“你说派谁去,心中有数吗?”司仲问。
“人选倒是有一个。”古林森说,“云阳有个苏达月,是被逼为匪的青年人。他现在川、鄂边一带劫富济贫,手里有十多个人枪。听说自知为匪没有前途,正苦于无政治出路,只要通过工作可以争取过来为我所用。”
“他?一”田向东、祝方平、童少成同时发出疑问。
“可以争取、改造!”司仲看着大家说,“我听说过他夫妇俩都出身苦大仇深的家庭,成分好。义匪不同于惯匪,是被逼上梁山的。大家学过井冈山的斗争,知道毛主席不是把国民党称之为匪的王佐、袁文财也改造成了红军干部吗,老古,你不是说过他既是神枪手,又会武功吗,你同他联系好,我俩去登门拜访拜访如何?”
“这一”
“你怕他吗?”
“我是说你去太危险。”
“怕他把我吃了?”
“那倒不是。”
司仲:“好,这事我们会后再说。大家的工作很有成效,少成的交通站已按布局恢复和建立完善了,今后的信息、联络有了保证。下一步的首要任务是把支队重建起来,人员的问题、干部的问题、武器的问题,都很重要。具体怎么办?会后我将分别和大家商量。今后,地方党组织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要保障游击队的供给,打到哪里,那里的党组织就要提供供给。当然,不会把全部担子都压在地方身上,大家放心:我们的药材、煤炭生意基本上能保证一二百人的吃穿。”
司仲:“可我占七成红利呀!”
古林森你全都贡献了?”
司仲:“我留着有什么用?”
田向东沉重地说林森,你就不要说了,子章同志离开前对我说过,一号的母亲被国民党杀害,爱妻受连累被捕关进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孩子寄养在夕卜婆家。他的田产全部卖了给高梁山支队买了武器装备。老家只剩下一座没人敢买的宅院了……”
司仲坦然你们都看过纵队的通报,比起牺牲的黎容位、龚云东等烈士,这算得了什么?”
……散会后,古林森连夜去找东方斌,东方的小姨是苏达月的亲婶娘,要他马上去通过他小姨约苏达月见面。第三天古林森就得到了东方斌的回复,告诉了他见面的方式、时间和地存。
古林森应约来到太阳河兴义旅馆,刘巴热情地将他带上三楼的上等客房,说:“古经理稍坐喝茶,你要见的人一会儿就来。”
自上个月司仲买下这个厂后,就把古林森调到太阳河地区兼任区委书记,公开身份是荣成煤厂的经理,领导荣成煤厂及周边各支部的工作。同时,把以炊事员身份掩护的潘大竹,矿工身份的陈易德、麻奔义和会计身份的刘正学等几名党员者卩安插进了煤厂,组成机关支部,刘正学任书记。发展组织,搭建矿工大队的架子。
“咚咚!”有人敲门。
“个?”古林森刚喝了一口茶,放下茶碗说,“请进!”
推门进来一位头包蓝布帕子,长得高大黑痩,炯炯有中的两个大眼睛闪着睿智之光的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
古林森一见,心想:“相貌如此不凡,岂是草莽?”忙起身相迎:“请问,您可是达月先生?”
来人点头:“正是,不敢称先生!”
“谢坐!”苏达月坐下说,“古兄熟读三国,满腹经纶,广交义士,济困扶危,好大一份家产都用在此上了,如今已成贫士!兄弟我仰慕已久,今古林森一号,那是你岳父的血本哪得一见,达月三生有幸!”
“一点良心之使,算不得什么!”古林森递过早已泡好的茶碗说,“倒是你的作为之大,人为之起敬!
“小小绿林,视之为匪!何敬之有?”
“视之为匪者官府也,视之为宝者一”
苏达月急问:“老兄有何指教?”
古林森:“指教不敢,可为之引路也!”
苏达月:“敬请直言!”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古林森走到窗户前小心地朝夕卜扫视。
苏达月微笑着说:“古兄放心,三楼我包了,上、下楼口都有我的兄弟,
你只管说。”
古林森:“我是想劝你把路子扩宽点!”
苏达月:“未必古兄还想搭伙?这是一条死路哇!”
古林森:“我问你一个人,有个叫司仲的你听说过吗?”
苏达月:“人家是共产党,敢与政府抗衡的英雄!草莽岂可与他相比?
不过他也是个被叫做匪的人。”
古林森:“你还知道他多少?”
苏达月:“没有专门研究,只是听社会传言在他家乡闹得天翻地覆,国军围剿也奈他不何,被穷人称为救星!”
古林森:“你,其实也可以成为七曜山人民的救星!”
苏达月:“古兄,莫把我抬到半天云里掉下来摔得粉碎!苏某自知有几两几钱。”
古林森:“苏兄,莫误会!中国北方早就一片红了,只是大山挡住了我们的眼睛。那里,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倒了国民党政府,成立了人民政府。打土豪,分田地。”
苏达月:“真有这种事?分的田地保得住吗?”
古林森:“有人民政府给老百姓撑腰,人民坐天下当然能保住啊!”
苏达月:“还有人民的政府,苛政猛于虎也!古大哥,自古官府都是为富人立的,你那是梦想吧?”
古林森:“我也说不大明白,你如愿听,我请个人来给你一点拨,就自然明白了。”
“是司先生?”
“你先莫问他是哪个,只说见不见嘛?”
“人在?里,你们很熟?”
“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文武双全,武术精湛,神枪百步穿杨!”
“那一你马上带我去拜见如何?”苏达月起身开门要走。
“等等,我这是顺便说起,还得去给他说说,看人家愿不愿见你呀?”“是呀,人家为什么要见我呢?”苏达月坐下喃喃地自问。
“那倒不是那个意思,再熟呢也得先给人家打个招呼吧?”
“那是,那是。”苏达月不好意思地说,“那就请古兄引见!”
接着苏达月告诉了古林森,再见面的几个地存和方式方法。
古林森说苏兄,这是掉脑壳的事,只你知我知!”
苏达月发誓古兄,小弟我决不会当出卖朋友的狗杂种!”
古林森回到吐祥,将此行向司仲作了汇报。
司仲听完说今晚我就去你们家住,闷一会儿就出发去见苏达月,可否?”
“好!我回去准备一下。”
皓月高升,司仲和古林森踏上了去拜访苏达月的山路。
爬上垭口,一个背柴的老头坐在石头上歇气,吧嗒着两寸长的烟叶卷成的栀子花,吐出的烟雾遮住了他的脸。古林森警惕地想从他侧面绕过去,刚到他面前老头把丁字杵故意拿起一横,把路挡住了。
“老人家,为何挡路?”古林森压住火问。
“先生,对不起!”老人家件着丁字杵想撑起来,一使劲反倒又坐下去了。他叹着气说嗨!老了,无用啊!”
司仲快步上前左手抓住干柴往上一提,右手扶住老人帮他撑起来了。等他站定将丁字件撑在柴捆底下后,司仲问:“大爷,家有多远,这么晚了还没回家,走迷了路还是背不动了?”
老人看了司仲一眼,又看了古林森一眼才说就在山下住,我是个孤人,靠打柴糊口,这阵还没吃东西,饿得慌!”
司仲:“那一我帮你背下去?”司仲提起柴捆要背。
老人护住说:“要不得,要不得!”
司仲没关系,我们同路。您这点柴,我不费力。”
老人放下柴捆问:“你们是进山去的?”
古林森答是。”
老人:“前头走了个年轻人,给我一个铜板,叫我在这等你们两个。他叫你们快去,他在前面等你们。”
古林森您晓得他是等我们?”
老人:“看你们的打扮与他说的一模一样!”
司仲问:“你们认得?”
“不认得。”老人说,“他说了,你们是去找他的。你们要是朝山里去了,叫我走人,不是呢,叫我还等。听口音,你们是川省夔府人吧?年轻时我挑盐去过那边的。”
古林森您快回去吧!这个铜板您挣到手了。”
“那一我们两下一请!”老人敏捷地背起柴走了。
“林森,这人的化装术竟瞒过了你我的眼目青!”
“他是个年轻人?”
“没看出来?”
“没有。”
“脸形没有破绽,刚才起身的动作一那么重的一捆柴,从地上轻轻一踮就背上走了,老人能行吗?”
古林森那么,他一定绕到前面去向苏达月报信去了!一号,苏怎么知道我们今夜要去呢?”
司仲这就是他的精明之处了,从你同他谈话后他随时监视着你的行动。天亮前可以赶到吗?”
“从里程上说,应该没问题。”
“没关系,他不是画得有图吗?虽是意想图,但标记还看得清楚,没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人,能做到这样已很不简单了,我们照图前进。”
翻过垭口,平行走了一截,古林森往前一看一大路消失在绿波细浪之中……“哎呀!我古林森长在山上,占有五木,亲见这么大的林海还是生平第一次哩!”
“你没来过?”
“只听说过,这千里林海是七曜山的原始森林,大虫、土匪交替出现,无人敢进。林边通省大路行人也只在中午结伴而过,否贝儿,不是被虎豹吃掉就要被土匪剥皮了!”
“长年如此吗?”
“百年以来,基本如此!”
在林中忽明忽暗的石板大路上走了很久,司仲惊奇地问:“这里边还有这么好的路,为什么废了?”
古林森答:“这恐怕就是老人们说的死亡之路吧!百年前,这才是通省的盐道,就因我先前说的那两个原因,就废了。”
“啊,这路一得益于林子,水土保持良好,路基没有一点毁损,石板仍然平整。真是世道黑暗,大路也无天日!”
“古一大哥一”
司仲林森,有人喊你。”
古林森一惊咦!不是勾魂的吧?”
司仲:“你仔细听,声音尖,随风而来,又随风而去了一”
“对!是苏达月!”古林森这才发现前面有条岔道,忙大声问:“走一哪一条一路?”
“咚”的一声,从背后树上跳下一人,笑着说:“你们来得好快!”
“啊!达月一,”古林森指着司仲说,“这就是你想见的符老板!”司仲欠身说你好!”
“走,到家去慢叙。”苏达月带路拐进小沟,披荆斩棘前行,古、司跟进,上坡下坎走了好大一阵子,古林森揩着汗水说:“达月,你这是带的什么路呀?”
“平时不走这条路,”苏达月说,“今天是避嫌!”
古林森避什么嫌?”
苏达月:“一避夕卜人,二避内部。”
古林森怎么讲?”
苏达月:“山里团伙不少,规矩不引外人进出。我手下人杂,与之避开。”
司仲:“有火并发生吗?”
苏达月:“无事互不相干。”
转过山包,出了沟口进了一块平地,天已大亮。
古林森感叹道:“这里头真是难见天日!”
苏达月:“古兄说的是,我是有家不能回呀!这个鬼地方,不是为了栖身,?个愿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