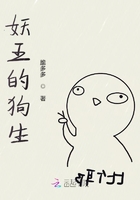次日,董卓他们带着国隐来到了一座庄园。庄园的高大,需要仰着头才能观望到顶处。庄园的景色,无法用几片文章来描述。庄园的阔绰,几乎可以让数百人在一夜之间富裕。而庄园的花费,又亦可以让数百人在一夜之间贫穷。国隐一路打量一路观望,问旁边的李儒:“这样的庄园我在梦里也没见过,拥有它的应该是皇上吧?”
“皇上?”李儒一愣,转而轻笑,回复国隐:“这院子不是皇上,是皇上父亲的。”
“太上皇不是死了吗?”
“是皇上的阿父。”李儒解释道。
忽然众人登上高楼,看见十二三个人在嬉戏打闹,他们光着脚或坐或卧的栖在软席,饮酒作诗。若不是有尖细甜腻的嗓音,样子就像是读书人的聚会。其中一个看见董卓他们来了,于是离开软席坐在木案上:“你就是董卓?”
“哼。”董卓应了一声,听不出喜怒。
“你就是李儒?”那人转而问李儒,李儒微笑施礼,但眼神始终盯着那个人。
“那,”那人又看着国隐:“你就是郭英咯?”
“是国隐。”国隐说道。
“都一样都一样,”那人打个哈哈:“你要问的事我都知道了,我建议你们也不用献天书了。因为我可以告诉你那个偏方在哪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只要你让这个孩子陪我们一天。”
董卓望了望李儒,似乎有什么顾忌。
“不用担心,我可以保证明天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人。”
听到这句,李儒向董卓点头:“这条件我们可以答应,希望中长侍您能信守承诺。”
“自然自然,我张让虽然算不上是个男人,但信守承诺的美德却不是只有男人才可以有的。”
“如此也好。”于是董卓和李儒离开了高楼,留下了国隐。
“过来坐吧。”张让招呼国隐,并向他介绍其他人:
“他是赵忠,我们中最聪明的。”
“他是毕岚,小时候想当个木匠。”“现在也想。”毕岚回应。
“他是夏恽,我们中最娘的。”“貌似是你最娘吧!”夏恽急忙反对。
“他是蹇硕,是皇上的小跟班。”“什么小跟班啊,我是大汉最忠诚的走狗。”蹇硕辩解道。
众人(0-0):“......”
“咳咳,他是程旷,反应很慢,总是慢半拍。”
“他是郭胜,总是自言自语,和程旷很聊得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那里去?”郭胜对着一个柱子说。
“他是侯览,我们中最老实的。”“我哪有慢半拍啊!”程旷说。
“他是段珪,这院子就是他设计的。”
“他是封谞,是我们中最正常的。”“废话,郭胜和我的关系那是没得说,你说是吧,郭胜。”
张让:“现在介绍完了,该说说我们的组合了。”
赵忠:“霍乱天下,”
毕岚:“败坏朝纲。”
夏恽:“翻手为云,”
蹇硕:“覆手为雨。”
程旷:“先有赵高,”
郭胜:“再有蔡伦。”
侯览:“长侍在手,”
段珪:“天下没有。”
封谞:“日出东方,”
张让:“唯我十人!”
“咚”旁边一个仆役急忙敲锣,于是十人摆了个POSS,样子像百兽战队。他们摆着姿势持续了10秒,然后集体倒下。
“有必要这么拼吗?”国隐喃喃说。
“不拼不行啊,大汉朝迟早要完啊。”赵忠说。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啊,我们明明不认识啊。”
“因为你什么都不知道,我从你的眼中,你没有受过儒家教育。”张让说。
“儒家思想是管理下级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好方法。”毕岚。
“不说这些了,我们把你留下来是希望你能把我们合创的一首曲子传播出去。”张让叫人把一份竹简送到国隐面前:“看看吧。”
“看不懂。”
“那我们唱给你听。”张让说,然后国隐听到了一阵难听的合唱,露出了不舒服的表情。张让看见了面色不悦让国隐唱一个,于是国隐唱了首胡歌的逍遥叹。张让他们脸色复杂,却不得不承认比他们编的那首歌好听:“这首曲子是你编的吗?”“不,是胡歌唱的。”“哦,胡歌(胡人的歌)啊。”赵忠说,然后他把手上的竹简烧了。
“看来我不用把这曲子传播出去。”
“是,明天你到王允那当刀笔吏吧。”
“啊?为什么?”
“我们不开心。”
“额......对了,”国隐好像想到了什么;“之前是不是有人说大汉要完啊?”
“对啊,是我说的,不服啊?”赵忠说。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为什么,你想想,皇上发号施令却要受制于人,十长侍也就是我们霍乱朝纲,大将军蠢如猪狗,皇室宗亲各怀鬼胎,朝不闻民声,民不闻朝令,你说说,怎么不玩完啊?”赵忠。
“你们手握大权,可以改变的啊。”
“呵呵,”十长侍相互看看:“我们手握大权?我们只不过是皇上的遮羞布罢了。商朝灭亡人们怪罪苏妲己,秦朝灭亡人们怪罪赵高。其实都是那些皇帝自己没用,才让我们这些奸臣钻了空子。”毕岚说:“而且朝廷的财政出了很大的漏洞,急需很多的钱,于是我们提出了买卖官爵的方法,虽然临时解决了财政问题,但留下的问题却更多了,就像,就像......”毕岚一时之间找不到形容词,开始思考。
“饮鸩止渴?”国隐说。
“饮鸩止渴?”张让说:“对,就是饮鸩止渴。”
“那你们为何还有弄死大将军?”
“他要害我们啊,你想,皇上轻信宦官是皇上的事,杀了我们有什么用?我们死了皇帝就会变得贤明了吗?不会,他还会宠信妃子,甚至会恐惧大将军的权利。所以我们为了活下去,便逼死了窦武。在我们看来,以前的霍光,之前的窦武,以及现在的何进都是同样的人,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现在窦家的不幸是你们造成的啊。”
“不幸?确实是不幸。但天下间哪一个不是不幸的人?窦武死了,天下读书人都在哭,我们死了,天下读书人都在笑。可是天下却还是同样的一个天下,什么都没有改变,不是吗?”
“可是......”
“不必说了,你之前是不是去见了窦辅?就是窦武的那个孙子。”
“是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不要紧,但我想要说一句,窦辅他没疯。”赵忠说。
“没疯?这不可能啊?”国隐说,我亲眼看见的。
张让他们也没有回应国隐,而是回到软席上,继续聊天。
国隐站在原地,他原本就没什么主见,现在也是一样的。
“你要喝一杯吗?”侯览问:“你应该还有很多问题,过来问吧,反正我们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呢。”
于是国隐躺在软席上,享受凉风,说了句“高处不胜寒。”
其他人都闭着眼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我觉得你说的对,”一直没说话的蹇硕说:“我们可以试试,和皇上商量。”
张让:“算了吧,我只想坚持让活得让自己开心,毕竟遮羞布什么时候被人烧掉也不知道。”
“我想到一个更有意思的,”赵忠说:“明天你先不急着去王允那报道,我们先让你去和皇上单独见面,这是给你的一个机会,希望你能把握住。”
之后,国隐和他们聊了很多,不过聊的都是些诗词歌曲,国隐毫不隐瞒,把自己所知道的都没有保留的告诉了他们,并且没有说是自己创作的,把原作者的名字告诉了他们。张让很高兴,说自己可以答应国隐的一个心愿,但被国隐拒绝了。
第二天临走时,张让交给国隐一张白绢,说上面写有治疗哑巴偏方的所在,就看董卓敢不敢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