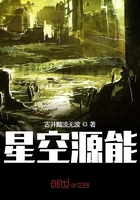杨锦尘看得清清楚楚,急得大叫:“慕容前辈,这酒喝不得的!”
朱政炀大喝:“大胆!怎么人敢这么污蔑联?!”
杨锦尘挺身想跳进窗去,张惟一连忙阻止他,从自己的夜行衣上撕下两块黑布,要杨锦尘蒙在脸上。
杨锦尘一想,朱政炀给慕容青天喝的酒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毒,在和朱政炀撕破脸前,还是先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比较好。就蒙了脸跳进窗内,对慕容青天道:“慕容前辈,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慕容青天总算粗中有细,虽然已经听出杨锦尘的口音,但见他蒙着脸,想到这里毕竟是皇宫大内,杨锦尘和朱弯弯的关系特殊,在朱政炀还没正式交出皇位前,还是替杨锦尘隐瞒身份比较好。朗声笑着说:“老奴活了七十多年,喝下的酒没有一百担,只怕也有九十担,酒有毒没毒,还是能尝得出来的。”
朱政炀沉着脸,一指杨锦尘,喝道:“你是什么人?竟敢夜闯皇宫?”
慕容青天连忙呵呵一笑,打起圆场,说:“他是我的同伙,本来是你的敌人,现在自然和你是一家人了。”
朱政炀脸色稍稍好转,说:“不知爹爹还有多少同伙,不妨请进来一同喝杯酒吧。”
慕容青天说:“喝酒也不急在一时,等你把皇位交出后,我们有的是时间喝酒。儿子啊,你禅让皇位之事,还是尽快办妥吧。”
朱政炀干笑几声,说:“儿子尊命,请二老静候佳音。”
杨锦尘见慕容青天言谈自如,没出现什么异状,看来是自己多心了,没想到朱政炀竟然是个提得起放得下的人,不由地对他另眼相看起来。也跟着说:“这事得想个妥善的方法解决,操之过急,只怕会引起朝局动荡。”
朱政炀连声说:“这位壮士很有见识,联自有安排,请放心。”
慕容青天说:“如此最好。此地不宜久留,我们暂且离开吧。”
杨锦尘陪慕容青天和俞乐儿从侧门离开皇宫,张惟一一直隐藏着没有现身,杨锦尘猜想他肯定另有用意,也就没有向慕容青天和俞乐儿说起。
三人到了宫外,慕容青天问杨锦尘进宫有什么事?杨锦尘说:“我是路上看到前辈和大娘进宫,一时好奇,才跟着进来看看,并没有别的什么事。”
慕容青天和俞乐儿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两人都兴奋无比,也没细想,其实杨锦尘的话漏洞百出。
杨锦尘借口自己还要去寻找蓝可,就和两人道了别,随后返身再次潜回皇宫,见御书房依然是窗门大开,只是房内不见了朱政炀,房外也找不到张惟一的身影。
刚想转身离开,忽然发现情况不对,御书房内的书籍散落一地,连书案也倒了。可是他记得刚才慕容青天和俞乐儿行刺朱政炀时,并没有把书案打翻,难道……昏黄的灯光中,他又发现地上似乎有一滩血痕。
不由地心中一紧,连忙飞身跃入书房,地上确实是一滩新鲜血痕。“难道老张真的杀了朱政炀?若不是,这血又是哪里来的?他们人呢?”如果张惟一真的把朱政炀给杀了,那事情可就闹大了。
杨锦尘越想越着急,忍不住说了句:“老张啊,你怎么可以杀人呢?”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嗤”的一声笑,连忙回头,张惟一眯缝着他的三角眼,正满脸得意地朝着他笑。
“老张,怎么回事?这血是哪里来的?”
“我好好的,这血当然不是我的,你说会是谁的?”
“你……你不会真的杀了朱政炀吧?”
张惟一笑得更加得意,说:“当然没有。我张惟一是尊纪守法的一等良民,怎么能杀人呢?小杨,你看到这滩血的时候,是不是马上联想到我把朱政炀杀了?”
杨锦尘见他一副故作高深的样子,也不知他葫芦里卖得是什么药?说:“是,这血是哪里来的?”
张惟一说:“放心吧,这血不是人血,我把宫中养的一只锦鸡杀了,这是鸡血。我要故布疑阵,明天一大早朱政炀遭人暗杀的消息会传遍整个忘忧谷。当然也会很快传到战鱼的耳中……”
不等张惟一把话说完,杨锦尘就明白了他的计划,问:“朱政炀呢?你把他藏哪里去了?”
张惟一说:“今晚和我一同出来的还有国安寺中的两名和尚,我把朱政炀制住后,交给他们带回国安寺中藏起来。”
杨锦尘说:“不见到朱政炀的脑袋,战鱼是不会放人的。”
张惟一说:“这个简单,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不但要救出蓝可和叽叽,还要除掉战鱼这人杀人狂魔,当然这事成功的关键在于你。”
“我?”杨锦尘有点惊讶,“你就别卖关子了,把你的鬼主意全说出来听听吧。”
张惟一从地上拿起一个包裹,说:“这里是朱政炀的一件龙袍和一顶皇冠,现在天快亮了,我们好好休息一下,让满城官兵去寻找朱政炀,搞得声势越壮大越好,等到了晚上,你穿上龙袍,戴上皇冠,我背了你去见战鱼……”
“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假扮成朱政炀的尸体,对不对?”张惟一才说了一半,杨锦尘就已经心领神会,“战鱼听到朱政炀遭暗杀的消息后,先入为主,以为你给他送去的,一定是朱政炀的死尸,自然就不会对一具死尸有所防备,我就趁其不备,将他击毙。”
张惟一笑着说:“对!关键是你一向心慈手软,这回能狠下心肠,痛下杀手吗?”
杨锦尘想到那几名被战鱼吸干血液的少年,耳边仿佛又响起死者家属撕心裂肺的哭叫声,牙一咬,恨声说:“这王八蛋不是人,杀他是为民除害!”
两人从皇宫出来找了个隐蔽的地方睡上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的午后,上街一打听情况,朱政炀被害的消息,果然已经传得满城风雨。翠萍公主下令全城戒严,全体官兵出动,挨家挨户搜查。
两人耐着性子等到半夜,杨锦尘穿上龙袍,戴上皇冠,张惟一背着他避开巡夜的士兵,溜进战府。
战府内有不少的密室、暗道,天知道战鱼会躲在哪个角落偷看。两人不敢再说话,径直来到碧云轩,还没来得及上楼,就隐隐听到一声低吼,那声音很轻,若不是夜深人静,两人又全神戒备,还真不容易发觉。
杨锦尘在张惟一耳边轻声说:“这间屋子里一定有密室,这是从密室里传来的声音。”
张惟一问:“你知道密室在哪里吗?”
“不知道。你先放我下来,我们找一下,也许阿可和叽叽就藏在密室里。”
谁知张惟一刚放下杨锦尘,突然“嘭”的一声巨响,石屑泥沫飞溅。两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本能的飞身掠到屋外。只听到屋内有人大叫大喊,听上去十分的痛苦。
杨锦尘说:“这是战鱼的声音,他又怎么了?”
两人小心翼翼地靠近门口,借着微弱的天光,依稀见到屋内有条黑影在地上痛苦地翻滚着、吼叫着,听声音是战鱼没错。也不知他在发什么疯病,满地打滚,把屋内的桌椅等家什撞得稀烂,好几次撞上木柱子,震得整幢竹楼都不住晃动。
杨锦尘进屋从地上找了根蜡烛,点着后斜插在木柱子上。
屋子的左侧墙壁上破了个大洞,洞内漆黑一片,这里果然有一处密室。战鱼用双手捂着双眼,躺在地上嚎叫着,痛苦的像被谁咬掉了心肝一样,鼻涕眼泪流得满脸都是。
张惟一小声问:“毒瘾发作?”顿了一下,摇头说,“不像。”
杨锦尘说:“看他的样子像是眼睛受了伤。这就奇了,还会有谁能伤得到战鱼?”
“郎哥,是你吗?郎哥……”墙壁的破洞中跑出一位少年,看身形应该是蓝可没错,只是他模样让杨锦尘有点不敢相认。特别是他的嘴,上下双唇又红又肥,就像嘴上安了两根香肠一样,口中叫着“郎哥”,嘴角的口水直挂到胸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