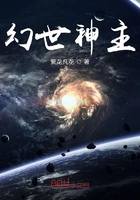但我还是出于主人的礼貌送他们出门——在楼梯上,他们的话从下方传来,令我听了暗暗庆幸:“唉,白来一次……”“我有什么办法?你没见我无论怎么用话激他,他就是一句可作把柄的言语都不说么?”听听——不是被别人用钱雇了,会怀此鬼胎?我的朋友提醒我:“你别什么人都往家门里让啊!”我说:“那叫我怎么办呢?我也不习惯站在自家门里和人说话啊!”
又有一天,医生又在家为我按摩,家中仍有客人,电话响了:“喂,是梁晓声么?”我说:“是。”“真是?”我说:“真是,这是我家电话。”“我们想请您写一篇文章,不太长,刊物已经联系妥了,素材也是现成的,真人真事儿。当然,不要写成报告文学,写成像小说非小说的那一种……”女郎娇滴滴的话语很急促。我打断她问:“你们是谁们?”“我们是一家公司……”“文化公司?”“不是……我替我们老板联系你。你先说你干不干吧?我们老板肯出高价……”“干什么?”“直说吧,我们老板只不过为出口恶气。放心,绝不至于让你惹上什么官司的。一万。一万元怎么样,或者你出个价?”我说:“小姐,滚你妈的蛋!也滚你们老板******蛋!”无绳电话,医生在按摩,客人坐得离我那么近,女郎的声音那么尖——我听到的,医生和客人都听到了。我因居然有这种电话打到家里而无地自容。我们可对它们的存在说些什么好呢?
9.论“苦行文化”之流弊
理念好比粘在树叶上的蝶的蛹——要么生出美丽,要么变出毛虫。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报刊上繁衍着一种荒唐又荒谬的文化意识,我把它叫作“苦行文化”的意识。
其特征是——宣扬文化人及一切文艺家人生苦难的价值,并装出很虔诚很动情的样子,推行对那一种苦难的崇拜与顶礼。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曹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红楼梦》,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有些人可不是这么看问题。他们似乎认为——贫病交加和冻高粱米饭团构成的人生,肯定与世界名著之间有着某种意义重大的、必然的联系。似乎,非此等人生,便断难有经典之作……
仿佛,曹雪芹的命,既祭了文学,那苦难就不但不必同情,简直还神圣得很了。
对于梵高,他们也是这么看的。
还有八大山人……
还有瞎子阿炳……
还有古今中外许许多多命运悲惨凄苦的文化人和文艺家……
仿佛,中国文化和文艺的遗憾,甚至惟一的遗憾仅仅在于——中国再也不产生以自己的命祭文化和艺术,并且虽苦难犹觉荣幸之至犹觉神圣之至的人物了!
这真是一种冷酷得近乎可怕的理念,也无疑是一种病态的逻辑意识。好比这样的情形——风雪之日一名工匠缩在别人的洞里一边咳血一边创作,足旁行乞的破碗且是空的,而他们看见了却眉飞色舞地赞曰:“好动人哟!好伟大哟!伟大的艺术从来都是这么产生的!”要是有谁生了恻隐之心欲开门纳之,暖以衣袍,待以茶饭,我想象,他们可能还会赶紧地大加阻止,斥曰:“嘟!这是干什么?尔等打算破坏真艺术的产生么?!”
如果谁周围有这样的人士,那么请观察他们吧!于是将会发现,其实他们的言论和他们自己的人生哲学是根本相反的——他们不但绝不肯为了什么文化和文艺去蹈任何的小苦难,而且,连一丁点儿小委屈小丧失都是不肯承受的。
但他们却总是企图不遗余力地向世人证明他们的文化理念的纯洁和至高无上。证明的方式几乎永远是礼赞别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似乎通过这一种礼赞,宣言了他们自己正实践着的一种文化和艺术的境界。而我们当然已经看透,这是他们赖以存在,并且力争存在得很滋润很优越的招数。我想,文化人和艺术家自身命运的苦难,与成就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艺术之间的关系,虽然有时是直接的,但并非逻辑上必然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文章憎命达”。当然这话也未必始于鲁迅之口,而是引用了前人的话。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一个人生来有福过着王公般的生活,那么创作的冲动和刻苦,就将被富贵的日子溶解了。例外是有的,但是大抵如此。
鲁迅先生在一篇小品文中也传达过这样的观点——倘人生过于不济,天才便会被苦难毁灭。不要说什么大苦大难了,就是要写好一篇短文,一般人毕竟尚需一二小时的安静。倘谁一边在写着,一边耳闻床上的孩子饥啼,老婆一边不停地让他抬脚,并一棵接一棵往他的写字桌下码白菜,那么他的短文是什么货色可想而知……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纳粹集中营里根本不会产生任何文学和艺术,尽管那苦难是登峰造极的。记录只能是后来的事。“****”十年,中国之文学和艺术几乎一片空白,不是由于当年的文学家和艺术家都幸福得不愿创作了,而是恰恰相反。
这么一想,真是心疼曹雪芹,心痛梵高,心痛八大山人和瞎子阿炳们啊……
在他们所处的时代,倘有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人生救济基金会存在着的话,那多好啊!
还有伟大的贝多芬,我们人类真是对不起这位千古不朽的大师啊!他晚年的命运竟那么的凄惨,我们今人在富丽堂皇的场所无偿地演奏大师的乐章,无偿地将他的命运搬上银幕,无偿地将他的乐章制成音带和音碟,并且大赚其钱时,如果我们居然还连他的苦难也一并欣赏,我们当代人多么的不是玩意儿呢?!
“苦行文化”的意识,是企图将文化和艺术用某种崇敬意识加以异化的意识。而这其实是比文化和艺术的商业化更有害的意识。
因为,后者只不过使文化和艺术泡沫化。成堆成堆的泡沫热热闹闹地涌现又破灭之后,总会多少留下些“实在之物”;而前者,却企图规定文化人和艺术家的人生应该是怎样的,不应该是怎样的,并且误导世人,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似乎比他们留给世人的文化遗产和艺术经典更美!起码,同样的美……
不,不是这样的。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我这么认为……
10.中国“尼采综合征”批判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理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后来是校园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的,相互浸润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伎。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八十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溶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在于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癫。
这是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培、海德格尔和隆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知而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理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以思想武器“行刺”上帝,是意义决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敌视或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截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的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几天就可以读完。十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的那一种。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地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但——他对“哲学”二字并无什么切实的贡献。这样的哲学家全世界很多。名字聒耳的不是最好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看,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一九○二年,尼采死后第二年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
再二年后,王国维在《叔本华和尼采》一文中,亦对尼采倍加推崇,所予颂词,令人肃然。如:“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之以极伟大之智力,高瞻远瞩于精神界”,并讴歌尼采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又三年后鲁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抨击扫荡焉”;“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朕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一向以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鲁迅,对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东一西,各自为战却不谋而合。
到一九一五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也更见容于当局。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中国的一概当局,向来是颇愿表现出宽谅的开明的。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一九○○年到一九一五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国之封建统治的历史,比大日耳曼帝国之形成并延续其统治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国是没有“知识分子”一词的。有的只不过是类似的译词,“智识分子”便是。正如马克思曾被译为“麦喀士”、尼采曾被译为“尼至埃”。
早期中国文人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