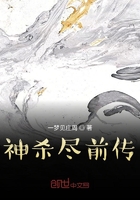千绯不愿再理会花仲天,径自站起来,慢慢的踱回绣架前,重新拿起针线。
皇帝待她确实是极好的,任她怎么任性、怎么闹腾,都没有怪罪过他。对皇帝这样手握天下苍生的人来说,能至如斯地步,确实是极为难得的了。只是千绯早就心有所属,这来自情窦初开的少女时代的爱意,岂是说放就能放下的。
只是如今,念了这么久,千绯已经累了,很累,便不再想了吧。
千绯想着就在这华丽的牢笼里了此一生,也算是常人求不到的幸福了,这样想着,自欺欺人的安慰着自己,念叨了这几些年,也就相信了这个退路了吧。
这是千绯从来都没有停止认为,自己这一生是多么的失败,是多么的不甘。这样的悲剧千绯怎是能看见落在他人身上的。更何况,现在要走上自己老路的,是自己在这个世间唯一的嫡亲妹妹了。
此情此景,千绯的内心如在地狱的油锅上煎熬着一样,如此的痛。
千绯心乱了,手下的功夫也就散了。各色的绣线都如同千绯的心绪一般,在绣布的下面,团做了一团,彼此缠绕,结成了再也解不开的死扣。
千绯右手执针,拼命地向外拉扯着绣线,只是拧在一起的线团,岂能被拉扯出绣布。千绯发狠似的拉扯了几下,定然是无果的。其实千绯明白是绣线缠绕在了一起,只是瞬间被一股凭空来的执念控制了心神,忘记了冷静和理智罢了。
怔然间,细细的绣线终是承受不住千绯的狠命拉扯,利落的断开了。千绯暮然回神,颓然松手,就连针从绣线上脱落,“叮”的一声掉在了地上,都没有理会。
是啊,花千绯,你已经是个棋盘上的弃子了,若是偏安一隅,或许还能苟延残喘的活着,若是不听从安排,恐怕就要消失了吧。
千绯知道就凭今日,手里掌握着皇宫中数百名仆役的这一点点权力,绣花读书的这点儿本事,如何能和手握天下的天子相抗衡,如何救得了妹妹。就连说服父亲,都是不可能的。
若是娘还在,若是娘还在,娘是断然不会同意娇儿嫁入皇家的。就连自己这个皇后,也是比不当了的吧。
若是娘还在,只是娘,已经不在了。
娘……
“绯儿,绯儿,你听得到为父的话吗?”花仲天叫了几声千绯。
“父亲还有何吩咐?”千绯拢了拢发髻,重新端端正正的坐在了椅子上,拿出了一国之母该有的仪态与气势,转瞬间,与刚刚无助的陷入了执念中的小女人一同,判若两人。
“也再没什么旁的了,既然你这么关心你妹妹,那你就多照顾照顾她吧。”
“照顾唯一的妹妹,那自然是我这个做姐姐的,分内的事情。”
“为父一直知道绯儿是个通情理的,心地善良,是个可以托付的人。既然绯儿如此承诺了,那为父就放心了。”
花仲天说完,行了一个拱手礼,深深的一作揖,“万事拜托娘娘了,臣告退了。”
“走吧”千绯懒得看一眼,就让花仲天出去了。
千绯只是在花仲天转过身去,跨出未央宫那高高的门槛时,瞥了一眼自己的父亲。
突然觉得这些年来,父亲似乎苍老了许多,迈过门槛的动作也不似从前那般轻松了,刚刚瞧见了父亲脸上的皱纹,也不知不觉的多了许多。
不过,苍老又能如何,生老病死,谁人能躲过。
花仲天出了未央宫,沿着来时的路出了宫门。
“驾”随着相府车夫的一声吆喝,训练有素的马匹一扬马蹄,马车缓缓的开始移动,马儿们步伐稳健的走在青石板路上,发出悦耳的哒哒声,引人沉思。
马车中的花仲天随着马车的晃动,自己也是晃动着的,在封闭静默的马车里,花仲天逐渐陷入了深思。
其实,刚刚花仲天自己是想要开口解释,却不知从何说起。花仲天想要说,当年的事,并不是千绯所想象的那样。这一切都是在为了她好,都是花仲天苦心经营的结果。只是时至今日,都开不了口。原先想着等到千绯再长大一些,就能自己想明白。
现在看来,人一旦陷入自己的执念中,这种偏执的相信力只会越来越重,是不可能自己走出来的,一个人是不可能自己打破自己建立起来的执念的。
但是,若是被外人强行打破,那股执念的消失,可能是支撑着她的最后支架的执念,也会消失无踪,到时候恐怕整个人都是要崩溃的了。
这可如何是好,花仲天不知道,花仲天自诩有匡扶宇宙的济世之才,只是这夹杂着人世间情感的难题,是无论如何也无能为解的了。
花仲天甫一出皇宫,皇上就出了小书房,直奔未央宫。
未央宫里,千绯拿起剪子,发了疯似的,绞碎自己已经绣好了大半的百鸟朝凤图。
但是千绯并没有大吵大闹,只是动作凶狠的,疯狂的把绣品剪成一条一条的破布,再也拼不起来。
千绯就这样,抱着双腿坐在地上,坐在一群破布中央,不哭、不闹,只是静静地坐着,了无生气罢了,就连皇帝驾到的唱和声,都没有听到。
宫曜洛一踏进未央宫,看到的便是这样的一副情景。
“绯儿,怎么坐在地上,快起来。”宫曜洛心疼的抱起千绯,放到了软榻上。
宫曜洛原想着千绯久居深宫,长日无聊,见到自己的父亲,心情能够好一些。只是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宫曜洛兀自叹了一口气,他早该想到是这样的结果的。当年千绯百般不愿嫁给自己,是他和老师逼着千绯以师母牌位进祖坟这件事逼迫千绯,才使得千绯嫁了的,千绯若是放得下这口气,就不是当年爬过万人坑的花千绯了。
宫曜洛也想解释的,只是事到如今,自己也好,老师也好,都对这件事无能为力。
千绯再如何也是不会再相信他们两个人了。
这误会,冰冻三尺,任是这盛夏再酷热难当,都再难消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