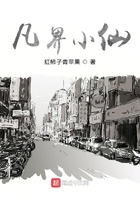学士府里,项闻济看着那笼中的麻雀犯愁。
他回府的时候,还以为谢祁送的礼是为了给自己赔罪的,想着自己好歹也是朝堂官员,谢祁肯定也不敢和他撕破脸。
却没想到,揭开笼子上边的黑布,里面却只躺着个死掉的麻雀!
真要把他的魂都吓掉了!
项北辕反应得快,一见了那麻雀,便想起昨晚父子两人在屋里嚼舌根时说的话。当时,项闻济把云危画比作了麻雀,说她被踩死了都不会有人搭理。
想来这话,是被白王府的探子听去了,又传到了谢祁的耳朵里。所以今天,谢祁才会给他们来这么一出。
——这白王的手伸得是有多长啊!连他们两父子偷偷在屋里说的话都能打听到。
见着麻雀的样子,项闻济便懊恼不已!原来不是云危画在摆架子给他们看,是谢护卫故意给他们颜色看呢!
谢祁有意护着云危画,也就是说……那云危画在白王府有一定的地位了?
这还怎么得了!他今天可实打实地和王妃娘娘吵了一架!
于是项闻济赶紧准备了东西往白王府去了,想着赶紧见着那两个主儿,赔罪一番,想法子把这一页揭过去。
结果呢?
人家白王府直接闭门不见,礼照收,就是不肯露面。
而谢祁,又是出了名的记仇性子。
项闻济满心懊恼,瘫倒在太师椅上,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次得罪了白王府、以后可该怎么办啊……
项北辕也烦恼不已。这整件事情,说到底都是他“中了毒”引起来的,作为项闻济的儿子,他心中也愧疚。
“哎,和白王府的梁子算是结下了,这以后……”项闻济看着笼子里那只死麻雀,眼睛都红了。
项北辕赶紧吩咐人把那鸟笼子扔出去,免得项闻济看了烦心。他思忖片刻,道:“父亲,可这世上,又不是只有白王府一个皇家。”
项闻济埋着的头抬了起来:“什么意思?”
项北辕起身,在大厅里踱步。片刻,好像是打定了主意,凑到项闻济的耳边,悄声道:“不如考虑一下,昨天苏老爷的提议?”
这个想法一出现在项闻济的脑海,就好像烙在了上边,怎么甩都甩不掉了。
听从苏遗通的提议……投靠明德皇帝!?
是,是了。
如果真得罪了白王府,那么明德皇帝那里,确实是项家最好的避难所。可这也意味着,项家从此再也不是一个中立的门第。
白王和明德皇帝之间,注定了只能留一个,项家一旦参与了站队,就要肩负起这两兄弟竞争带来的后果。
项闻济不敢,不愿,却好像……也别无他法。
“父亲,现在只能这样了!”见项闻济还在犹豫,项北辕再次怂恿道,“陛下是遵从遗诏登基的,名正言;这阵子白王府又折损不少,想来之后也再难翻身。若遭到白王府嫉恨,那唯有跟随陛下,才能保住项家!”
项北辕的一番话,仿佛点醒了梦中人。项闻济眼里泛着血丝,飞速地在脑子里分析了一下如今的状况——是,自从上次白王“失心疯”之后,白王府麾下确实折损了不少,估计以后也不会好过了。
“快,把笔墨拿来!”项闻济又重新振作了精神,吩咐着仆人,“我得赶紧给苏遗通写封信!”
-
另一边,云危画回了谭风院以后,舒心和鹦歌赶紧迎了上来,进了屋,鹦歌二话不说就跪在了地上。
云危画一愣:“鹦歌,你这是做什么?”
鹦歌噘着嘴,捻动衣角,却也不说话。舒心侍立在一侧,也是面露难色。
云危画见两人神色有异,道:“出了什么事,直说便是。”
舒心从怀里拿出一被锦帕包着的物什来,递到云危画的跟前。那锦帕是上好的布料,绸缎丝滑,薄如蝉翼,上边还绣着一只粉嫩的牡丹,一看便知是贵重人家的物件。
云危画接过来,拆开看了,里面包裹着的是一堆黄色粉末,闻起来还有淡淡的清香。
那味道,云危画一闻就察觉了端倪,和她在闲月阁的老槐树上取下来的药粉一模一样!这是害她容颜尽毁的毒药!
云危画蹙紧了眉头,望着鹦歌,问:“这是怎么回事?”
鹦歌红着脸:“昨晚在路上碰见了三夫人房里人,她们……她们把这东西给了奴婢,要奴婢将这东西放到小姐的吃食里!小姐,当时她们人多,我不得已才接了,鹦歌没想害小姐的啊!”
云危画将毒药包好,放到小桌上:“你怎么知道,这是害人的物件?”
“奴婢本想扔了它的,又好奇那三夫人卖的什么关子,就将药粉兑在昨晚剩的鱼塘里给了路边的野猫了……”仿佛是想到了什么异常恐怖的事情,鹦歌整个身子都颤抖起来,“哪知那猫儿……那猫儿死了!而且浑身溃烂生脓,可怕极了!所以鹦歌……就找了舒心姐姐出主意,决定把这事儿告诉小姐!”
“小姐,鹦歌绝无二心!收了这物件也只是怕三房的人胁迫,三夫人心肠歹毒,小姐不得不防啊!”鹦歌跪在地上,言辞恳切,“对了!这银两,这银两是三房的人给的,鹦歌不敢收!”
鹦歌从怀里摸索出一锭银子来,放在了云危画脚边。
“小姐,”舒心观察着云危画的神色,小心唤了一声,“我见过那猫儿的死状,真是可怕极了。鹦歌还小,她被吓得魂都丢了大半呢!”
知道舒心是在给鹦歌求情,云危画揉了揉额头,道:“起来吧,这事儿我知道了。”
“小姐?”鹦歌好像还没反应过来,大约是没有想到,云危画会这么轻飘飘把这一页翻过去。
云危画见她还是一副小心谨慎的样子,便走上前亲自扶起了鹦歌:“我在这世上没什么亲人,和丞相府也早已经决裂。我还能信的,也就是你们这两个丫头了。”
上一世,舒心对自己的忠心云危画见过;鹦歌坚定不肯害主的心她也见过。至少在短期里,只要不发生什么变故,云危画相信这两个丫头。
这也是嫁入白王府后,云危画仍旧固执地要求他们两个服侍自己的原因。
鹦歌站起身,看了看小桌上的毒药,满面担忧:“可那三夫人心肠实在歹毒。小姐都出了云府了,她居然还不肯放过!”
“她不肯放过我,我更不会放过她!”云危画冷冷说着,一双眸子仿佛覆上了冰霜。
她原以为,重生之后揭开南宫卿安和项北辕的真实面目,保住云家的基业便也罢了。如今看来,不管是云百宁还是宁氏,都没有将她这女儿放在心上,甚至巴不得她死!
这些人想看她死,她偏要活着!更要活得漂亮!
云危画浑身的气质非同往日,眸子里满含恨意,舒心和鹦歌相互搀着,都对云危画如今的表现大吃一惊:这哪里还有半分怯懦的影子了?
“王妃!您在吗?”屋里气氛冷肃,却忽听见院子里的急切呼唤声。
舒心开了门,就见谢祁一身红衣待在院里,神色慌张。他的面前,则站着面容冷峻的段惊澜。
见了这阵仗,云危画还以为是项闻济告状告到了段惊澜那里,惹得白王不快打算处罚她呢。云危画上前一步,正要询问,却被段惊澜一把抓住了手腕。
段惊澜二话不说,运足了内力便飞上屋顶,带着云危画走了。
“小姐!”舒心和鹦歌看呆了。
飞那么高,万一白王一不留神手一软,把她们家小姐扔下来怎么办啊!
谢祁朝她们两个拱拱手:“两位姑娘放心,片刻就回。”
说罢,那火红色的影子也消失在了谭风院。
云危画不记得这是第几次被段惊澜揽在怀里了,只觉得他身上的味道异常好闻,全然不见新婚那日,身上满沾着的血腥气。虽是盛夏,可夜晚的时候空气还是有点凉,云危画拢紧了臂弯,搂住段惊澜的腰。
段惊澜的身子还是有了片刻的僵硬,却又很快恢复。
不知是过了多久,云危画觉得胳膊有些酸,快要搂不住了。感觉稍有松懈她就会从天上掉下去!
——看来以后,还是要自己学会轻功比较好,被人带着飞的话,危险性实在太高了。
云危画调整了一下姿势,想要避免自己从段惊澜身上滑下去。段惊澜仿佛也看出她体力不支,搂着她的那只手又紧了紧,只是那么一瞬间,云危画便觉得铺天盖地的温暖席卷而来。
给她一种久违的……安全感。
她最缺少的东西。
——看来,以后不学轻功也没什么,需要的时候找白王就行。比轿辇还快呢。
云危画心里的小算盘打得精细,却听到段惊澜开了口:“你重了。”
哈???
云危画抬起头,怒目而视。
仰头时,她恰好能看见段惊澜姓感又完美的下巴,还有一张微抿着的、带着冷硬感觉的唇瓣。
云危画想起那天夜里的亲吻来,觉得自己被那双唇瓣触碰过的脖颈又开始发烫。
——可惜了,怎么亲的不是嘴呢?
云危画舔了舔唇,为自己的想法感到羞耻,赶紧埋下了头。
她却不知道,自己刚刚那舔着唇瓣的动作都被段惊澜看在了眼里。段惊澜看着埋在自己怀里的小人儿,喉结不受控制地一动。
白王妃,还真挺好看的。
啧。
让人想做点什么。
“殿下!前边就是了!”谢祁的声音忽然传来,打断了段惊澜的思绪。
段惊澜只觉得原本酝酿的情绪和气氛全都不见了,脸色一沉,狠狠瞪了谢祁一眼。
谢祁被他这么一瞪,险些没吓得从半空中摔下去!
——殿下这是怎么了?瞪他干嘛?他他他好不容易追上了白王,却被白王瞪了!?
谢祁觉得自己一颗忠肝义胆都被段惊澜狠狠摔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