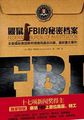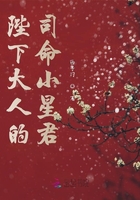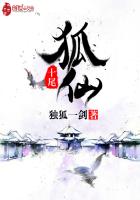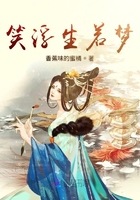莫斯科郊外的俄罗斯最大的东正教堂后来,普京又以旅游者的身份带着全家再次访问了耶路撒冷。那次从圣城回来之后,普京就成为教堂的常客。普京经常去教堂做礼拜引起了不少人的极大兴趣。在一次电话热线问答中,一位女职员问道:“常去教堂是不是因为心中有什么痛苦和烦恼?”普京承认,上教堂做礼拜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意愿,他还希望自己的孩子也2002年1月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距莫斯科150公里处的一座教堂里点燃蜡烛,庆祝东正教圣诞节养成这个习惯。
2002年8月15日圣母升天节,正在远东视察的总统普京百忙之中也抽空参加了赤塔市的祈祷仪式,并向打败土耳其海军为俄国夺取黑海、2001年被册封为圣徒的沙俄海军将军乌沙阔夫的圣骨行了圣礼。在这次活动中,当地的大主教明确表示:“今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圣母升天节日里,我们聚集在此不仅仅是为了举行一次爱国主义的活动。伟大强盛的俄罗斯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支不可战胜的海军舰队。这支海军舰队不仅要以精神建设为支柱,而且还要有崇高的道德观。”
六、外交政策发生较大变化
重振大国雄风,需要内外兼修。在全球化时代,俄罗斯既不可能再像苏联时期那样与外界隔离,也不能像苏联解体之初那样搞“一边倒”。普京认为,俄罗斯是全球大国,而非仅仅是有着全球利益的地区强国,尽管无须重蹈苏联扩张的覆辙,但绝不意味着放弃全球视野。基于这种国家定位,普京继承俄罗斯传统外交思想,主要是19世纪俄国外交家戈尔恰科夫的思想,以现代理论为指导,摈弃意识形态,提出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外交准则。
在2000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就明确指出:“我们对外政策的自主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个政策的基础是务实、经济效益、国家利益至上。”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又强调:“俄罗斯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实现我国的国家利益。”因此,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外交总的原则是:国家利益至上,突出经济外交,务实和避免对抗,外交服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
2000年6月,普京签署了新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该构想对俄罗斯在新千年的外交政策从国家定位到具体的实施过程都作了详细规定,认为俄罗斯外交方针至高无上的优先方向是保护个人、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为此,应主要致力于实现的根本目标是首先是确保国家的可靠安全,维护和加强其主权、领域完整、在国际社会中的牢固和权威地位,这种地位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俄罗斯联邦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势力中心的利益,这也是增强俄罗斯政治、经济、人才及精神潜力不可或缺的。
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目标与手段相平衡的基础上,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外交构想》明确提出,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是否真正有助于加强国家地位为标准,集中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及其他手段解决外交任务。为此提出五大任务:建立世界新体制、加强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关系、人权与国际关系、外交活动的信息保证。这一外交构想全面体现了普京的外交理念:
内外结合的务实观念。政策导向不是简单的好恶,而是以更好地为国家利益服务为要旨;外交应同俄发展目标和改善国民生活相适应,要有实际回报;安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要以实际进展和收获衡量政策;俄罗斯应在经济外交上更加进取,拓展商机、吸引外资将经济发展与政治、安全目标相结合。
全方位外交。同所有重要国家全面发展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在突出美国是俄罗斯最主要的战略关注点的同时,发展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如法、德、中、印等。
多边主义的国际秩序观。新的国际秩序应建立在多极的基础上,其中主要大国能对全球事务发挥影响,要有选择地运用多边主义和国际机构,实现政策目标。因此,多边主义是俄罗斯推进外交的重要手段。为了应对新威胁和挑战,必须加强联合国职能,依靠集体的力量,包括小国,也不排斥美国。
安全第一。安全始终是俄罗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俄美只要相互信任与尊重,完全可以对地区和世界局势施加积极影响,俄罗斯不需要与他国争夺世界影响力;未来许多年内,反恐、冲突管理和地缘政治问题将是最紧迫的外交任务,需要国际社会通力合作;俄罗斯会强调对话,不同欧美搞对抗。
弱化意识形态分歧。俄罗斯不会接受西方的“普适”价值观,但相信与不同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国家可以合作,安全、经济的互利不应以道德观念和政治为前提。
机遇与风险意识。俄罗斯要善于抓住机遇,作好准备,应对全球战略性变化可能带来的冲击,如中、印的崛起,大国关系潜在的紧张等。为此,将采用务实和规避风险的政策,使目标和手段相平衡。
在上述理念指导下,普京外交政策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尽量避免对抗,但不放弃核心利益。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外交优先方向的原则,普京认为俄罗斯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在俄罗斯周边营造稳定的安全形势,以便能为其最大限度地集中力量和资源解决国家和社会经济问题创造条件。因而确定“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优先方面是保证与独联体国家进行多边和双边合作,重点是发展与独联体所有国家的睦邻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以维持对独联普适价值观:或说普世价值观,指超越文明、种族、民族、宗教等的人类共同适用的价值观。然而,西方的“普适”价值观往往带有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因而为许多非西方国家所指责。
体的影响力。
从历史来看,“泛斯拉夫联盟”是19世纪中后期沙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当时,在东正教教会的支持下,沙皇接受了泛斯拉夫主义学者有关“罗马-日耳曼世界与斯拉夫世界互相排斥,东正教是斯拉夫人的真正宗教,只有俄国的救世主义才能解放在东欧居多数的全体斯拉夫人”的观点,以“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名义向西扩张。泛斯拉夫主义思想也充分反映在冷战期间苏联的对外战略中。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独联体。在中东欧各国纷纷申请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情况下,它就成为俄罗斯的最后的战略屏障,具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被俄罗斯视为其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目前,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倾向有加剧的趋势,外部的地缘政治干预也日益增强,但俄罗斯仍在努力维持独联体及其在独联体的特殊地位。
俄罗斯也将把与欧洲国家的关系作为外交优先方向,目的是建立欧洲安全与合作的民主体系。与此同时,重视维护业已形成的俄美合作的基“泛斯拉夫联盟”:泛斯拉夫主义最先由捷克和斯洛伐克学者在19世纪上半期提出。鉴于这两个民族弱小,无力抵抗奥地利当局的日耳曼化政策,由斯洛伐克诗人、历史学家杨·柯拉尔(1793-1852)和历史学家帕·沙法里克(1795-1861)提出在俄国帮助下建立斯拉夫各民族平等的大家庭的主张,得到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斯拉夫人的支持,却遭到受俄国统治的波兰人的反对。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奠基人是尼·达尼列夫斯基(1822-1855)。他在1869年发表的《俄国与欧洲》一书,以文化历史类型论为基础,把人类分为10种文化历史类型:埃及、中国、亚述-巴比伦-腓尼基-迦勒底、印度、伊朗、犹太、希腊、罗马、阿拉伯、日耳曼-罗曼或欧洲。此外,还有斯拉夫,主要是俄罗斯。他认为,日耳曼-罗曼文化正在走向衰落,斯拉夫-俄罗斯文化因其有东正教的统一性和农村公社的主谐性,有着无限美好的前途,必将取代欧洲文化。他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由俄国领导的称为“泛斯拉夫联盟”的斯拉大帝国。这个帝国的首都将设在君士坦丁堡,即沙皇格勒,帝国将统一使用俄语。它包括以下8个部分,其中4个是斯拉夫国家和地区:(1)俄罗斯帝国;(2)捷克-摩拉维亚-斯洛伐克王国:(3)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4)保加利亚王国;(5)罗马尼亚王国;(6)希腊王国;(7)马扎尔王国,即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8)沙皇格勒地区。在达尼列夫斯基拟建的泛斯拉夫联盟中没有波兰的位置,波兰在18世纪末被俄普奥3次瓜分后,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被第四次瓜分,其大部分土地以波兰王国名义被并入俄国。恩格斯指出:“泛斯拉夫主义的统一,不是纯粹的幻想,就是俄国的鞭子。”泛斯拉夫主义同斯拉夫主义的东正教弥赛亚主义(弥赛亚即救世主)不同,它是帝国世界霸权的工具。
础架构,因为俄美的互相合作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实现外交平衡,包括巩固与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改善与伊斯兰世界关系,为解决车臣问题创造外部条件。
综上所述,在俄罗斯新思想的指导之下,俄罗斯外交政策发生了较大变化,俄罗斯正在以一个全新的姿态出现于国际政治舞台。“9·11”之后,俄罗斯的国际政治观较之普京上任初期更加显示出务实的特点,哪怕不惜做出重大的牺牲和让步。与此同时,仍然坚持全方位的外交政策,力求争取更大、更广阔的国际空间,早日实现普京恢复俄罗斯大国、强国的地位的思想。
七、国家模式定位:不左不右的公民社会普京上台时,面对激进改革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既要继承改革路线又要对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他说:“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精疲力竭。只有幻想家或对国家和人民冷酷无情的政治力量才会呼吁再进行一次革命。无论在什么口号下(共产主义的也好,民族爱国主义的或激进自由主义的也好)再发生一次突变,国家和人民都无法接受,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都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使俄罗斯复兴和繁荣的战略,应当以在市场改革和民主改革中一切好的东西为依据,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人民生活恶化,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要求。”
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普京坚持中派立场,稳健地将俄罗斯引向“第三条道路”,确立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明确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目标,基本改变了俄罗斯的混乱局面,出现了政局稳定、经济好转、外交独立的局面。从普京执政期间的民意调查可以看出,他已经赢得了大多数俄罗斯人的支持。至于未来俄罗斯的国家模式,普京认为,应该是不左不右的公民社会。俄罗斯老百姓不希望回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喜欢现在这个贫富悬殊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们企盼把俄罗斯建成一个公正、平等、民主、自由、法制的社会,这是一个体现公民意志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