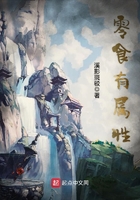庞老二的刀已刺中那白袍者的左胸,胯下的战马早和他心意相通,没有片刻的停留,就这么把那白袍者串在刀上,奔向官道的另一侧树林,一名敌军的轻步兵奋不顾身向前一扑,抱住那白袍者的双腿,就这么硬生生地把那白袍者扯了下来——从胸腹到头顶全被长刀勒成两半,没有血,没内脏,甚至没有骨头。
王逸从林内冲出时,左手结了个正一派手印,咬破舌尖喷出一口血来,吼道:“敕令!”此时这里张强的战马正轰然倒地。王逸冲出树林驰上官道,身后瞬间光芒大作,那金色光芒在半空中交织成一尊金甲神像,横眉怒目,怀抱金刚杵,威风凛凛!
“斩!”王逸怒吼一声,那金黄光芒裹着长刀,横斩向那结着手印,大约想准备弄出白光救治白袍者的轻步兵。王逸本是门阀子弟,虽无仙根道骨可入修真门下,但也学得正一派的几个咒法,以此历经战阵无往不利,这一刀斩落,但是顽石也要教它分离!
“叮”的一声,那轻步兵匆忙间举起长弓招架,弓刀相触,尽管把那轻步兵斩得腾空飞起,但王逸手上钢刀竟然断了。身为斥候,大军未行而先,原就是行走生死边缘的角色,何况王逸是数历战阵的,几乎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弃断刀,伸手握住那敌军轻步兵的弓背,便借这奔马之速,加之背后那尊金光神像还未消退,一下子弓弦套在那轻步兵颈间,尽管那敌军一手也持在弓上,但哪里能把握得住?电光石火之间,王逸已奔入官道另一侧林间,那轻步兵被自己弓弦割去了脑袋的无头尸身,犹自行了几步,才仆倒在地,血如泉喷。
这时古虎餐画完了五芒星的第五画,画起最后的圆。
“杀贼啊!”这是张强最后的嘶叫,五把骑枪再一次捅进他的身躯里,他终于无力地放开握在刀柄上的刀,那名重步兵脑袋上就这么嵌着刀,慢慢地软倒。
二千步外那三骑敌军,听得自己袍泽惨叫声起,慌忙勒马回转,那马确是神骏,片刻已逾数百步。但古虎餐也画完了五芒星最后一笔,便在那三骑离他二三十步之时,古虎餐发动了这个魔法,以五十多条人命为代价的魔法。
除非领悟了领域,否则没有人能在攻击时隐匿身形。古虎餐显露了身形,那三名敌骑向他举起了骑弩,那异界的战马也几乎在一瞬间就要将他撞飞,但时间,仿佛在这里变得黏稠了。古虎餐淌着泪,自谓谁的死活也与他无关的古虎餐,任谁都看出他心中的悲凄,他咬着牙凭空一拔,天地间五行元素疯狂涌起。
水在他手中凝结,他便以水为刀环,生出木来,为刀柄;再生火,为刀锷;复生土,为刀脊;金为其刃。他从虚空里拔出这把刀。
那三名敌骑看着古虎餐慢慢地凭空拔出这把刀,而他们的食指,离操纵骑弩击发的悬刀还有不到半厘,他们明明感觉自己的食指在慢慢地移向悬刀,但慢到不能再慢,慢到这半厘却几乎成为以他们的一生也无法达到的距离。
古虎餐斩下了第一刀。这一刀把一名敌骑连人带马竖着斫成了两半,那溢出的血,在以极缓慢的速度淌出,而那名敌骑尽管说不出话来,但眼神的痛苦,却清清楚楚地震撼着另外两名敌骑的意志——有什么比把一瞬的死亡的痛苦,无限地延长更可怕的呢?
而从千步外发出的白光早已到三名敌骑的身前三寸,但这三寸,却让这团白光如陷在沼泽里的旅人一样,无论如何努力跋涉,却越用力便陷得越深、越动弹不得。第二道、三道如云的白光,以至第四道,就几在一息之间已轮番掠到,但都陷于其中了。
古虎餐毫不犹豫地砍断了另一个骑兵和他的战马的头颅,把三具骑弩缴过来。他之所以要这陈三带治所的军士来,就是要引开对方轻骑,然后以王逸他们三名久经战阵的斥候冲击步兵,再等敌军轻骑回援之时,由他启动魔法,弄个活口回去。
他的计划里,是不用死一个人的。
只是没想到敌军的马居然如此之快,没想到敌军有如此犀利、连绵不绝的骑弩,没有想到传说中敌军的白光竟然如此之快、快到张强根本没机会冲阵后离开,没有想到治所那些军汉一个也没活下来……
就当古虎餐想把那两个被他杀死的敌军轻骑身上的装备,全弄到那匹活着的异界战马上时,一种极度危险的不祥感油然而生。古虎餐没有犹豫,从陈三殉职的那一刻起,他就清楚今天的计划是完全地失败了,他的生命随时有可能随着陈三一起逝去。
如同王逸瞬间弃刀、夺弓、用弓弦勒飞敌军的头颅一样,古虎餐心念未动已纵身骑上那匹活着的异界战马,咬破食指在那名活着的敌军轻骑前胸、后背、头盔、靴底,快速地画上四道禁魔咒,除了天牢甲号房的其他人,这个世上没有人比古虎餐画禁魔咒更快——十年,在甲号房呆了十年,日夜对着就是前后左右上下的禁魔咒,没事比赛谁画禁魔咒画得快,便是甲号房为数不多的娱乐。
就在古虎餐解除了这个时间魔法,拨转胯下异界战马时,那些白光在一瞬间就笼罩在那两名被古虎餐杀死的轻骑身上,那本来将要裂开的身体、本来下一刻就要掉下的头颅,在白光消失以后,完好如初。若他继续支撑这个时间魔法,直到最后力竭再解除,岂不是如张强一般,被那两个恢复的敌轻骑击杀当场?古虎餐吓得汗湿重衣,哪里还敢托大停留?把捉到的活口搁在马鞍前,催着那异界战马狂奔而去。
跑到起码离方才战场二三十里,古虎餐见身后没有追兵,才惊魂未定地停下马来喘气。
庞老二从自己先前挖的坑道里,慢慢地探出了头。方才越入树林远遁而去的,只是他的战马。他看着敌军那两个轻骑,在古虎餐逃离以后,居然没有追逐过去,只是呆呆地坐在那异界战马上,而那两匹异界战马,似乎也不太对劲,一点也没有方才那种神骏气势。
那名从他刀下扯成两半的白袍者,似乎从来没有受过伤似的,轻飘飘地跟在六名重步兵身后,那异界的战马,突然地发起癫痫来,把马上的敌军轻骑颠了下来,而那两个轻骑便坐在地上,呆呆地如傻了一般。
几个敌军的重步兵想去安抚同袍,却不料那两名敌军轻骑竟被惊吓一样的缩开,歇斯底里地挥舞手脚,然后惊恐地喊着一些听不懂的语言……疯了,人疯了,马也疯了!尽管语言不通,但分辨正常人和疯子,往往并不需要言语上的沟通。
庞老二心中对古虎餐很是佩服,他是目睹了古虎餐整个施法过程的,他也猜到那两个敌军轻骑发疯的缘故——原本一刀受的罪,在让时间变得缓慢的魔法里,也不知道这痛苦维持了多久,不疯才怪!
事实上古虎餐全力施为的这个时间魔法,足足缓慢了八万倍,也就是如果本来是一息的痛苦,那么将延续成一天。
张强殉难的悲痛,因着这两个敌军的发疯,在庞老二心里渐渐地减缓了一些,而当他注意到那个从他刀上抢下白袍者的轻步兵,正在痛哭着在路边挖掘土坑,似乎准备埋葬袍泽,而那个被弓弦勒飞了头颅的轻步兵,无头的尸体横在官道中间,一点活气也没有时,庞老二兴奋得几乎要把嘴里咬着的软木棍咬穿!杀得死,这些怪胎可以杀得死!只要杀得死,东陵有的是军队!
但他的注意力马上就被那些敌军的举止吸引了:六名暴跳如雷的重步兵,在发现同伴疯了以后,每人从左臂拆卸下小臂的护甲,又不知从哪摸出一些铁线团,塞进那个锥形臂甲里,然后六个臂甲不知用什么方法锁成一个管状,六面巨型塔盾也锁成一个支架;之后他们把那个臂甲套成的管子锁在巨盾组成的支架上,白袍者就把那臂甲管子的一头插入自己的腹部——庞老二几乎以为自己眼花,但是没错,那白袍者就这么把管子插进了肚子里。
那名正在挖掘土坑的轻步兵向这边凝视过来,似乎发现了什么,扔下手里的小铲拿起了长弓,庞老二暗叫不好,连忙慢慢地退进先前留下的坑道撤离。而就在这时,那巨型塔盾上的管子通体泛起光芒,七彩莹光流淌不绝,指向前方的管口猛地一下吐出长长的电光,然后那七色光便消失了,如烧红的铁条慢慢冷却一般;而此时才传来一声破空的声响。
那些敌军开始拆卸臂甲管子和巨盾支架,似乎完成了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庞老二撤走时,以为这是异界狄夷给死者送行的仪式。
但在三十里外的古虎餐却在为保住自己的生命而苦苦挣扎。在他发现危险时,仓促发动的时间魔法,对三十里外发射来的这枚弹丸效果实在不堪,古虎餐在十息之间右手至少画了五个五芒星,发动了五次默发的小型时间魔法,左手又在空中画了不下七张禁魔咒。
这颗弹丸从冲出臂甲管口以后,它并没有附带着一丁半点的五行魔法,禁魔咒完全就是对牛弹琴,而它快——无坚不摧,唯快不破!五个五芒星根本还没来得及反应,它就穿过了魔法有限的范围。
当那被俘虏的敌军轻骑的大腿皮肤被撕裂、肌肉被穿透,血的腥味开始急速散布到空气里时,那鲜艳的血花还未绽放,而这时那颗弹丸已穿过他另一条大腿,然后穿透古虎餐的左肋,从左背透出再洞穿那异界战马的脑袋,在路边松树上留下一个通透的洞,最后在一块坚硬的岩石上,击出四寸多深的深孔。
直到此时,那俘虏的惨叫才响起,那匹长角的战马头上的弹孔才溢出红白相间的液体。
古虎餐捂着被洞穿的左肋,痛得哆嗦着说不出话来。当血从指缝溢出来时,稍为缓过气来的古虎餐觉得自己的运气总算不是太坏,尽管伤口只是一个拇指粗细的洞孔,但如果再往上几分,这个洞孔留在心脏的话,那么他现在便不用考虑如何止血疗伤——死人只需要等待尸体最后一丝热气散去,而后慢慢僵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