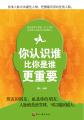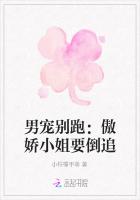当年我曾在美国加州的政府做过十年事,负责难民的福利,帮难民在美国定居下来。多数的难民都好相处,独独有一位越南来的难民态度蛮横,可能因搭渔船漂洋过海时,遇到海盗,受过刺激。我身为公仆,也不好对这位常出言不逊的人有所责难。
有一回他向我报告添丁,申请增加福利;我看机不可失,就去超市买了两只鸡送到他家,请他炖鸡汤给太太吃。他看我态度真诚,且身为政府人员无此必要“光临寒舍”,心中显然受到感动。从此与我联系时,口气全然不同。后来,他们全家要搬去洛杉矶,临走之前,他说要来见我一面。
来时,他手上拿着一包东西要给我,我说我是公务员不收“贿赂”,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钱买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五六条他钓的鲑鱼。
事隔多年,我每每想起这事,心中就觉温馨。我给的是鸡,他却回报我鱼。很多人都知道,美国的鸡是饲料鸡,很便宜;但是鱼,喝干净的河水,价钱比较贵。算一算,我给五美元的话,他给我的至少多了十倍。
真心付出摇回收丰富有余
在加州,我除了上班外,每周固定两次义务帮教会开车,接送妇女小孩。每次要先从家里开车去换教会的十五人座厢型车,再去接人;等聚会结束,送完人后,把车子还回去。后来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也浪费时间,于是计划自己买一辆厢型车。
去看一辆旧厢型车时,车主知道我的用途,特别算我便宜。我花点钱整修,开了两三年后,教会另有年轻人接棒,旧车用不着,我就登报出售。
第一个来看的人是位专业油漆匠,一看就中意,不但出高价,还附带帮我免费油漆房子。他出的价钱,扣除我买的原价,维修费及两三年消耗的汽油费,还绰绰有余,真是奇妙。我在想,一个人若肯给出时间、金钱,甚至是心力,回收的一定是加倍的祝福。
厢型车卖掉后,每次回家开车靠近院子,看到那粉刷得焕然一新的屋子,嘴角都会泛起会心的微笑。
善待他人摇全家蒙福受益
我有个舅妈,在我读初、高中时,很恩待我,每次去她家找表兄弟玩,她一定会端出好东西来招待;我要离去时,她也会塞些零用钱在我口袋里。当时我还年轻,只懂得“受”,几年下来,从来没有回报她什么。事隔四十年,我再次想起她老人家的恩情,才找到一次机会买点小东西给她。
舅妈如今已八十出头,笑容依旧,身体也很硬朗,与舅父都已庆祝过钻石婚,儿孙满堂,各有所成。这样看来,肯给人的,别人得祝福,他自己的福分也会代代传承。我现在愈来愈不难明白施与得之间的微妙关系。“施”只要真心,不求回报,不计代价,都像在播种一样;种子在地里暂时看不见,但时候一到,一定会结出许许多多的果子来。
台湾曾被讥讽为“贪婪之岛”,许多人只要得,不肯付出。让我们都来学习“给”,以给代得,久而久之,臭名就会有洗刷的一天。
做人要慎对一个“比”字
人生应慎对这个“比”字,同高人比较使自己高洁,同粗人比较使自己粗鲁,同智者比较使自己聪明,同俗人比较使自己沉沦。
生活是一个宏伟的竞技场,人们尽可以在那里进行夺取胜利的较量,而较量就是“比较”、“比试”、“比赛”。人一来到世上,就为这个“比”字所困惑,所纠缠。读书时比分数、比成绩、比名次,长大后比财富、比地位、比名气。
“比”字看去很简单,很直接,一目了然,然而它却隐藏着人生的大智慧。比什么,如何比,跟谁比,无不检验着人们的人格品位、知识修养、襟怀情操、精神实力。老虎同绵羊比试,比出了凶猛残暴;麻雀同苍鹰比试,比出了浅薄无知。万物之灵的人,也常常在和别人的比较中比出了丑陋和荒唐。
台湾作家林清玄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富翁的儿子,为了能像父亲那样凭自己的实力白手起家开创新的基业,便打造了一艘坚固的木船去闯荡天下,他闯过了险风恶浪,经过无数的岛屿,最后在热带雨林找到了一种树木,这种树木高达10余米,在一片大雨林中只有一两株,砍下这种树木经过一年时间让外皮朽烂,留下木心沉黑的部分,会散发出一种沁人肺腑的香味,放在水中,也不会像别的树木浮在水面而沉到水底去。他把这种珍贵无比的木材运到市场去出售,可是一连数日无人问津,他非常烦恼。偏偏在青年隔壁的摊位上有人在卖木炭,那小贩的摊前每天总是围满了人,生意兴隆得很。青年开始并不为所动,日子一天天过去,清冷的日子终于使他产生了“比”的念头:“既然木炭这么好卖,为什么我不把香树变成木炭出售,也兴隆起来?”
这一比,比出了荒谬,青年第二天把香木烧成木炭,运到市场,一天就卖光了。青年高兴地告诉父亲时,父亲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孩子,你那烧掉的香木,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树木‘沉香’呀,只要切下一块磨成粉末,价值就超过一车木炭!”
青年目瞪口呆。
“比”字伴随人生,无时无刻不像恶魔一样袭击着人们的心灵,它是人们心灵动荡不能自在的根源,使得大部分人都迷失了自我。一个在讲坛上辛勤耕耘了十年的教师,忽一日看到当了建筑包工头的昔日同学坐轿车、住别墅,看看自己吃粉笔灰的寒酸,心态失衡了:“他一个四门功课挂红灯的‘傻帽儿’能挣大钱,我连他都不如吗?”于是辞职下海,最终弄得鸡飞蛋打,沦为乞丐;一个才华横溢,多年来献身舞台艺术的青年演员,曾多次在省市和中央舞台上获奖,然而同那些跳槽离团的女友相比,感到自己“白活了一场”:她们在歌厅酒吧穿金戴银,一夜挣来的钞票能抵她一月的工资。这样一比她放弃了人生的追求,混入灯红酒绿的浊世做了陪酒歌女……人生应慎对这个“比”字,同高人比较使自己高洁,同粗人比较使自己粗鲁,同智者比较使自己聪明,同俗人比较使自己沉沦。当“比”的意识浮现脑海时,不妨远眺自己的人生道路,审视一下灵魂是否清白,权衡一下利弊得失,然后量力而行,惟如此,才能比出气度,比出高度,比出境界,比出人生的智慧来。
舍得
我们只要真正把握了舍与得的机理和尺度,便等于已经把握了人生的钥匙,成功的门环。要知道,百年的人生,也不过就是一舍一得的重复。
郑秀文唱过一首很著名的歌,歌名《舍得》。歌的结尾有这么两句:“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过我自己的生活。偶尔想你的时候,就让回忆来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曲调沉郁优美,歌词充满禅意,每听一次,心弦都会有所触动。贾平凹先生有一篇文章,说的也是“舍得”。在贾平凹先生看来,世界是阴与阳的构成,人在世上活着也就是一舍一得的过程。诚如先生所言:会活的人,或者说取得成功的人,其实懂得了两个字:舍得。不舍不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平凹先生是个参悟透了人生的奥妙与玄机的人,的确,“舍得”二字,其实已经囊括了人生所有的真知。追根溯源,舍得一词,最早出自佛经《了凡四训》。在传入中国后,迅速与中国传统的老庄道学思想相互融合,成为“禅”的一种哲理。随着光阴的流转,舍得这一禅理,又迅速渗透到了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逐步演进为一种雅俗共赏,启迪心智的“生活禅”。
舍得舍得,不舍不得,这是人们对佛教“布施”观念在寻常生活中的运用。“布”,是流通的意思,“施”是给予的意思。舍得,便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人生境界。舍得还是一种时空的转换,精神和物质的交流,人情和礼节的传达,是物质世界的“流通”。
从古至今,有不计其数的著名人物,取得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抑或巨大成就。他们的成功,无不得益于对“舍得”二字的把握和了悟。田忌与齐王赛马,舍小负之悲,得全胜之喜;诸葛亮自出茅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谓之,舍私益,得百世流芳;越王勾践亡国被俘,卧薪尝胆,饱受凌辱,谓之,舍王尊,得江山社稷光复;韩信以三千将士迎战二十万赵军,背水一战,谓之,舍生死,绝退路,最终得到的是以弱胜强;陶渊明仕途不平,归隐山林,安享“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乐,谓之,舍名利,得自然之奇趣;王羲之,勤学苦练,成古今之书圣,谓之,舍闲娱,弃安逸,得《兰亭序》绝世之美体;李时珍一生行医济世,救死扶伤,历经艰辛,终成巨著《本草纲目》,谓之,舍个人之安乐,得天下之安康;林则徐凭借一身正气于虎门销烟,弘扬我国威,捍卫我尊严,谓之,舍个人之安危,得民族之大义;雷锋舍个人之私,得助人为乐之榜样;李素丽舍个人荣辱,得社会“活雷锋”之好评;焦裕禄舍个人利益,得兰考人民万世爱戴……人如此,万事万物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蛇是在蜕皮中长大,金是在沙砾中淘出。就是在我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不也是每时每刻都在围绕着舍与得和得与舍,演绎着无数成功和失败的故事吗?
舍得既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更是一种处世与做人的艺术。舍与得就如水与火,天与地,阴与阳一样是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概念,相生相克,相辅相成,存于天地,存于人生,存于心间,存于微妙的细节,囊括了万物运行的所有机理。万事万物均在舍得之中达到和谐,达到统一。要得便须舍,有舍才有得。
我不否认,作为一个凡夫俗子,我们有着太多的欲望,对金钱、对名利、对情感。这没什么不好,欲望本来就是人的本性,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生产力。但是,欲望又是一头难以驾驭的猛兽,它常常使我们对人生的舍与得难以把握,不是不及,便是过之,于是便产生了太多的悲剧。因此,我们只要真正把握了舍与得的机理和尺度,便等于已经把握了人生的钥匙,成功的门环。要知道,百年的人生,也不过就是一舍一得的重复。
舍得,是一种精神;舍得,是一种领悟;舍得,更是一种智慧一种人生境界。
自由与猪
罗曼·罗兰说过:“也许只有到了一提到自由便潸然泪下的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自由的可贵。”
把自由与猪相提并论,绝没有诋毁自由的意思,这一点我必须首先声明。猪绝不是自由的使者或者化身,相反,猪一生都生活在圈栏中,活动范围极其有限。高尔基曾激烈抨击过“猪栏式的梦想”———他说,“一个人在生命的盛年,只知道吃吃睡睡,那算是什么东西?不过是一头猪!”这话对年轻人很有警示意义,当年我读到它就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猪的白吃白喝是要付出惨重代价的!猪有位勇猛难驯的兄长,一生啸傲山林,饥餐野果,渴饮清泉,很有侠士兼隐士的作风。不用我提醒你也知道那是野猪。人们蔑视猪,却对野猪保持警惕,就像敢于轻侮武大郎却对武松畏惧三分一样。但人们不该忘记猪的天性是野的,是人使它变得老实而驯服。也就是说,是人使猪失去了自由。在没有自由的环境里,猪就会一代又一代变得越来越温顺,任人宰割。
有篇文章名叫《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作者王小波。这是一个辛酸而幽默的故事。王小波插队的时候喂过猪。在一大群猪当中,有一只又黑又瘦、两眼炯炯发光,这家伙能像猫一样跳上房顶晒太阳,还能学拖拉机响和汽笛叫。除了容许喂它的知青走近它,其余人一旦靠近,它不是咆哮就是出逃。后来因为学汽笛叫造成糖厂工人提早下班,这头猪被定成坏分子遭到持枪兜捕。但令人惊叹的是这家伙居然机敏地跑掉了,回到大自然过上了自由自在的流浪生活。
王小波在文中亲切地称这头猪为“猪兄”,就像《红楼梦》中贾宝玉称石头为“石兄”一样。我想他一定在这头猪身上发现了某种闪闪发光的品质。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这头猪不过是在撒野,而作为知青的王小波却由此联想到人的自由。
我听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叔子先生做的一个学术报告,他讲自己“文革”中下放劳动的经历时,也有一个与猪有关的故事:饲养场的工人师傅分配杨叔子打猪草,这可叫从小长在城市的他犯了难。漫山遍野都是草,哪些是猪草呢?作为“五类分子”,他又不敢向贫下中农请教。正在着急之际,杨叔子灵机一动,把猪赶到山上,看猪吃什么就打什么,居然圆满完成了任务。杨叔子先生这个报告是讲思维观念的更新的,他谈到把猪赶到山上时用了一个词———天赋猪权。我想,当年杨先生看到这群猪在蓝天下随心所欲地啃吃葱绿鲜活的猪草时一定会心生羡慕:这真是一群幸福的猪!
罗曼·罗兰说过:“也许只有到了一提到自由便潸然泪下的时候,人们才会明白自由的可贵。”许多关于“文革”的痛切回忆,现在讲出来都成了笑话,不少年轻人对那些荒唐的故事都感到难以置信。这也不奇怪,如今人们的自由度提高了,语境变了,对事实的理解必然会有所不同,但当时的情况的确是那样。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笑忘录》中,提出了笑与忘两大主题,不过确切些说,笑而不忘,才是人类的希望所在。文章写到这里,离自由与猪的话题已经很远,但可以肯定的是,人如果长期失去自由却浑然不觉,就会越来越近似于又懒又蠢的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