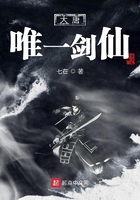(1)
法国当代思想大师、符号学家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说:所谓爱情,那只是深陷其中的恋爱一方的想象与虚构,是少年维特的白日梦。这个白日梦对于年轻的凡·高来说,也同维特一样,是无法治愈的伤痛。
(2)
1869年秋天,因家境日趋贫困,16岁的凡·高经叔父介绍到一家美术行当小职员。他诚实可靠,聪颖勤奋,不久被晋升后派往伦敦。在伦敦,他对房东太太的女儿厄休拉一见钟情。
这时的凡·高还没有对绘画着迷,他的理想是像叔叔一样成为艺术品经销商,美丽的厄休拉是他认为理想的艺术品经销商的妻子。
厄休拉身材苗条,大眼睛,鹅蛋脸,在凡·高的眼中,她就是一个天使。凡·高开始恋爱了,但恋爱在凡·高这里成了一个人的事情。他的恋爱更多的是想入非非的单相思。在他的想象中,厄休拉已经成了艺术品经销商凡·高的妻子:每天早晨喊他起床,给他准备早餐,在他就餐的时候,陪他聊天,说着让他高兴的话;他上班走了,厄休拉整理房间,准备晚餐,等待他下班归来。这样想着,凡·高情不自禁地向他的同事们宣告他要结婚的喜讯,人们都为他高兴,向他祝福。
可是,他还是没有跟厄休拉坦白他的爱情。坦白与否好像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厄休拉现在是艺术品经销商凡·高心中的妻子。
有一天,凡·高隐约听到厄休拉已经订婚的传言,他有些疑虑,犹豫再三后,鼓足勇气向厄休拉求了婚,厄休拉的回答证实了那些传言,她在一年前就已经订婚了。
这如晴天霹雳打在凡·高身上,他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他一直认为她知道他是爱她的,并且作为一个艺术品经销商的妻子而深感骄傲。
这次冷酷的拒绝给凡·高造成的打击是巨大的,因为他的性格过于真诚和神经质。他比所有失恋的人还要痛苦,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不幸的爱情史是一切悲剧的起点。
原来愉快的生活和亲近的人们在他眼里完全变了样,他对身旁的美景视而不见,失去了原来对于画廊工作的巨大热情,也失去了为公司赚钱的兴致。凡·高不再和同事们来往,更不喜欢他们来打扰他,他那生气勃勃的眼神不见了,剩下的只是被刺痛的忧郁,他选择了沉思和凝视,用漫无目的的游荡来消磨那些时光。
凡·高失恋了,画画就是他唯一喜欢的消遣,只有在此时他的头脑中才摆脱了厄休拉。经过一个假期之后,状况仍然没有改变,回到伦敦后,凡·高依然不知不觉地走到他幻想中的妻子的家。
对于厄休拉的婚期的日益临近,他只当没有这回事。在他的头脑中,那另外一个人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终于有一天,他亲眼看到厄休拉被一个身材修长的男人拖进了教堂,他才伤心地离开了英国。
这次恋爱改变了凡·高的一生,这个女人即使不是厄休拉,是任何一个女人,由于凡·高性格中的特殊性,他的初恋都会是一场悲剧。或者说这次恋爱唤醒了他血液中的偏执、狂热和抑郁,他性格中潜伏的这些因子在这场痛苦恋爱中逐渐积蓄、发酵,最终捕获了凡·高,让他的生命沿着它所规定的方向跌跌撞撞地奔去。从此,痛苦和荆棘就一直伴随着他。
(3)
离开了英国并不意味着离开了厄休拉。凡·高对宗教产生了热情,研读《圣经》的结果更使他滋生了狂热情绪,他整天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坐卧不安。现在厄休拉不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商的妻子了,他仿佛看到她是一个福音传道者的忠实的、任劳任怨的妻子,和他一起在贫民窟中为穷人服务。
几个月后,凡·高找到了在琼斯先生的监理会学校任职的一个位置。琼斯先生是一个大教区的牧师,他让凡·高当乡村牧师。凡·高不得不又一次把脑海中的想象加以改变,厄休拉不再是在贫民窟中工作的福音传道者的妻子了,而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妻子,在教区内帮助她的丈夫,就像他母亲帮助他父亲一样。他仿佛看到厄休拉对他不再经营艺术品、转而为人类服务一举感到高兴。
但人们被他的牺牲精神和苦行主义吓坏了。他那红棕色的头发,笨手笨脚的举止,莫名其妙的动作,褴褛的衣衫和过分明亮的眼睛,令人们感到不安。刚开始时,人们躲着他,远远地审视他;后来发现他并不凶残,就又开始不断地挖苦他。但孩子们依然惧怕他,女人们常常拒绝这个单身汉的好意。
1879年7月,这个乡村牧师因为不受人欢迎而被开除了,而厄休拉,作为牧师的妻子也已经渐行渐远了。
于是,凡·高生活中最阴沉的时期开始了,他在几个月里贫穷潦倒,精神崩溃。由于极度失望,他沿着大路流浪。
就是在这个时期,他给弟弟提奥写了封感人肺腑的信,宣布自己决定从此献身绘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