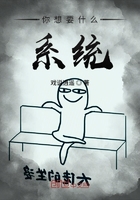“责罚,皇帝都舍不得责罚你,不过是降了莲衣的品级,哀家若出面责罚,人家只当哀家是恶婆婆。”皇太后言辞犀利,嫁入皇宫至今,不曾这般严厉地对待过我,又冷哼一声,“莲衣身为御前待诏,平日是怎么侍奉皇后,怎么告诉她宫里规矩的?竟让她为了你做出这样有失体统的荒唐事,皇帝降了你的品级,实在是太轻饶了。”
“母后……”
“滚去宫门前跪着,太阳不落山不许起来,好好反思你的过错。”太后大怒,勒令左右把莲衣架出去。
“母后,莲衣她……”我企图为莲衣求情,可太后却狠狠地瞪了我一眼,甩开我的手就往门外去,撂下跪在地上的我,头也不回地就离开了。
宫里大大小小都吓得不知所措,金儿跑去外头瞧瞧,又跑来搀扶我,哭着说:“娘娘起来吧,姑姑要知道您也跪着,怕是想死的心都有了,姑姑叫奴婢好好照顾您,叫您别着急。”
我晃晃悠悠地起来,举目看一眼正当午的骄阳,嘴里念念着:“太阳何时下山,何时才能下山?”
我不敢去门外看跪着的莲衣,无法面对被无辜牵连的她,一下午都过得恍恍惚惚,我摸不清太后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知道她是真的动怒怨我无知的行为,还是洞悉我和寰宇的心思才一起演这出戏,若是前者我不知何时才能与她解释真相,若是后者,寰宇又会不会误会?
脑中很混乱,我到底生不出一颗作恶的心,才胡闹了那么几天,就身心疲惫到了极点,更还连带莲衣受皮肉之苦,果然做好人最豁达最简单,永远不必惦记将来该怎么办。
“娘娘,娘娘!”金儿突然闯进来,这一下午她也忐忑不安,这会儿更是不知为何脸色苍白,扑在我脚下哭道,“娘娘救救姑姑,敬事房的人把姑姑拖走了,说要拖她去打板子,娘娘……”
我已顾不得听金儿把话说完,飞也似地冲了出去,果然莲衣还没走远,几个大太监架着跪了大半天早不能好好走路的她几乎拖着前行。
“站住!”厉声一喝,直觉得嗓子疼,但前方的人果然应声停下,而架着莲衣的太监手一松,她便跌了下去。
“去把莲衣带过来。”我吩咐身后的宫女太监,他们也是恨透了,不顾那些太监面目凶恶,一听我这般说,竟一拥而上把莲衣给抢了过来。
那边为首的太监是个面生的,皮笑肉不笑地走近我,躬身道:“娘娘,奴才是奉太后的旨意来带莲衣去用刑,娘娘这样做,奴才不好对太后交代。”
我不理会他,转身就要回去,更吩咐金儿:“去把袁太医请来。”可身后那太监却不肯善罢甘休,死死地跟着我,“娘娘这样可不行,奴才不好对太后交代。”
我怒而转身,扬手就是一巴掌挥在他脸上,那一声脆响惊得周遭煞静,我怒道:“一个奴才也敢跟在本宫身后?太后那里本宫自有交代,何时轮到你来指手画脚?你们!”我指向那几个太监,“把这个狗奴才拖走重责三十大板,胆敢有人姑息,不等你们去向太后交代,本宫先要了你们的命!”
那几个人目瞪口呆,个个愣在原地不动,我身旁金儿忙怒斥:“愣着干什么,没听见娘娘的话?”
为首那个太监挨了打先是怔了会儿,回过神忙嗷嗷叫:“奴才是替太后娘娘办事,娘娘怎么好责罚奴才……”
“给本宫堵上他的嘴。”我恨得咬牙,一声令下,身边小太监就拥上去按住了他,随手撕了块布就塞在他嘴里,那边跟来的太监眼看事情闹大了,忙也来抢走了他们的头儿,连声答应我会照着办,仓皇带着人就走了。
“金儿,去请袁太医来,告诉她是莲衣受伤了。”我不再理会那些狗仗人势的东西,吩咐金儿去找人,一边让大家把莲衣抬了进去,跪了一下午的她已经耗尽体力连话都说不出,膝下裙子也被血浸透了,小宫女轻轻撕开黏在血肉上的裙子亵裤,每每都疼得她浑身抽搐。
袁卓已来后什么话也没问,只是照我的吩咐为莲衣处理伤口,他随军行医时最擅长的便是治疗创伤,果然手法利落精到,莲衣不再像刚才被小宫女清理伤口时痛得眼眉紧蹙,伤口很快就被包扎好,一边御医馆已有煎好的药送来。
莲衣吃了药便安然入睡,我让金儿守在她身边,自己则独自回寝殿,袁卓已也收拾了药箱要离去,与我在廊下相见,他躬身道:“臣已做好准备,可随时随娘娘去凌岩山行宫。”
我一愣,却不知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是看透了我和寰宇的用意,还是仅简单地为元宵后做准备?
“好。”简单地应了一声,再不说什么话,撂下一众人回寝殿,孤零零地坐在镜台前,身心疲惫之下镜子里的自己看起来仿佛一下子老了几岁似的,憔悴的双眼里写尽了辛酸,可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