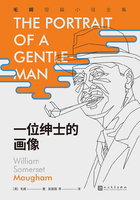曹跛子坟头的青草,绿了又枯,枯了又绿。正月十五的月亮临照了八次之后,春天又在云雾中探头探脑,要来提醒他的梦了。
那时,曹跛子正躺在山中的三角棚子里把呼噜打得山响,鸟雀不敢拢来。他的两条看山狗在不远处发现有人鬼鬼祟祟想砍树,汪汪汪的吠声惊得他翻身坐起,连忙穿了一只鞋,摸了那根檀木拐杖,就出了棚子。这时天已发白,启明星刚升起来,闪闪烁烁。近树远山正在渐渐露出清晰的轮廓,离天亮还有一袋烟的工夫。
他侧起耳朵,听清狗在桂花崖上叫。叫声急促,那是狗在唤自己快去。狗的每一声呼吸和叫唤,都含有不同的内容,他都能辨别清楚。他系紧了裤带,便一步一点地朝桂花崖赶去。那只空裤筒也就一前一后地摆,摆得很快。他要尽量走得快些,害怕那狗叫累了,委屈了那狗。
山路本来就很崎岖。靠近桂花崖,也就更加陡峭。路两边尽是灌木丛,常把那空裤筒拽着,不让走。他不得不停下来,把裤筒从那刺啊杈啊什么的取出来,再走。那空裤筒获得了片刻的自由,于是又一前一后地摆,摆得很快。
除了狗叫,林子再也没有其它的声音。若没有狗叫,曹跛子可以听得出鸟的声音、树的声音、溪的声音以及虫的声音土的声音石头的声音。那些声音在他听来都是天籁。他喜欢听那些声音,日伴那些声音巡山,夜枕那些声音入眠。可现在只有狗叫,满耳朵只有狗的声音。他在心里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哪个狗鸡巴日的惹得山林只剩下了狗叫!
他已经走上了桂花崖。狗还在前边叫,叫得更急了些。他的空裤筒也就一前一后摆得更快了些。
空裤筒一旦摆得快起来,他的胸口便发闷,气也赶不上了。曹跛子大张着嘴,简化了鼻孔那一道手续,直接用喉咙呼和吸。他这才觉得黄枯牛一样奔跑的日子已经去得很远,再也领不回来了。他突然感到日夜伴随他的那只脚,踩在青石上,竟飘飘的,有些虚,还不听使唤。他连忙用胳膊夹紧那根檀木拐杖,把自己支牢,不让身子晃动,免得栽到崖下去。
他是栽下去过的。那时牛牛才两岁多。那时他被称为曹家湾的一扇门板,两只裤筒并未空,都派上了很实际的用场。那天大家都在追赶一个砍树的人。跑着跑着,他就跑到了前面。那时他的腿真好使。他恨那些砍树的人,那些人偷偷摸摸,三斧两斧就把那好不容易长出来的树砍了,或变成了梁,或变成了柴。有的还悄悄地扛到山外去,变成了钞票。他跑到桂花崖的时候,离那砍树者的后背仅两步之遥了。谁知一块松动的石头,没有驮稳他的脚板,身子一斜,他就栽到崖下去了。
崖有六七丈深,黑幽幽的,看一眼也令人毛骨悚然。大家以为再没有活人了,队长正愁着到哪里去弄来一口棺材。可他却叹了一口气,松了大家的紧张,解了队长的围。七手八脚把他弄回家,无不说他命大。
他就丢了一条腿。
丢了的那条腿,在城里医院没有拿回来,裤筒从此就空了。空了的裤筒,在风中摆动,摆得众人心里酸酸楚楚的。大家推举他干脆去看山,也好弄几个工分。他脖子一歪:
“我残废了么,要把我养起?!”
队长也不说他废不废,给他点袋烟,让他云里雾里地吸。只说看山这活儿并不轻,春要栽树,夏要治虫,秋要防火,冬要防冻,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四季有活干。还要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睡觉也要睁一只眼。若是责任心不强,树就被人砍光了。你要是干不了,就等于我没说。
他脖子正了过来,两眼直视着队长:“上刀山我也干了!”便挑起了看山这副担。于是,山上山下,满山摆动着他的空裤筒。
后来,他满山摆动着的空裤筒被越来越茂密的树林挡得看不见了。再后来,林中的三角棚有了孙子树根的笑声。有了孙子的时候,他养了两条狗。两条狗跑起来像一道闪电,他说那是他的腿。他说狗是他的腿时,人们大多已经忘记了他曹茂公的名字,开口闭口叫他曹跛子。
砍树者怕曹跛子,曹跛子却怕堂客。在屋里,堂客说什么,他就点什么头。曹跛子很清楚,少了一条腿,多出一只空裤筒,若不是堂客撑着这个家,他一条腿能有么事用?自己有暖的穿、有热的喝?土地承包时,队长说:“曹跛子我到头了。你也下山吧!”
“我不!”
“没工分了。”
“我就图工分了?”
堂客在火里温了一盅酒,炒了一盘韭菜鸡蛋,煎了两条小鱼。趁他喝得额头冒汗时,堂客说:“撤回来吧,莫把一把老骨头扔在山里了!”
曹跛子正举起酒杯的手一下子僵住了,手背上青筋毕露,脸上皱纹粗粝:“你,你今日摆的是鸿门宴么?”
堂客也不让步,道:“现如今谁不是各顾各!你看山,能得什么好处?”
曹跛子酒杯一放,筷子一搁,摸起那根檀木拐杖,颠起就走,还扔下一句话:“浅,眼窝浅啊!”平生第一次没听堂客的话,空裤筒一前一后摆出堂客的视线,上了山。
牛牛又长成一副门板。他对哭泣着的娘说:“妈,田里地里都有我哩。父不回来就由他。要是硬让他回来了,没有事做,说不定还憋出他一身病来。”也就从此太平。
与牛牛光着屁股蛋一起长大的七犁,耕田种地总是蹒跚着,打不起精神,到山外去转了几趟,馋人家致了富,推倒茅棚起了洋房,心里也就痒痒,恨不得走路踢起一块金砖。忽然有一天得了点拨,真是守着金山想钱花哟。村子周围虽然全是山,可哪里埋的不是煤?那煤不就是钱么?用山上的树开一孔小煤窑,又不要本钱,是于民于国多大的好事!七犁便来找牛牛商量,请牛牛出面。牛牛见七犁满面放光,也受了感染,就上山,去讨父亲的意见。
曹跛子吸着一袋水烟,呼呼啦啦响。牛牛讲完了,等着父亲的回答。可父亲闷着头,只管抽自己的烟。
“父,你说行不?”
曹跛子又装上一袋水烟。
“你要是说行,我就去叫人来砍树。”
曹跛子把烟袋一磕,脸暗起:
“不行!”
“我就晓得你要说不行。父,你这不是跟大家过不去么?再说,这树又不是我们一家的,怎么能不要别人砍?”
曹跛子觉得有必要跟村人说清白,那空裤筒一前一后地便摆下山来。很快就拢来一帮男女老少。曹跛子咕咕地灌了两口水,就亮了喉咙:
“你们说,我们曹家湾的地脉风水好不好?”
大家一齐说:“当然好!”
“好在哪,好在山中有林,林中有溪。泉水夏天凉,冬天暖,你哪一个手上冻裂过血口子?”
“说正事,说正事!”便有人起哄。
“正事,么是正事?开煤窑是正事么?那才是败家子哩!”
“何以见得呢?”
“煤窑一开,也就越挖越深。动了地脉,水就带走了。没有水,莫要说山上的树长不活,就是人也活得难。山上的树砍一棵就少一棵,过不了多久,山就成了秃子。那还有风水么?那不是败家子干的么?!”
众人也不吱声。
七犁手叉了腰,不屑地道:“么事风水不风水,莫宣扬封建迷信那套玩意儿。什么地脉风水的,自从盘古开天地,我们村也从来没出过什么屌大人物!是出了几个举人,还是出了几个进士?他娘的大队长也没有出—个,还不是人人盘泥巴!盘泥巴现如今有什么出息,要是这煤窑一开……”
曹跛子用拐杖那么一磕,地像是动了两动。神色肃然地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七犁赌狠似的说:“开,煤窑一定得开!”曹跛子呼地立起来,一只腿竟也站得那么稳,满嘴唾沫星子飞溅出来:“狗鸡巴日的!我把丑话说在前头,煤窑开在哪里,我就死在哪里!”说罢,空裤筒一前一后地摆,在村子拐角上山处,消失了。
那煤窑就没有开成。
可上山偷偷砍树的渐渐多起来。一个月总有那么一次两次狗叫。这一次是哪个呢?敢上桂花崖上来,不就是欺自己有了气喘么?他往前走了几步,看见两条狗一前一后围着那个模糊的背影,不让他下斧子,曹跛子仔细一看,喝道:“七犁么?”
是七犁。七犁害怕被曹跛子捉住。捉住了那是多么丢人现眼的事!便往山上跑。曹跛子也就去追。谁知,一根青藤绊了他的脚,他失去重心,訇然倒下崖去。
七犁扭头一看,只见两只狗对着青幽幽的桂花崖吠得很惨,也就晓得了曹跛子的下场。心里竟也楚楚的,一个大活人说没有就没有了。
那两条狗突然不叫,呼呼呼地朝他蹿来。七犁有些慌。两条狗朝他齐齐扑来,把他扑倒在地,他吓得大叫,手中的斧头飞出老远。两条狗各咬住他的一只裤腿,把他拖到崖上来。
七犁一脸土色。惚恍一看,崖边下吊着那只空裤筒!再定睛一瞧,曹跛子挂在桂花树上,一双手吊在树枝上。
曹跛子有些可怜地说:“七犁,拉我上来!”
七犁只要解下腰带,或找一根青藤,扔下去几尺深,再弯下腰,就可把曹跛子拉上来。可七犁静了静心,两只眼立即骤起得意的光,完全是一种行家的口气,道:
“以后我来砍树,你只当没看见。”
曹跛子没有做声。
“老家伙!”七犁在心里骂道,“死到临头了,还把树当命!”七犁想,要想砍到树,只有砍断他的“两条腿”。没有了“腿”,一个跛子,量他也跑不赢我七犁,树还不是照砍不误?
七犁又道:“那就把你这两条狗给我!”
崖边桂花树索索抖动。曹跛子骂道:“你个黑了心的狗鸡巴日的。我只要没死,你甭想砍去一棵树!”
七犁道:“你曹跛子也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怎么就不晓得得让人处且让人这个理儿?你要满山的树做你的棺材么?”
也许是桂花树承受不起,曹跛子把那根弯枝吊直了。一阵风过来,枝叶簌簌响,那树像是瑟瑟地絮语,大约是叫曹跛子求七犁伸出手来,留得青山在,还怕不长树?
“曹跛子!你答应我,让我今天只砍一棵树,我就把你拉起来。”七犁倒像在哀求了。
曹跛子俨然是一个傲慢的怪物,吊在这棵芳香暗动的桂花树中,像是桂花树上长出来的一根不肯就范不肯屈服于撒野的魔风的树枝。这根树枝在风中摇摆,在迷蒙的晨曦中无力地垂挂着。突然,桂花树颤栗地呻吟一声,曹跛子猝然脱离树枝,那只空裤筒在风中飞舞,如鸟儿的翅膀。
牛牛把父亲抱回来的时候,曹跛子另一条腿也摔断了,幽幽地竟然还有一口气。
门外边围满了人。神情似乎是在料定之中,并无多少惊异,也无多少哀痛。有几个人还连忙嘱咐:“快烧纸,快烧纸。”孙子树根就跪在爷爷跟前,一边抹鼻涕,一边烧那盖了圆印的黄表纸,好让爷爷到了阴间有钱用。
牛牛倒有些急。父亲要落气了,还没有他睡的棺材。父亲满花甲那年,牛牛提出用山中木材打一口棺材。父亲说:“准备我死么?我还早哩。”坚决不同意打。牛牛跟娘说:“去借一口让父先睡好不?以后再还人家。”娘呜呜地哭:“这遭孽的老鬼哟……”
牛牛就去借。
棺材很快就借来了。两个膀大腰圆的汉子先把棺材盖抬了进来。牛牛把眼睛瞪得牛大:
“么样搞起的,你们吃屎长大的么?”
在乡里,抬棺材原来有很多的规矩,“要想死得快,先抬棺材盖”,牛牛怎么没有火!
其中一个答道:“牛哥,这是我的意思。你看,曹……”“跛子”两个字就要溜出口了,便顿了顿,“曹大伯摔成这样,还不是蚀心地痛,还不如早去,一了百了呢!”
牛牛气也不是,恨也不是,一跺脚:“还不快去把板抬来!”
这口棺材又高又大,是用九根圆杉树做成的。已经打了油,上了漆,闪着黑黝黝的光。众人也就七嘴八舌:“曹跛子睡这么好的大屋,算是享福了。”
曹跛子深陷的眼睛微微睁开了。他看到了儿子、孙子,都在他的面前,他的眼睛仿佛有了生气。他被痛苦糟蹋得扭歪的脸部,这时却很平静,呈现着死亡也能将我如何的那种神气。
当曹跛子看到那口棺材时,他的面孔顿时又扭歪了,浑身抽搐着,双目一闭,又不省人事了。
守了两天,曹跛子也没有落气。奇怪的是,只要他一看到那口棺材,他的面孔就扭歪了,接着就浑身抽搐不止,不省人事。有一老者对牛牛说:“是不是你父有话要对你说?要不就早落气了。”
牛牛就跪父亲面前,等他眼睛睁开。
曹跛子幽了一口气,又睁开了眼。牛牛就捏住父亲的手掌。“父啊,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么?”
曹跛子黯淡的眼神亮了些,他把目光聚在那口棺材上。
牛牛说:“这是村子里最好的棺材了。给你住的呢!”
曹跛子又盯住牛牛的险,嘴唇颤动着,却说不出话。牛牛感到父亲的手指微微动了一动。牛牛把自己手掌放平,父亲枯瘦的手指竭尽全力在他掌心划了一个“火”字。
牛牛脱口而出:“父啊,你要火化?”
众人也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外面的世界都兴火化了,在这偏僻的一隅山村,还没有过火化的先例啊!
曹跛子的目光抚摩着儿子,抚平了儿子的疑问,显得很安详。
牛牛叫人把棺材快抬出去。棺材刚抬出的时候,曹跛子就落气了。
曹跛子火葬之后的第三天,村人便开始砍树开煤窑,做那发财的梦。那煤越出越旺,巷子也就越掘越深。山上的树也就砍得越来越多,所剩也就越来越少。七犁扬眉吐气,当了煤窑的窑长,也盖起了山外那样的两层小洋房。
只是村人果真再喝不上泉水。溪水也无影无踪。奇怪的是,只要下雨,就起山洪,山呼海啸的,很骇人。一次,山上下来从未有过的泥石流,把七犁的小洋房给淌平了。
村人起五更去八里外的水库挑水吃。
曹跛子躺在山坡上,守着那山,再不发一言。他的在风中雨中摆来摆去的空裤腿,现在还有多少人记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