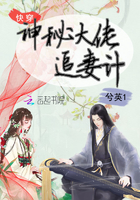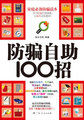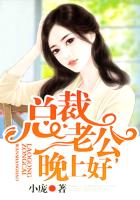米尔豪斯家族是镇上最古老的家族之一,把姊妹、表亲和姨妈们都算在一起,这一家包括好几十人。这个家族最初是以尼克松的外曾祖母伊丽莎白·普赖斯·米尔豪斯为女族长。这个卓越的妇女,和她的先辈们一样,完全是杰萨敏·韦斯特的动人小说《友好教派》中的伊莱托·科普·伯德韦尔一类人物。她死于1923年,终年96岁,那时的尼克松只有10岁,但却完全记得她。
尼克松的外祖母阿果米拉·伯奇·米尔豪斯一直活到94岁。圣诞节举行传统的团聚时,她总爱穿着她最好的红色天鹅绒礼服庄严地坐着,接受孙子、外孙子们送给她的极平常的礼物。她对这些礼物一视同仁地赞扬一番,对每一件礼物都说是她特别需要的。但她对小尼克松似乎特别感兴趣,在尼克松的生日和其他一些特殊节日,她总是写一些诗送给他。1926年在尼克松过12岁的生日时,她送给尼克松一幅嵌在镜框里的林肯像,以及她亲笔录下的朗费罗的《生活诗篇》中的几行诗:
伟人的一生常提醒我们,
要使自己一生崇高庄严,
在去世时,
在时间的沙滩上,
留下我们的足迹。
尼克松一直把这幅像挂在家里他睡觉的床头,这幅林肯像伴随了他的整个少年时代,直至一生。也许正是外祖母给予了尼克松这种对伟人及政治的崇拜的心理,使尼克松萌发了自己也要成为林肯式人物的愿望。他钦佩林肯的那种超群的智慧和丰富的阅历,以及当涉及真理和正义的基本原则时,像钢铁一样坚定不移的意志,还有那孜孜不倦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恒心。
尼克松把林肯作为他当时最敬仰的人,他一直把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词中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我们在这块土地上说过什么世人很少会注意,也不会长久地记住,但是那些战斗过的活着和牺牲了的英雄们在这做过什么,却永远也不会被人遗忘。我们要继承他们为之战斗的,迄今已发展起来的事业,让这个国家获得自由的新生,让这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而后,外祖母又送给他一本《甘地传》。小尼克松如获至宝一样,废寝忘食地从头到尾看完了那本书。甘地的和平改革和消极抵抗正合外祖母的心意,因为她是一个反对一切种族或宗教偏见的虔诚的教友会教徒,而甘地那种视政治如生命,一生为自己的国家献身、热爱人民的无私忘我精神,是那样深深地感染着少年时代的尼克松。
尼克松生长在一个既是非常严格,同时又是非常宽容的宗教环境里。他的母亲和她的家族信奉教友会的一个支派,它也有自己的牧师和唱诗班,实际上具有其他新教派所具有的一切特征。仅有的差别是,教友会没有洗礼和圣餐,并特别强调默祷。尼克松的父亲是在结婚时,从一个相当坚定的卫理公会教徒皈依教友会的,他因而也具有皈依者对他的新宗教的特殊的热忱。星期日,他们一家一共去教堂4次:一次是去主日学校,一次是做例行的早礼拜,下午晚些时候去一次勉励会,晚上还要做另一次礼拜,星期三他们要做夜礼拜。在尼克松读中学的几年里,他每星期还为教堂里的各种礼拜弹钢琴。当他八年级毕业时,他的母亲送给他一本《圣经》,在以后的日子里,尼克松在晚上就寝之前总要读上几节《圣经》。
约巴林达和惠蒂尔教会那么广泛的宗教活动,也还不能使尼克松的父母感到满足。他们两个人对当时的一些福音派教徒和信仰复兴派教徒十分着迷,因而他们常驱车到洛杉矶的安吉勒斯教堂去听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讲道,并到卫理公会三一教堂去听麦克弗森的最大竞争者鲍勃·舒勒的讲道。这时候,尼克松的父母做出决定,把已经12岁的尼克松送到一家离家较远的教会学校去寄宿读书。
那是一个拥有100多名学生的学校,老师都是教友派的信奉者。因为母亲是教友会的,小尼克松以前也常常伴随母亲去教堂做礼拜,所以他对老师们一身黑袍子还不算陌生。
可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们个个都是凶巴巴的,每天早晨6点钟,所有的学生都要起来朗诵《圣经》里面的诗文,而且所学的课本也比其他普通学校多一样《圣经》。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令小尼克松特别思念父亲和兄弟们。
小尼克松刚入学的时候,就是因为上《圣经》课时溜号而被罚站,那是尼克松第一次因为学习而被处分,而且当时最令尼克松难以忍受的是晚上睡觉时不准穿内裤,说是怕影响孩子们的正常发育。许多孩子初时都很不习惯,晚上睡觉时偷偷穿着内裤,可是有几个人被辅导员发现后,第二天上早课时每个人被处罚打了20个手板,这其中也有尼克松。从此之后他们再也不敢违犯了。这个习惯一直延续了好久,直到尼克松上大学时才改掉。
教会学校的学习生活虽然枯燥无味,但是环境却是清静幽人。它坐落在一个小山岗旁,地势颇为有趣,沿着岗子上的小路往上走,整个山谷便尽收眼底,四周是一些农家的住屋、仓房和场院。这美丽的景色又引起了小尼克松绘画的兴趣,有的时候他就坐在离学校不远的空地上,画天空,画小鸟,画白云。有一次,在一棵菩提树下,他看见了一个约摸只有4岁的小男孩,盘腿席地坐在不远的坝子上,怀中搂着个半岁光景的幼儿。他用自己的双腿和胸部,给自己的弟弟做了一个安乐椅,那小弟弟静悄悄地坐着,一对黑眼睛却活泼泼地瞅来瞅去。不一会儿,小尼克松便完成了一幅布局完美、构图有趣的素描画,那其中掺杂着他对克莱德曼妈妈的怀念,对自然的向往和对家人的思念。因为那情景使他想起了自己的小弟弟阿瑟。
将近一年的教会寄宿学校生活,使小尼克松尝到了远离亲人的痛苦,同时他最大的收获是增添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许多年后尼克松曾为此事说过一段话:“只有自然,才是无穷丰富的;只有自然,才能造就伟大的艺术家。对于成法定规,人们尽可以讲许多好话,正如对市民社会,才可以致这样那样的颂词一般。诚然,一个按成法培养的画家,决不至于成为一个讨厌的邻居或恶棍;但是,另一方面,不管你怎么讲,所有的清规戒律,统统都会破坏我们对自然的真实感受,真实表现。”
尼克松虽然在后来没能成为一个画家,也没有一张成名的画,但那一段教会生活的确使他幼时的画技和对自然的热爱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在还有将近半年就要小学毕业的时候,尼克松的父母决定把他接回家,继续在惠蒂尔小学读书。原因是尼克松的弟弟唐纳德在操场上摔坏了腿,每天上学放学必须得有人接送,而尼克松父母因为照顾小杂货店而无法分身。如果尼克松能回到惠蒂尔小学继续读书,那么唐纳德便会有人照顾了。
尼克松返回惠蒂尔小学,继续他还有半年的小学生活。
虽说宗教信仰和祈祷是尼克松家庭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每一个孩子几乎都被从小就灌输了宗教内容,但是似乎每一个孩子对宗教都不是很感兴趣。
特别是尼克松,虽然在教会小学呆了近一年的时间,每天接受严格的教会式的教育,但是他却始终不能够按父母的意愿把心思放到那上面去。
虽说母亲最初的愿望是希望温文儒雅的尼克松做一个教派的圣徒,一个标准的传教士,但是尼克松并没有按母亲的话去做。他只是对读书萌发出了最大的兴趣。尼克松家是一个开明家庭,既然这样,父母也不勉强,因为这些基本上属于个人的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尼克松以后的求学时代以及从政时期,他演说时从来没有引用《圣经》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生活在一个如此信仰宗教的家庭,他没有热衷于宗教真是怪事。
在后来的从政期间,他反对其他政党中政治上显赫一时的宗教盲信者。他坚定地信奉宗教与国家截然分开,他认为混淆宗教与政治是极其危险的。他认为作为政府官员,不应该干预宗教事务,教士也同样应该避免就政治的问题而传道。尼克松认为,即使像奴隶制和人类平等这样的道德问题也不是传道的合适题目,但是他在任总统期间曾以宗教和道德的理由反对妇女流产。这虽然曾引起当时一些性解放人士的大力反对与攻击,但是却受到教会的欢迎与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