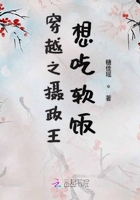凌少桀对付国公府侍卫同时朝章庭湮低喝一声:“敢跑,那个男人便会为你付出代价!”
那个男人,无疑是指季长安。
季长安固然是绑定她的一个好筹码,但章庭湮更加知道,她还远没有季长安重要,凌少桀根本不会因为她,在两国战争一触即发时,杀掉对他有莫大益处的安乐侯世子。
“你把这些侍卫们全部打退,我才服你!”章庭湮深知对于凌少桀这种男人来讲,请将不如激将。
他最好能和国公府撕开脸面。
章庭湮没有必要,对残害她双亲的皇室、与想置她于死地的赵氏持一分仁慈!
诚如她所想,凌少桀是个自负的人,他似乎想在章庭湮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果然就和侍卫卯上了。
人越积越多,把他们两人围得密不透风,凌少桀很快已被逼入颓势,匆忙中,一名侍卫一刀削在凌少桀左臂上,凌少桀躲闪不及,叫那一刀划出一道血口。
“住手!”后一步来到的侍卫统领认出了凌少桀,吓得面如土色,立刻喝停侍卫们,跪在凌少桀面前请罪:“小人不知太子殿下驾到,小人罪该万死!”
说完那首领拔刀出鞘,一刀砍下那名误伤凌少桀的侍卫。
房顶上的打斗惊得整个国公府惶惶不安,尊华夫人与赵琛见凌少桀受伤无不心惊胆战,凌少桀和章庭湮跳下房顶,尊华夫人走在赵琛之前,惊心地打量着凌少桀,泪水涟涟:“殿下伤得这么重,叫我国公府何以赎罪啊。”她慌得不知如何是好,眉眼里的担忧似要溢出来,“我一定要将今晚负责守卫的侍卫们,全部处死!”
凌少桀站在尊华夫人面前,尽管受着伤,但不减他姿容一分美感。
“夫人言重了,他们罪不致死,是本宫不速而来,侍卫们为国公府抵御外来者份所应当。”他平淡地道:“该是本宫向您道歉,本宫为了抓捕逃走的太子妃才进来国公府,也请您见谅。”
尊华夫人眼光看向章庭湮,刚才在凌少桀身上的怜惜与紧张,到了章庭湮身上时,便是阴森与诡秘了。
“不知太子妃因何事而离开东宫?”
章庭湮身上一冷,笑眯眯答道:“跟殿下之间的一些琐碎事罢了,说句见外的话,夫人您不便打听。”
“你怎么能如此说话,本夫人身为一品诰命,你……”
不等尊华夫人搬家底,凌少桀淡淡地向尊华夫人道:“她说的没错,本宫与太子妃家事,怎容外人打听。”
一句话说得尊华夫人直逼红了脸,尴尬地道:“我也是关心殿下,请殿下恕罪。”
“夫人今晚,是在为您次子过生忌?”凌少桀问道。
尊华夫人面上似在遮掩,“正是。”
赵琛见场面局促,忙道:“殿下受了伤,快请屋中坐,已让人去喊大夫,马上就能过来。此事在国公府发生,臣罪无可恕,纵然殿下原谅,臣明日也自当向皇上请罪。”
凌少桀未言,带着章庭湮走向主屋,尊华夫人紧张地移步拦下,委婉地道:“祭祀不吉,请殿下前去厢房。”
“夫人多虑了,本宫百无禁忌。”凌少桀弯唇,笑中有隐隐邪气,他不顾尊华夫人的婉拒执意前去。进到主屋时,原本在屋中诵经的尼姑站成两排,纷纷向凌少桀合十,颔首示礼。
这个生忌过得很简单,只有香案上一份寿面,以及十多位出家人,对于赵氏豪族而言,这甚至算得上寒酸。
一个大胆的猜测在章庭湮脑中生成,不由又惊得她一身冷意。
凌少桀坐在主座上,任大夫将他伤处包扎,一旁的尊华夫人和赵琛仍在频频致歉请罪,凌少桀却都充耳不闻,看起来颇失神。
凌晨时分离开国公府,章庭湮自知无路可走,也就老实跟着凌少桀回往东宫。
她提出去刑部看哑嫂,凌少桀却以哑嫂之死事关重大,要她避嫌为由拒绝了她的提议。
意料之中的说辞罢了。
大战前夕,东卫京都却不见丁点紧张气氛,这种现象反映的并不是京都防卫懈怠,而是显示了东卫的绝对自信,即使战事将起,京都仍未受到丝毫影响。
章庭湮不禁抽一口冷气,东卫国内的团结远是天裕不可比拟的,如今的天裕千疮百孔,安乐侯世子又身陷东卫成为天裕国软肋,这一场仗,天裕国取胜艰难。
遐思间,想起母亲留给她的那封遗书,想到哑嫂的死去,想到赵国公府的插手,再想到尊华夫人家次子的生忌……
东宫,一间位于废殿的封闭房中,季长安抬起被凌碎头发遮住的眼眸,挣着双手上紧绷的铁链,恨恨地看向那扇紧紧锁闭的铜门。
门外有说话声,熟悉,刺耳。
“我答应过我,只要我配合东卫,你就不会伤他,他已经身中逍遥散,为什么还要把他锁起来?”
“听侍卫说他不乖,他的情绪很不稳定,为防止不必要的伤害,本宫自认如此甚好。”
“当朝储君言而无信,何以治理江山?”
“你质疑本宫的江山,那便留在本宫身边,本宫证明给你看!”凌少桀声音恶怒:“你对季长安的担忧,只会让他活得更加痛苦,所以你想好,要如何与本宫说话了么?”
“我以为你至少有一点君子风范,你越是对他充满恨意,越是让我觉得你很无能。”章庭湮被他的出尔反尔激怒,斗兽场过后,她答应要将所知道的天裕国情相告,包括卫皇和凌少桀都无比看中的军事分布图,而她的条件,是要凌少桀善待季长安,她以为尽管季长安得不到自由,但至少不应像狗一样被上着锁,困在废旧脏乱的房子里!
“本宫无能?”这应该是凌少桀自打出生以来,所听过的,最好笑的话了吧,“不用激本宫,你可以更放肆了一点,反正本宫不会杀你,更会留着季长安。但本宫可以决定,让你们用什么方式活着。”
“我从没想过能活着离开你的视线,”章庭湮逼近凌少桀,抑下声音,一字一顿:“但你别以为,你的路就一定会好走,当心被捧得越高,便摔得越惨。”
凌少桀眉心紧蹙,眼中有着露骨的危险讯号,“把话说清楚点。”
章庭湮却忽视凌少桀的疑惑,“等我见过季长安,自然会跟你说。”
凌少桀疑虑更深,他直觉章庭湮并没有在故弄玄虚,她一定是掌握着某些关键信息,比如昨天,她在张府与哑嫂的一见。
“关于昨日事,你确实该给本宫一个交代了。”凌少桀眸光深沉,示意侍卫打开铜门。
铜门一开,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季长安双手被缚、头发凌乱的颓姿,但他的一双眼,现出章庭湮从未见过的阴冷、狠戾与狂躁。
那种只能在她身上才能体现的温柔,她永远地,求而不得了。
这样的判若两人的季长安,令章庭湮心头一痛,她忍住哽咽,轻轻关上铜门,生怕这刺耳的摩擦声会令季长安心情更糟。
他们楚河汉界,隔阂如天堑,从之前的无话不谈,之前的出双入对形如一人,到今天的彼此成仇、相见无言,他们都在冰与火的洗礼中挣扎,苦不堪言。
她放弃了准备好的很多抱歉,他也不再对她有半句质问,他们坦然接受了对方立场,想透了,就没什么。
既然是敌人,那就恨吧,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章庭湮默默走近他,不顾他随时会爆发的危险,毅然拿出藏在怀中的小梳子,帮他打理乱糟糟的头发。
她梳得极轻,这柔和与耐心,她连对自己都不曾。
他默默接受她的好意,冰狠的眼神渐渐软下来,多了几分凄然。
“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见你了,”她声音极轻,轻得令人不忍耳闻,“我应该和他赌一局,输也不要紧,高低就只有这条烂命了,若能赢,兴许就是转机。昨天我见过一位旧人,那时我才知我应该身在一个怎样立场。”
她的父母若是死在卫皇屠刀下,她将不会再对东卫寄一分感情,不仅无感,还要尽己所能地让他们都不得安生。
季长安拳头微微握起,带动手上的铁链啷啷响动。
“你就只听着好了,”章庭湮靠向他的背,之所以这么近,是因为她不想她的话,被不知安排在哪的侍卫偷听,“你说我左右摇摆,立场不坚都不要紧,从昨天开始,我已不再是那个傻子。”
季长安眼神一动:章庭湮想投靠天裕国?
“我唯独放不下你,就算太子肯放我,卫皇不会认同,我注定只能来个鱼死网破了。”
“哼,”季长安低诮一声,惜字如金地开口:“若鱼死,网仍旧没破么?”
章庭湮脸上闪过一丝惊喜,忙低声道:“我会得到一个结果的,你要相信我。”
“是什么东西,让你自信有那么一条路?”季长安嗤笑,“和太子赌,你岂非找死?”
“我别无选择,”她抚着季长安头发,一点点将打结的发丝梳开,笑着向季长安道:“但也不是没希望的,你别替我担心。”
季长安笑笑:“你想多了,我何曾在为你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