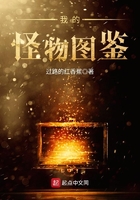这个孤据一隅的小村子名叫黑水村。村落实在是小,总共不过七八十户人家,并且,其中有很多户就只剩下了行将就木的老人。但听冯婆婆说,从前,这里曾经是方圆百里最大最热闹的村庄。
冯婆婆就是白水灵寄宿的人家里的那位老婆婆。
那么,黑水村究竟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的冷清呢?白水灵很是好奇。但冯婆婆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
天色终究完全归于了黑暗,一入夜,本来就寂静的小村落更是安静得有点可怖。雨已经停了,所以,就连淅淅沥沥的雨声都消失了。吃过晚饭后,冯婆婆早早的就去歇息了。白水灵一个人坐在堂屋里,和母亲通过电话之后,便有些百无聊赖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了。
怔怔的发了一会儿呆,她站起身来走到屋里那台老式电视机前,抬手将其打开。好多年没见到过这种旧式的电视机了,小小的屏幕,连遥控器都没有,要换台的话还得伸手在电视机上面按按钮。屏幕上,一片雪花,劣质音箱里发出沙沙的嘈杂声响。咔咔的按了几下换台按键,只能收到两个电视台,并且其中一个还十分的模糊,连画面中人的面容都看不清楚。而另外一个虽然能看清画面,却听不到声音。白水灵正准备将电视机关闭,突然间有细细的乐声响起,能听到声音了吗?再仔细一听,声音却不是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似乎竟是从屋外传来的。
白水灵走到门口抬手打开门,循声望去。声响是从村口处传过来的,好像,是在那座贞节牌坊底下?雨后的夜晚,起了一层淡青色的蒙蒙的薄雾。雾气氤氲中,牌坊下似乎有人身着戏服翩然起舞。长长的惨白的水袖,挥起来了,又垂下去了。那戏子袅袅婷婷,边舞边唱:
……连就连,你我相约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尖尖细细的女声,幽怨寒凉。这个村子里有人是学唱戏的吗?还真是勤谨刻苦。可是这个时候在外面唱戏,会不会有扰民的嫌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却见青衣戏子的身影飘忽不定,时而隐入黑暗中,时而又挥舞水袖显现在牌坊底下。声音也是若有若无,忽远忽近。这场景,怎么看起来有点诡异?白水灵忍不住打了个寒噤,收回探出去的半个身体,关上了屋门。
因为白天开了一天的车,身体累得狠了,所以白水灵的脑袋一挨上枕头,就开始迷糊了。不多时,她就睡了过去。身处陌生的地方,她睡得并不安稳。朦胧间,村口那个唱戏的女人似乎一夜未停,时不时就有一两句唱词钻进她的耳朵。害得她连做梦都梦到坐在台下看戏,台上的戏子咿咿呀呀的唱着,惨白的一张脸,偏偏两颊抹得血一般的红。唱着,舞着,一晃眼,戏台却又消失不见了。在她眼前,是一片荒草漫漫的山坡。寒风萧瑟,乌云覆盖了天空,灰败的枯草在风里摇来晃去。然而枯黄的草地里竟有一小块地方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一个身穿戏服拖着长长水袖的女人从红花里冒出半个身体来,披散的黑发中露出一双僵冷的眼,定定的望着她:“你回来了?”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白水灵只觉得头痛欲裂,摸一摸额头,有点烫手。可能是因为黑水村里的温度比之其他地方要低很多,她一时不能适应,感冒了。询问了一下冯婆婆,这个小小的村落里只有一家售卖油盐酱醋的杂货店,没有药店。冯婆婆拿出了一小袋头痛粉给她,里头装着指甲盖大小的一撮白色粉末,味道苦涩极了。尽管味道很差,但效果似乎不错,服下去没多久,她的头就不那么痛了。
吃过早饭,和冯婆婆聊了一会儿天,她走到屋外散步。雨虽然停了,太阳却没有出来,天色阴沉沉的。旁边一栋房屋的大门前,一个小女婴坐在学步车里咯咯的笑,一脸的欢欣灿烂。然而,守在一旁的看起来是婴孩母亲的女人,却是满面愁容,心事重重的模样。她手里拿着一个拨浪鼓,时不时的摇两下。咚咚咚,咚咚咚,欢快的响声敲不平她眉间的皱褶。
慢慢的踱到村口的贞节牌坊底下,这个时候白水灵才有闲心细细观看它。它足有七八米高,四五米宽。经年累月的风吹日晒让牌坊上面的雕刻模糊了,但还是能够看得清楚。门楣上头分别刻着“冰清、玉洁、竹香、兰馨”一共八个大字。另外,还用小字镌刻着一篇表彰节妇的碑文。粗略看了看,内容无非就是说黑水村有位齐魏氏,二十四岁时死了丈夫,她坚贞守节,赡养双亲,抚育儿女,一生不曾再嫁。为了表彰她的节烈,吏部上奏皇帝,诰封建坊,以此弘扬贞节,教化百姓。
短短一篇碑文,道尽一个可怜女子的一生。她是不是自愿的并不重要,反正,鲜活的面容,绚丽的青春,都已经埋葬在这座贞节牌坊之下。鲁迅先生都说过,“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才要表彰他。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才要表彰他。”
长长的叹息了一声,白水灵离开贞节牌坊,往村子里面走去。途经一棵老榕树时,她看见,树下坐着一位非常老的老人。他可真是老啊!头上只剩下稀稀疏疏的几根白发,脸上的皱纹重重叠叠,找不出一块稍微光滑点的地方。他干瘦的手里拿着一根旱烟袋,正眯着眼睛,吞云吐雾。
白水灵从老人的身边走过,被浓烈的烟雾熏得抬手掩住了鼻子。老人在身边的大石头上磕了磕烟杆,抬起头来看向她。而后,他咧开缺牙少齿的干瘪的嘴,对白水灵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她最后一次唱戏的时候,唱的是什么?”
“什么?老人家,你在跟我说话?”白水灵停下脚步,一头雾水的望向老人。
老人没有回答白水灵的问话,自顾自的说道:“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我却还记得清清楚楚啊……”他拍着膝盖沙哑的唱了起来,“连就连,你我相约定百年。哪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唱完了,老人放下烟袋,嗬嗬的干嚎起来,边嚎边含糊不清的说着:“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戏台高呢,我藏在大人身后,一直跟在后头看。那一路流下来的血哟,后来怎么洗都洗不干净。男人,女人,都眼睁睁的看着,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她求情。作孽啊,作孽啊……怨不得她要诅咒这个村子啊,所有的人都眼看着她流干血,耗尽命。她心里苦啊,她心里恨啊……”
老人的话让白水灵只觉得莫名其妙,且毛骨悚然。这个人是不是不正常?她不敢再多加停留,抬起脚匆匆离开了此处。身后,老人嚎哭了一阵,又开始嘶哑的唱了起来:“弯眉毛嫩脖子,水水的眼睛哟,香香的唇,坟上的红花多茂盛。你舞的是血和肉,我见的是白白的骨,白白的骨……”
这人肯定是个疯子,白水灵笃定的想到。她此时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那棵老榕树,但那老人的声音还能依稀听得到。沿着石板路又朝前走了一段,才彻底听不见了。
这个村子实在是冷清得过分,她这一路行来,只遇见了两三个人。个个阴沉着一张苍黄的脸,比这阴冷的天气还要令人不快。唉,真想早点离开这里啊,也不知道毁损的道路什么时候才能修葺好。听冯婆婆的意思,再怎么也得等上好几天。为什么就这样的没有效率呢?想一想,自己也真够倒霉的……
走着走着,前方出现了一座破旧的庙宇。大门只剩下了半边,院墙也塌下来了一截。从坍塌的泥墙口子处望进去,空旷凄冷的场院里,有座古旧破败的戏台。看上去,很多年没有被使用过了。情不自禁的,她抬起脚走了进去。
一步步接近戏台,不知怎么的,她逐渐的恍惚起来。朦胧中,那朽败的戏台竟然焕然一新,红红的灯笼亮了起来,鲜丽的彩绸挂了起来。台子底下坐满了人,巴掌声和叫好声响成一片。戏台上,青衣花旦款摆柳腰,曼转秋波,水袖飞扬,启声唱着婉转悠扬的调子:
……往生不来,背影常在,害了相思,惹尘埃……夜雨恶,秋灯开,照亮空空舞台……谁等谁回来?……该来的,都不来,该在的,都不在……
唱完了,笑完了,花旦抬起袖口遮住了脸。再次放下来,一张妍丽鲜艳的面孔变成了死白色。死白一片中,一双僵冷的眼睛定定的望向神情恍惚的白水灵,张开染着血一般的红嘴,说道:“你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