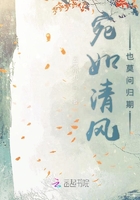贺桩听他这话,清丽的眸子剜了他一记,半晌才道,“不许!”
王锋方才被卫良和训了,但一碗绿豆汤下肚,仍旧败不下火,气得把碗重重摁在案上,“大哥,姓柯的在桂城就对咱们下手,如今小夫人怀着身孕,您若再不反击,只怕他会欺负到夫人头上。”
卫良和也放下碗,想来不与他分析一番其中厉害,王锋是不会懂的,语重心长道,“老王,大哥知你心里委屈,这些年你跟着我,我也是记着的。可你当真以为圣上对当年之事一无所知?”
此话一出,便是焦实禄也极为震惊,“当年将军与北燕的裕王在凌云鏖战,世人只知您大伤裕王,却也被他一剑刺下悬崖,生死未卜。难不成还另有内情?”
卫良和只苦笑,浓黑的眉毛微微皱着,“焦先生何时听说,双方交战,一方的将军没了,还能胜的?”
王锋一想到那卑劣的柯景睿,便狠狠啐了一口,“当年,将军伤了裕王不假,往后几年北燕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也只因他们的裕王爷伤势尚未痊愈罢了。而将军坠崖却是拜柯景睿所赐。一回两回地只会捡漏,他也不嫌丢人!”
孟氏立在门侧,仔细琢磨着方才卫良和的话,“此番内情诸位也都知,只不过,听侯爷方才的意思。柯将军当年狼子野心,莫不是受了谁的提点?”
此事极为隐秘,知情人甚少,且过去多年,许多痕迹线索早被抹得一干二净,卫良和也不大确定。
只不过自打他清醒以来,骨子里的东西未变,却是想得深远了些,“那两年宸王被幽禁,本侯久居边关,不懂朝政漩涡,只觉咱们的皇帝昏庸无道,宠信奸佞,便大肆屯兵。本想等着有朝一日宸王改变主意,来个反扑逼宫,想必圣上早对比颇为忌惮,恨不能削了手头的兵权!”
“将军一心为皇家稳固江山,皇帝却是这般千防万防,难道就不怕寒了将士们的心?”王锋义愤填膺道。
卫良和冷漠一笑,脸上已有了严峻的眼色,“咱们的这位圣上,素来疑心重,又想顾全自个儿的颜面。一旦觉得谁动摇了他的皇位,自然赶尽杀绝!”
“可您当年也是钦定的大驸马呀!”王锋委实震惊,听着卫良和的话,细细想来,也有几分道理。
就凭柯景睿,他还没那个胆儿,可打凌云一役后,他便平步青云,皇上甚至还亲赐了长公主给他!
卫良和累了十年的赫赫军功才挣得的名头,他仅凭一役便唾手可得!
何辅瞧见卫良和脸色不对,暗道这王锋在桂城冯家当屠户久了,脑子也越发不灵光,明知将军不喜大驸马的名头,生怕伤了小夫人的心,他还往剑刃上撞!
只道,“圣上连自个儿的亲骨肉都不放过,宸王被幽禁八载,何况将军一介外人?”
焦实禄点点头,又道,“不过王副将话糙理不糙,将军再不寻思着反击,大驸马只会以为咱们怕了他,别闹到最后,伤了咱自个儿的人。不过,他背后既有皇上与萧王撑腰,此事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此话算是说到卫良和心坎上了,若是旁的倒也还好,他终究放心不下贺桩。他也不说话,只回眸,淡淡笑着,望向何辅。
何辅登时会意,也笑道,“焦先生请放心,柯景睿以为把桂城知府任知荃灭口了,便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底罪证。殊不知,军务处的账本早被在下偷偷换了,就等将军发话!”
王锋心急道,“那还等什么?赶紧呈上去呀!”
“稍安勿躁,先让他得意几天再说!”男人运筹帷幄道。
暮色将至,长公主府前一派肃静,大门前已是扫得干干净净。
管家正领着一群下人恭顺地候在门侧。
未几,只听遥遥传来一句铿锵有力的长吼,“迎大驸马回府!”
只一会儿,只听铁蹄敲在青石之上“嘚嘚”作响,垂首的官家只见那一只只健硕的马腿之上,沾满泥尘,再往上,便是将士们墨色的军袍,正随风悠悠轻扬。
一众下人齐齐跪地,齐声道,“恭候大驸马大驾!”
“起来吧!”随着一声低哑雄厚的嗓音,官家起身抬眸,只见一支二十余人的黑骑兵,皆是神色肃穆,身姿挺拔如苍松,气势刚健似骄阳。
为首的男子身躯凛凛,小麦色的健康肤色。相貌也不差,一双眼光射寒星,刀削的眉,高挺的鼻梁,薄薄却紧抿的唇许是久经风沙,颇有些干裂。
此人,便是当今的大驸马,柯景睿!
柯景睿沉默地扫了一圈立在门前的下人,却是不见他希冀的那抹身影,眸子里不由闪过一丝凉薄之意。
想他几度征战杀伐,离上次回京述职,已是整一载,她却是从来不闻不问,一封书信也不见!
她还是放不下那人罢?如今那人已回了京,她是不是该旧情复燃了?
思及此,柯景睿心底愈加不好受,连带着脾气也来了,猛然翻身下马,随后把马鞭一扬,大跨步往里头走。
管家堪堪接住,小跑着跟上,“驸马爷舟车劳顿,不若好好洗洗?老奴已命人为您备了热水……”
柯景睿登时停步,管家差点撞上,堪堪刹住脚,却又听他问,“她呢?”
她,自然指的是长公主容萱。
管家也知大驸马不见长公主出府迎接,心头不痛快,只道,“公主这几日正病着,夜里凉,奴才便私自做主,不敢劳公主出府……”
病了?
柯景睿不由冷哼,他可是时时注意着神侯府的动态,听闻那人的妻子有了身孕,她心里不好受罢?
他再度大跨步,见管家还跟着,只道,“行了,别跟了!回去好好招呼府外的几个兄弟!”
柯景睿还真猜对了,容萱自那日隐约猜到贺桩怀孕,心里一时堵得慌,甚至失态到无法顾全皇家颜面,如同妒妇一般与贺桩撕破脸面,回府后心头仍旧阴郁,这阵子寝食难安,人也越发懒散。
五月里热得慌,她闷出了一身汗,索性命下人抬来热水。
屋里头空寂得很,她的夫君今日回京,她是知晓的。不过,想必他还得进宫一趟,便只着了一件纱衣出来。
正厅里传来碗筷磕碰的声音,她甩甩头,起先以为是幻觉,直到重重“哐叽”一声,着实吓了她一跳。
她扭头,只见一件沾着尘土的盔甲,安安稳稳地躺在洁白的贵妃椅上,随后,更衣室里传来脱鞋的声音,未几,在她晃神之际,一抹袖长疲惫的身影隔着珠帘,映入她的清眸。
乱七八糟的披风,脏到透顶的外袍,男子的衣领也是翻折着,但仍旧难掩其出色的容貌。
容萱怔怔望着,目光停留在那风尘仆仆的脸上,一时忘了挪步。
而珠帘之内的柯景睿,也早就发觉她的存在,只不过仍旧继续手上的活儿,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冷冽的漠视。
夫妻二人,没有任何礼貌的招呼,是淡如清水?还是情到深处不知如何开口?
室内静得离谱。
柯景睿这半月来忙于赶路,饿得很。他也懒得招惹她,径自坐在桌前,端起碗,大口大口地扒饭,夹菜的动作极大。
容萱总算回过神来,默不作声地撩起珠帘,在他对面坐下,见他吃得急,便倒了一杯水挪到他面前。
她的主动示好,柯景睿都倍加记着,手上微微一顿,继而腾出一只手来,饮下那杯毫无味道他却觉得清甜的白水。
“听管家说,这几****病了?”男人悠悠开口道。
容萱望着他,语气仍旧淡淡的,“嗯,前几日来了葵水,今儿身子才干净。”
柯景睿放下碗,瞧着她温静如水的模样,这哪是妻子见到久不归家的丈夫的神态?
他登时火上心头,一掌将玉箸拍在案桌之上,惊得容萱花容失色,只听柯景睿冷笑道,“莫不是旧情人回来,瞧见人家夫妻恩爱,心里头难受,却拿这般烂借口敷衍我?”
“你什么意思?”容萱顿时气得浑身发颤,站起身,她心里头本就有怨,可终究也只能藏着掖着,他又何必撕破脸面,在她伤口上撒盐?
“怎么?正中下怀了吧?”柯景睿亦站起,居高临下地睥睨着她,笑得残忍。
容萱见他舟车劳顿,不欲与他多说,只道,“你先用膳,好好歇息吧。”
言罢,便紧了紧身上的纱衣,转身回房,手却被他死死扣住。
容萱用力抽回,却拧不过他。
柯景睿只需一施力,便牢牢将她锁在怀里。
仔细盯着她的鹅蛋脸,粗糙的手抚上日思夜想的容颜,见她满是鄙夷,忽而笑道,“我仔细瞧着,你这眼角都有鱼纹了。你说,那人如今娶了个年轻貌美的小夫子,还会不会惦记着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