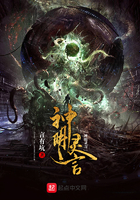太后瞅着炕几上的茶盏,视线顺带着就瞧到了玄烨的头顶,肚子里想说的话就说不出来了。
再过几年玄烨也要五十岁了,也是爷爷辈的人了,都快要成祖爷爷了,再给玄烨说个女人,还是个快四十岁的女人,太后真觉得说不出口了。
要是在普通人家,玄烨的年纪是可以说续弦的年纪,找个门第差不多的那也是找个媒婆来说了。玄烨不是普通人家的当家的,也没有皇后,可是还有四位相当于侧福金的妃子、俩位嫔呢。
太后真觉得这话不好说了,托娅的年纪摆在了那里,提出来似乎有些委屈玄烨了。这么多年都没让玄烨动了心,现在再塞给玄烨,若是年轻的能生产的也就罢了,现在托娅这个年纪怕是已经生不了孩子了。
这么想着,太后就觉得把娘家堂妹往玄烨那推有点心虚了,没了面子般,好像娘家堂妹比别人矮了半头,过去不觉得,现在真就这么觉得了。
等玄烨提出了要为太后的六十岁大寿庆祝,册封下后宫,太后就没有把托娅提了出来,按着玄烨的意思同意册封霁兰,只是还压了下,把瓜尔佳氏册为和嫔排在了霁兰前面,又把孝懿的妹妹佟氏封为贵妃。
看着那根马缰绳,托娅听到这些时已经没有了感觉。来安抚托娅的苏茉儿搓着两只手没话找话般地说了句:“这地火烧得还旺……”
“可不,这宫里还是挺冷的。”托娅说了这么一句却一下让原本温暖如春的屋子里结上了冰,冷煞了起来,冻得苏茉儿坐不住,早早地走了。
瞧着紫檀木榻上那根马缰绳,托娅不知怎么眼泪就滑了下来。这个年纪了,什么亲热的事也不是那么想了,就只想着能让主子握下自个儿的手,说两句家常的话,对着自个儿笑一下就成了。
原来这么个念头也是痴心妄想,难不成自个儿就不能跟主子并排坐在一张床上?为什么太后这些人全想着是别的?
托娅觉得冤,自个儿能生的时候,为什么旁人看中的身份;到了如今,自个儿就像一个已经可以扔到旮旯角里再也没用的布头了。
托娅瞧了瞧手里的布头,怎么着弄弄也能做出个荷包,原来自个儿还不如这个布头呢。
蒙古的几位老福金来北京了,玄烨特意让托娅也去了。坐在那里,托娅的身份真是尴尬,不是玄烨的后宫女子,只是一个寄居在玄烨后宫里的蒙古表妹,还是一个过了花季年华埋了半截子土的蒙古表妹。
老福金尴尬地笑着,随便扯着话,却不敢看托娅,仿佛多看一眼就让托娅再多一份可怜一样。
托娅忍着,脸上的表情是不变的那抹淡淡地笑,好像没人事般,却不知早觉得身上的那张椅子上已经布满了钉子,扎得实在是要坐不住了。
这就是汉人说的“如坐针毡”,托娅这么想着,到底是四十岁的女人了已经不能跟小姑娘般发作,只能忍着,忍到离开了蒙古福金。
隐隐从身后还是听到了几句:“怎么还是格格……”
“怪可怜的……”
“这么久,都没有得到主子的宠幸?”
“怕,是有缘故吧……”
托娅步子没有乱,听多了就习惯了吧。到底还是因着是宫里,大家全把心里想说的话藏了起来,若是在宫外,在草原上,怕更难听的话都有吧。
康熙四十九,是太后的七十大寿,托娅已经什么也不指望了,想着该有指望的还是那个女人吧,手里做着的荷包上扎上了一针,像是又给自个儿再上了个无关紧要的紧箍咒。康熙四十八年,几个阿哥封亲王、封郡王、贝子的都有,只有那个人的儿子还是贝勒,玄烨不补偿下那个女人吗?
托娅没有想到自个儿可以这样心平气和地关心着那个女人,甚至连她的儿子也关心上了。一直没有消息,托娅倒长叹了口气,好像白这么操心费神了。
没多久,托娅知道霁兰病了,心里倒有些觉得因为自个儿的缘故,那个女人和儿子才让太后和自个儿的哥达尔罕亲王班第额驸圧制住了,才会这样什么也没有了,不然位份和爵位也应该往上升升的。
托娅的亏欠内疚还没几天,就听到说玄烨给霁兰家抬了旗,虽说没有从辛者库抬到正身旗人,可是却已经放到了包衣。
抬旗,那可得有了功劳才成。像胤禛的侧福金年氏家,从下五旗的包衣抬到镶白旗,成了正身旗人,那不过是因为顺治年间缺得就是识汉字的官,能识个字就给个举人。年家也就是因为识汉字才抬了旗能去科举。
那个女人家凭什么呢,就凭那个女人是主子心尖上的人吧。人病了,就给抬旗,好让人高兴下吧。托娅把手里的荷包再看了看,荷包做得再好,不是人心里想的,那也是没有用的。
再过了几天,就听到了玄烨跪在太后的跟前求着太后给霁兰从嫔升到妃。托娅把手里绣着的荷包多扎了几针,却全是缝错了,只能拆了再重缝。
看来自个儿是没有亏欠那个女人,托娅重新把荷包缝了起来,自个儿怎么可能会亏欠那个女人呢,这一生自个儿是都不可能了。
康熙五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天冷的要命,也干得要命,天阴着就是下不来雪,好像下了雪就错了吧,天死命在那撑着了。
托娅放下了手里的荷包,那个让自个儿不舒坦了几十年的女人这么走了,心里一下就空了下来。几十年了,一直惦记着那个女人今晚在哪睡,是乾清宫还是长春宫,是在紫围子里还是畅春园。突然不用再惦记了,托娅都有些茫然了,不知道日子再怎么过下去了。
跪在霁兰的灵前,这是玄烨要的,就连贵妃佟氏都跪了,死者为大。贵妃跪跪没有什么,可是都知道,这不一般,这是没封后,却要大家按着封后的规矩来行了。
那个女人的金棺抬出了紫围子,又在五龙亭摆了几天,出五龙亭的时候是破墙走的。一切瞧着好像全按着规矩,可一切全让人觉得不一般。
托娅就等着玄烨回来,想看玄烨会怎么个举动。站在太后的边上,看着玄烨给太后请了安,闲话两句就走了。不能跟着去,托娅却头一回让自个儿宫里的太监去打听了。
玄烨去孙文善花园给那个女人奠酒了,听到这个的时候,托娅不再恨了,又悄悄落了泪,好像得了个圆满一样。紫檀木榻上摆满了荷包,托娅苦笑了下,出身好的只能做一辈子的荷包,主子心尖上的才能让主子这么守了一辈子,死后去亲奠吧。
出身,其实不过是给那些贫家小户的人说的,给那些没得了主子宠主子爱的人一个安慰吧,其实一切全凭的是主子的心。孝庄文皇后、太后拦了一辈子又能拦住什么呢?
看看前面的董鄂妃,再看看今天的良妃,没在孝庄文皇后、太后跟前落好,可是在皇帝面前落好了,这对于女人才是最实在的吧。
到底还是明白晚了,若是早知道这些,怕自个儿的一生也会不一样了吧。托娅又拿起了荷包绣起来了,那个女人真得是这一生足矣。
托娅的日子越来越平静,每天绣荷包念经,就像是宁寿宫里的老太妃们一样。宫里的蒙古女人也越来越少了,能用蒙古语说话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
托娅送走一个蒙古女人,就会想一下自个儿的未来了。如今还有着太后在,托娅不用担心,可是太后不在了,这个尴尬的身份再待在宫里怎么说呢?百年之后呢?自个儿的棺椁葬入何地呢?
更何况外面的大臣嚷嚷说立储,宫里的嫔妃不能说这事,可也关心着各自的未来,谁都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下面的新皇会如何处置这些母妃呢。
托娅不是母妃,更有理由担心了,难不成新皇上去要把自个儿送回草原去?托娅唯一盼着的就是太后真能千岁千岁千千岁。
可太后到底是人,没能千岁千岁千千岁,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薨殂了。
托娅在大行太后的灵前真心哭得很惨,这宫里唯一的依靠就这样走了。虽说太后这位堂姐没能给自个儿强封个皇后,可至少有太后在,托娅在后宫里还是有个根底的。现在托娅就像是浮萍了,在这后宫里该怎么生存下去呀。
玄烨是给人架到太后灵前,双脚浮肿,走不了路,伤心之余,听到了嫔妃那边的哭声,看到了托娅……
兴许就是这样,玄烨在康熙五十七年给自个儿的女人们做了安排,排在封妃名单上第一个的是托娅,一个没有做过玄烨女人的女人。
跪在咸福宫门那听着册封文的托娅,心踏实了,四十年的不定,四十年的担忧,今天终于全定了下来,虽然开头那句“备位宫闱”何等辛酸,可到底主子还是给了自个儿一个名份。可以踏踏实实地葬入妃园寝,可以百年之后有人祭祀了。
不再担心的托娅到了康熙六十一年,玄烨驾崩的时候,都已经感觉不到了难过。四十多年,原来可以把一切全磨光的,也可以跪在那里装着悲痛,却偷眼打量着和妃跟胤禛的惊鸿一瞥,更能看到夜深人静时,胤禛走到了和妃的边上……
托娅笑了,原来男人都有错眼的时候……
乾隆元年八月初八日,托娅走完了她的一生,她看到了两次新帝的登基,也避免了胤禛问她“皇考圣祖有没有睡过你”这样的尴尬问题,托娅可以平静地进入景陵妃园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