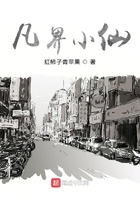五月的一个早晨,佳容北上了,她想凤来镇不可能像近来去的地方那样讨厌的,而且,尽管她对她那个姑妈和媚兰很不喜欢,她还是怀着好奇心想看看,从前年冬天战争爆发前她最后一次拜访这里以来,这个城镇究竟变得怎样了。
凤来镇历来比别的城镇更使她感兴趣,因为她小时候就听父亲说过她和凤来镇恰巧是同年诞生的。后来她长大了一些,才发现父亲原来把事实稍稍夸大了些,因为她习惯地认为一定夸张只能使故事变得更趣味,不过凤来镇的确只比她年长九岁,它至今她听说过的任何别的城镇比起来仍显得惊人地年轻,自己家周围有着一种老成的庄严风貌,一个个已经一百好几十年,更有甚者正在跨入它的第三个世纪,这从佳容年轻人的眼里看来已俨然是坐在阳光下安详地挥着扇子的老祖母了。可凤来镇是她的同辈,带有青年时代的莽撞味,并且像她自己那样倔强而浮躁。
尚武讲给她听的那个故事也有确实依据,那就是她和凤来镇是在同一年命名的,在佳容出世之前九年里,这个城市先是叫做小北村。后来又叫北巨城,直到佳容诞生那年才成为凤来镇。
尚武起初迁到千塔来时,凤来镇根本还不存在,连个村子的影儿也没有,只是一大片荒原。不过到第二年,国王授权修筑一条穿过新近割让的土地向北的路。这条路的终点是十分明确的,但是它的起点在凤来镇则尚未确定,直到一年以后一位师傅在那块土地里打了一根桩子作为这条路线的南端起点,这才确定下来,同时凤来镇也就正式诞生,开始成长起来。
在凤来镇亚那时还没有路,四周都是山,别的地方也很少。不过在尚武与雪乔结婚之前的那些年里,在水塔以北的25里处的那个小小的居民点便慢慢发展成一个村子。道路也在慢慢向北延伸。第一条路有了,于是第二条也就出来了。一条条的陆将凤来镇围了起来。
凤来镇由一条路诞生,也和它的路同时成长。到那四条干线完成以后,凤来镇和西部、南部和滨海地区连接起来,并且也同北部和东部连上了。它已经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冲,那个小小的村子已经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在一段比佳容17岁的年龄长不了多少的岁月里,凤来镇从一根打进地里的桩子成长为一个拥有上万人口的繁荣小城,成为全州瞩目的中心。那些老一点、安静一点的城市,总是用孵出了一窝小鸭子的母鸡的感觉来看一个闹哄哄的新城市。为什么这个地方跟旁的镇子那么不一样呢?为什么它成长得这么快呢?总之,它们认为它没有什么好吹嘘的----只不过有那些路和一批闯劲十足的人罢了。
在这个先后叫做小北村、北巨城和凤来镇的市镇落户的人,都是很有闯劲的。这些好动而强有力的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区和一些更远的地方,他们被吸引到这个以路交叉点为中心向周围扩展的市镇上来,他们满怀热情而来,在附近那五条泥泞土路交叉处的周围开起一店铺,他们在地脊上那条由当地人世世代代用穿鹿皮鞋的脚踩出的名叫桃树街的小径两侧,盖起了漂亮的住宅,他们为这个地方感到骄傲,为它的发展感到骄傲,为促使它发展的人,即他们自己,感到骄傲,至于,那些旧的城镇,让它们高兴怎样称呼凤来镇就怎样称呼去吧。
凤来镇是一点也不在乎的。
佳容一直喜欢凤来镇,她的理由恰恰就是人们诋毁它的那些理由。这个市镇像她自己一样是新旧两种成份混物,其中旧的成份在跟那个执拗而有力的新成份发生冲突时往往退居其次。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种对于这个市镇的个人情感上的因素----它是和她同一年诞生,至少是同一年命名的。
头天晚上是整夜的狂风暴雨,但是到佳容抵达凤来镇时太阳已经开始露出热情的脸来,准备一定要把那些到处淌着河流般的泥汤的街道晒干。车站旁边空地上的泥土,由于马车行人来来往往,不断塌陷搅拌,快要成一个给母猪打滚的大泥塘了,也时常有些车轮陷在车撤中的烂草里动弹不得。大车和救护人员川流不息,忙着装卸由后方运来的给养和前方的伤员,有的拼命开进来,有的挣扎着要出去,车夫大声咒骂,骡马跳着叫着,泥浆飞溅到好几丈远,这就使那一片泥泞加一团混乱的局面变得更糟了。
佳容站在车门口下面的那个梯级上,她穿着黑色丧服,绉纱披巾几乎下垂到了脚跟,那纤弱的身材还是相当漂亮的。
她犹豫着不敢走下地来,生怕泥水弄脏了鞋子和衣裙,便向周围那些扰攘拥挤乱成一起的大车、和马车匆匆看了一眼,寻找自己的姑妈,可是那位胖乎乎红脸蛋的太太连个影儿也没有,佳容感到焦急万分,这时一个瘦瘦的花白胡了的老头,手里拿着帽子,显出一种庄重不凡的气度,踩着泥泞向她走过来。
“这位是佳容小姐吗?俺叫老福,媚兰家的马车夫,你别踩在这烂泥地里。“他厉声命令着。因为思佳正提起裙子准备跳下来。“让俺来驮你吧,你跟你姑妈同一个毛病,像小孩似的不怕弄湿了脚。“他尽管看来年老体弱,却轻松地把佳容背了起来,这时,瞧见林茜怀里抱着婴儿站在梯台上,他又停下来说:“那孩子是你带来的小保姆吗,佳容小姐?她太年轻了,看不好力柯先生的独生婴儿呢!不过咱们以后再说吧。你这小女儿,跟俺走吧,可当心别摔着那娃娃。”佳容乖乖地让他驮着向马车走去。一面不声不响地听他用命令的口吻批评她和林茜。他们在烂泥地里穿行,林茜嘟着嘴一脚泥一脚水地跟在后面,这时佳容回想力柯说过的有关福伯的话来。
“他跟着父亲经历了故乡的全部战役,父亲受了伤他就当看护----事实上是他救了父亲的命。福伯实际上抚养了我和媚兰,因为父母去世时我们还小呢。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姑妈同她哥哥我的叔叔发生了一次争吵,所以她就过来同我们住在一起,并关照我们了。姑妈是个最没能耐的人----活像个可爱的大孩子,福伯也就是这样对待她。为了明哲保身,她事事都不作主,要由福伯来替她决定。我15岁开始拿较多的零用钱,那就是他决定的;当福伯主张我去学堂时,也是他坚持要我到去念的。他还决定媚兰到一定年龄就盘头发并开始参加舞会。他告诉姑妈什么时候太冷或下雨时不宜出门,什么时候该戴披巾。……他是我所见过的最能干的老头,也可以说是最忠心耿耿的一位仆人,唯一不幸的是他把我们三个连精神带肉体,都当做他个人所有的了,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清楚的。“力柯的这番话,等到福伯爬上马车驾驶坐位并拿起鞭子时,佳容便认定是确确实实的了。
“你姑妈因为没有来接你而不大高兴。她怕你见怪,但是俺告诉她,她和媚兰小姐要来,只会溅一身泥水,糟践了新衣裳,而且俺会向你解释的。你最好自己抱那娃娃。佳容小姐,瞧那小鬼快把他给摔了。“佳容瞧着林茜叹了口气。林茜不是个很能干的保姆。
她刚刚从一个穿短裙子、翘着小辫儿、瘦得皮包骨头的小鬼,一跃而成为身穿印花布长裙、头戴浆过的白头巾的保姆,正洋洋得意,忘乎所以呢。要不是在战争时期,在相关部门对水塔的要求下,雪乔不得不让出了嬷嬷或其他乃至罗莎或丁娜,她是决不会在这么小小年纪就上升到这样高的位置的。林茜还从没有到过离陆家村村或千塔一公里以外的地方,因此这次外出旅行,加上晋升为保姆,便使他她那小小脑瓜里的智力越发吃不住了。从千塔到凤来镇这20里的旅程使她太兴奋了,以致佳容一路上被迫自己来抱娃娃。此刻,这么多的建筑物和人进一步把她迷惑住了。她扭着头左顾右盼,指东指西,又蹦又跳,把个娃娃颠得嚎啕大哭起来。
佳容渴望着嬷嬷那双肥大又老练的臂膀。嬷嬷的手只消往孩子身上一搁,孩子马上就不哭了。可如今嬷嬷在水塔,佳容已毫无办法。她即使把小儿子从林茜手里抱过来,也没有用。她抱着同林茜抱着一样,他还是那么大声嚎哭。此外,他还拉扯她帽子上的饰带,当然也会弄皱她的衣裙。所以她便索性装做没有听见福伯的话了。
“过些时候也许我会摸准小毛头的脾气,“她烦燥地想着,同时马车已颠簸摇晃着驶出了车站周围的烂泥地,“不过,我永远也不会喜欢逗他们玩。“这时小孩已哭叫得脸都发紫了,她这才怒气冲冲地喝斥了一声:“我知道他是饿了,把你的兜里的糖给他,林茜。无论什么都行,只要叫他别哭就行。可现在我一点办法也没有。“林茜把早晨嬷嬷给她的那个糖拿出来塞进婴儿嘴里,哭叫声果然停息了。由于耳边恢复了清静,眼前又不断出现新景象,佳容的情绪开始好转。到福伯终于把马车赶出水坑泥洼驶上了桃树街时,她觉得几个月来头一次有点兴致勃勃地感觉了。这城市竟发展到这个地步啦!距她上次拜访这里才一年多一点,她熟悉的那个小小的凤来镇怎么会发生这许多变化呢?
过去一年她完全沉溺在自己悲痛中,只要一提到战争就不胜烦恼,因此她不明白从开战的那个时刻起凤来镇就在变了。那些在和平时期使凤来镇成为贸易枢纽的中心,如今在战时已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由于离前线还很远,这个城市和它的几条路成了联盟两支大军之间的联系纽带。凤来镇同样使两支大军与南部内地相沟通,从那里取得给养。如今,适应战争的需要,凤来镇已成为一个制造兵器中心,一个医疗基地,以及南方为前线大军征集粮草的主要补给站了。
佳容环顾四周,想寻找那个她还记得很清楚的小镇,它不见了。她现在看见的这个城市就像是一个由婴儿一夜之间长大起来并忙于扩展的巨人似的。
像个嗡嗡不休的蜂窝,凤来镇一片喧嚣,它大概骄傲地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所以在没日没夜地工作。战争开始前这里以南有很少几家布厂、染坊、和兵器厂,这种情况还是南方人引以自豪的。南方产生学士和士兵,农场主和医人,可是肯定不出铁匠师和建造师傅。让北方佬去挑选这些下等职业吧。但是现在联盟的港口已被北方船只封锁,只有少许偷越封锁线的货物从洋河暗暗流入,于是南方也就拼命制造起自己的战争用品来了。北方可以向全世界要求提供物资和兵源,在它优厚的钱财引诱下,成千上万的赏金猎人源源不断地涌入敌方军队。而南方就只好转而依靠自己。
在凤来镇,只有一些缓慢进行生产的兵器厂用来制造军需品----之所以缓慢,是因为南方很少可供模仿的木子,几乎每一把武器是按照从偷运口的图样制成的。现在凤来镇的街道上有不少陌生的面孔。一年以前人民们还会驻足倾听一个国外腔调的声音,可如今连来自别国的人儿也无不注意了。这些人都是越过封锁线来为南部联盟制造兵器和生产粮食的。他们是些技术熟练的人,如果没有他们,联盟就很难制造长枪、等武器了。
根据福伯所说的情形,佳容
觉得凤来镇已成为一座伤兵营了,因为那里数不清的普通草屋、医馆和医者,而且每天下午还要卸下大批的伤病员哩。
那个小小的城镇不见了,如今有的是一个迅速扩大的巨城,它正以无穷无尽的力量与紧张喧扰的活动不断更新自己的面貌。这种繁忙景象使得刚从乡下悠闲生活中出来的佳容快要喘不过起来了,可是她喜欢这样。这地方有一种振奋的气氛令她鼓舞,仿佛她真正感受到城市的心脏在同她自己的心脏一起合拍地跳动。
他们在这座城市的主要大街上穿过泥洼缓缓前进,佳容很有兴味地观望着新的建筑和新面孔。人行道上拥挤着穿士兵服的人,他们标明他们属于不同的军营。狭窄的街道塞满了各种马车,运输粮草的,救护伤病员的,驾车人浑身污泥,汗流满面、骡马在车辙中挣扎前进的盖着大布的大车;穿灰色服装的信使溅着泥水在各个街道之间匆匆奔跑着传递命令和信报;正在康复的伤兵一病一拐地走动,有的还由小心的小姐在一旁搀扶着。喇叭声、鼓声和吆喝的口令声从训练新兵的操场上远远传来。佳容还心惊肉跳地头一次看见了北方佬的制服,那是福伯用鞭子指给她看的一队垂头丧气的北方兵,他们正由一小队士兵的联盟军押送到俘虏营去。
“啊,多么富于生气,富于刺激性啊!我会高兴在这里住下去了!“佳容这样想。自从大野宴以来,她还是头一次真正感到乐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