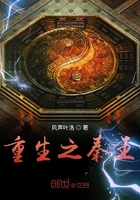第五章 女儿心事开
那个女孩子任谁也劝不住,这山庄里外的事情,她都要亲力亲为,不肯假手于人。是因为山庄里实在是没有值得信任的人,还是她一贯如此强悍能干,大权独揽?
兰缺想不明白,也不愿多想。
他懒洋洋地一觉醒来,业已冷月婷婷偏西。
待他开启房门后,幽幽的秋风廊里灯笼点点昏黄如星,便瞧见一个素白的纤细背影坐在院子里光秃秃的圆石上,一株朝夕花畔。她姿势优雅地昂首守月,像是在等人,又像是在沉思,连他衣襟飘飘地趋风走到了她身旁,仍然不惊觉。
兰缺暗暗地闻着她身上飘来淡缈的馨香,捂唇咳嗽了一声。
她才恍然回过神来,侧脸看向他。她神色依然不怎么好,似乎更差了一些,精神也不济。身上的衣裳倒是换了一套,仍然是月黄净绣的淡静款式,纤长婉丽的面容,再加上整齐梳理过的乌发摇髻,素钗环萦,在如此清风夜里秀花旁,颇有几分云浮仙子的空灵恣意,只是眉目间多了一点柔柔的缱绻倦意。
“一直没有调息吗?”兰缺心头忽悸,眉睫微动。
“没有!都要忙不过来,出去了这么些天……庄里庄外的事情……多着……”有极语气淡淡地说着,似乎淡淡地提起,不过是寻常之事。
“你就不能让别人去干?”兰缺看不下去,出言打断了她的话,声音里有种别于一贯轻浮花哨的肃然。
被他喝得愕然地抬起了眼睛,有极有些诧异地瞧见他神色担忧地望着自己,望着自己一个人背起这一个庞大的家族?不禁又是一笑,摇了摇头,却是不接话,不知道是无从接起,还是不愿意去说。
“下雨了……”摸着脸上忽来的清凉,“我们进屋去说吧!”兰缺不再纠缠话题地说了一句,转身往回走。
他实在不想让一个病人还淋雨受凉。
有极不介怀,随了他进屋,看着他燃起了明灿烛火,看着他喝了一口早已凉掉的茶水,看着他在窗旁倒掉,看着他问:“你吃晚膳没有?我好饿了。你们山庄不至于不让人吃晚膳吧?”
有极眯眼,忍不住一笑,她在屋内拍了一拍手,响声清脆有音律。
兰缺微微惊诧地瞪眼看她。
不久,脚步声就从屋外传来,一个个丫鬟捧着菜肴汤羹款款进来,又一一摆拼在圆桌上,刹那之间就变出了香喷喷的晚膳,碗筷茶茗壶具一应俱全,在所有的富贵人家里也不过如此了。
望着这一桌的山珍海味直摇头,兰缺抬起凤眸嗤嗤笑着,敲指问道:“你们每天都吃这些?我这穷酸肠胃可经受不起每顿都吃这么丰盛的饮食。”
有极怔了一怔,说道:“我以为你喜欢。”
“谁说我喜欢?”兰缺挑眉好奇地问她,看着她一脸的认真神色,这样的神色出现在她的脸上竟然有着说不出来的可爱之处。
“每一次我请你吃,你都吃得欢快啊?”有极掠眸回想起这一路上,他不都是吃得不亦乐乎吗?
兰缺翻了一个怪眼,眯眼说道:“既然你已经要了,我如果不吃岂不是浪费了?更何况你一片盛情,我怎么好意思回绝?“他笑吟吟地望住她,乌漆的眉睫在灯光中泛着微闪的光亮。如此衬托之下,一双眼睛更是熠熠流彩生光,犹如银河星辰,让人不能回避。
有极微微晕红双颊,这一路上她确实是在故意折辱他。现在想想,自己也忒小儿脾性了,竟然就这样的任性,不由是好生地一笑,笑了起来宛如繁花绽放,说道:“以后我尽管请你吃青菜白萝卜好了。”
兰缺冲她眨眼一笑,说道:“你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呗!”
这句话说得像是老夫老妻之间的撒娇。有极和他隔桌而坐,望着案上羹汤碗筷心中闪过一丝细腻思绪,不由脸上又是一烫,但转眼见他说得漫不经心,想是一句调笑的话儿,也就定下了心来,却又是莫名其妙地有些许的失落。
有极淡定地一笑,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径自喝了。
兰缺和她面对面地吃着饭菜,喝着酒,室内灯光悠悠,室外小雨纷纷,颇有点小家小室的柔和而温馨的感觉。
有极不知道是因为饮了酒的缘故,还是这秋雨让人生闷,心里竟然是暖烘烘的,一点儿一点儿地发热起来。她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而此刻坐在身畔的兰缺也不像是当初所见的那样无赖戏谑,浪荡不羁,虽然还是有点边幅不修,长发凌散,但是她瞧着这些竟然觉得亲切起来,仿佛要不是这样,他就不是她渐渐熟悉了的云兰缺。
她心底默然地一笑,谁也不知道。
这人的心思一直难以猜透。有时候明明瞧着他一身的正气,却偏偏言行举止怪诞不羁,浑然透着一股妖异邪气。
兰缺举茶漱了口,朝她莫名其妙地看了一眼,这一眼,眼神深邃难猜,令她一下子醒了过神来。
兰缺将散乱的头发胡乱一抓,拿起簪子随心所欲地固定住。脑后还是不时落下了几络,还是少不了那浪荡不羁的韵味。他诡秘地一笑,忽然用种不同一般的语气说话:“东方姑娘,我有一件要紧的事情与你商量。”
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认真,有极不由提起了神来,问道:“是关于我爹爹的事情?“
兰缺怔了一怔,回看她,没有料到她如此聪颖。顿了一下,他悄声说道:“是的,是关于令尊的……”他清莹透亮的凤眸在夜色里晃了一晃,感觉四下里皆无人,才继续用同样轻微的声音说道:“今日,我与东方庄主把脉之时,察觉他脉象有异……”他的眸中神色一闪,语调诡异了起来,“他那样的脉象,绝不是血竭病症。”
有极心头一惊,定睛睨着他,看了好半晌,似乎在审度他的话般,过了许久,才微微颤着唇瓣道:“那是……”
兰缺唇角一翘,眼睛里却是没有任何的笑意,他把她的神色看在了眼里,轻声说道:“如我没有料错……那是……中毒。”
“中毒?”有极微微挑起了纤眉。若然真的是中毒,那这件事情就该是怎么的复杂了?
“这毒也不是短期之内中的,根源已经有两年之久。中的毒不会立刻要人性命,却是会慢慢地发作出来,慢慢地侵蚀五脏六腑……这毒还下得极其微量,是以不易察觉,但所发作的症状就同血竭症无疑!一般大夫是分辨不出来的。”兰缺用带着阴谋般的语调把话一口气说完,并用凌厉的眼睛瞅着她的神色。
有极心头的惊诧一点一点地加深,她张了张唇,伸手不自禁地捂住心口,颤声问道:“你说是,有人一直在我爹爹身边下毒,企图置他于死地,却又不想被别人发觉?”
兰缺慎重地点头,眼眸沉沉。
有极双手微微颤抖了起来。心思一时混乱,下毒的人会是谁?为着什么呢?下的又是何种毒?这种毒又是如何得来的?下毒之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神不觉鬼不觉地杀害她的父亲?还是想要东方家的家财地位?
大家一起吃饭用膳,为什么偏偏只有爹爹中毒?这毒都是下在哪里了?一步步思索,一步步惊心!如此思索下去,那么能成为这个凶手的人……岂不是最能接近爹爹的那些最亲最近的人吗?
她惊诧着眼睛,看住兰缺,再一次谨慎地问道:“你确定……你确定这不是血竭症?而是中毒?”为何先前请来医仙岛的名医们诊断的也是血竭症呢?为何没有一个大夫诊断出端倪来?偏偏眼前这个少年却是如此说,他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小——二十尚不足。
他的才华当真如此异殊吗?
兰缺笃定地回答道:“绝无虚言。”
有极看见了他神色中的肯定与真诚,她不再怀疑。她心里一阵翻江倒海,刹那之间,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淡然问道:“中的是什么毒?可……可还有救治的法子吗?”
兰缺长长舒了一口气,“办法不是没有。”
“什么办法?”有极趋近于他问,眼中凝着坚毅之色。相处时日虽短,但兰缺知道她是一个脾气倔强的硬气的女子。她想要办到的事情,就一定会想尽办法去办到,何况她想救的人就是她爹爹,她更是会不顾一切地去想办法的。
兰缺心中无来由地生起了一股莫名的怜惜之意。他蹙了蹙眉头,悄声说道:“要知道这种毒是什么?就必须先找到它。”
“你是说要找到那个下毒之人,然后拿到他手中的毒药?”有极与他目光相对,心思无异,淡色的唇瓣轻张。酒气,香气,暖气,似乎还融化着什么在空气里蔓延开来,兰缺的眸光渐渐地迷蒙慵懒起来,少了以往对视时候的锐光,宛如隔了一层白茫茫的雾。
而彼此坐在咫尺之间,一股淡然的素馨香气扑鼻而来。
兰缺唇畔淡淡地带了一点梦幻般的笑意,眸眼如星,“只要有毒药在,我就能配制药方解毒。”这一句话他说得无比自负自傲,无人能抵。连她也抵挡不住他这样的光华耀眼,在这萧索孤清的夜里,一张笑脸艳煞了她的眼眸,使她毕生也难以忘记此刻的一眼一言。
有极怔忡良久,才避过了眼睛,她心存疑虑多时,不由转而问道:“你真的是有起死回生之术?”
兰缺听她这话问得天真,与她一向的作风迥然不同,不由翘唇而笑,“连你也相信这连篇的鬼话?世上有谁能够起死回生呢?”不由想起,昔日她看出他铜钱掷屋壁的巧妙关子,聪慧理智无比,才思敏捷异常,而今日却是来犯糊涂了。当真是关心则乱了?他默然一笑,眉梢暗挑。
“那今日之事,并非鬼神之说?”有极更是疑惑不解,淡定惯了的神色也起了一丝的俏皮。难道她今天所见的事情是做梦了?此刻回想起来,自己今日所经历的事情,当真不像是真实发生过的。
兰缺看了她心有余悸的模样,不由心头微微一颤,伸手轻轻拍拍她的肩。毫不避忌的行止让有极一下子立起了恍惚间稍微松垮的肩膀,看着他,脸色尴尬。她就像是一个端庄的淑女,他就是一个无行的浪子。
兰缺瞧着她紧张而深有教养的神情,不由收回了手,不以为意地笑笑,自己斟了一杯,举酒低声说道:“一切只因你爹爹并不是真正的仙去,而是阴阳之气失调所致的尸厥症。”他的笑容恢复了那一种艳丽妖异的颜色,也是一种深为寂寞的颜色。
有极闻言,更是心惊不已。尸厥症不是真死,而是一种气息不畅的假死,如果不是兰缺在此辨症敏锐,她爹爹岂不是要被生生钉入棺木,生生埋于土中闷死?她手上轻颤,瓷杯中的酒都点点地洒了出来。
兰缺转杯,漫不经心地笑,说道:“庄主病发于丑时,正是肝经当令,阳气渐升,阴气渐衰,是阴阳两气交汇之时。如果此时阳气当升不升,阴气当降不降,被阴气克制住了阳气,那么就会出现阳缓阴急,阳气被闭塞住,人便会出现佯死之状,是以并非真死。”
有极一听,顿时明白他为何要问清时辰与病发之时的脉象,而后的一切救治又是如此的从容不迫,胸有成竹,条理分明,用针取穴,下药得法——精、准、绝、妙,如此才华出众而又如此胆大妄为实在是无人能及,不愧是香富贵这家伙谓他为“燕洲第一神医”,舍云兰缺其谁?
她笑靥轻绽,秀眉微挑,眸光烁烁如华,宛如一夜开尽繁华清菊,一路开尽地角天边。
他于她的眼前垂眉低笑,从来不把自己的本事当成一回事。无论是在穷乡僻壤,还是在这天底下最富裕的东方山庄,他都是如此的淡眼人世,言行无拘。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
兰缺观察她的气色已久,抬起手臂,眯眼一笑,柔声说道:“你气色不畅,我给你搭搭脉?”
有极没有顾忌地伸出手,手腕纤细洁白,馨香不胜,脸上又一次暗暗显了一抹羞色,两颊晕红,心中一阵温暖之气洋洋四溢,无从来,无从去。以往心中孤清之意,都被它悄悄驱散,缓缓占领了她心中一些重要的位置。
今晚,她三番四次地脸红。当兰缺的三根手指拈住她手腕上的肌肤时,心头猛然一收缩,呼吸也滞了一滞。不知道他摸着她的脉络是否也已知晓了那乱纷纷的心跳?此刻眼睛都不敢正面瞅他的神色,眼角的余光却瞟见他一脸的凝神正气,才勉强平静下来,不去胡思乱想。
兰缺摸着她的脉相,径自运起内力助她调息。他就知道,这个女孩子不会顾惜自己的,在她的家族面前,在她的父亲面前,她自己似乎是可以完全忽略的人。
翌日午后。
老夫人被有极说服,领着一众人去城外的白云寺去吃素沐斋为东方庄主祈福。
和姨娘却如何也不肯去,要陪在东方庄主身边照料。自从东方夫人——有极的母亲逝去之后,老夫人先后给东方庄主纳了两妾,一个是莫姨娘,之后为东方家添了一个男丁,就是喜欢玩鸟斗乐,不务正业的东方洺;另一个就是和姨娘。
和姨娘不是老夫人做的主,而是东方庄主怜惜她身世凄凉,才纳其为妾,安置于山庄之内。和姨娘平日生性不争不怒,极是温驯,也渐渐得到东方庄主的欢心,长年陪伴在左右,宠爱有加。就连守在东方庄主榻前,动不动也会泪水涟涟,好不疼惜的一个水做的人儿!
兰缺与有极徘徊在前院里,这和姨娘不走,倒是坏了他们的计策。他们既然要在他们之中搜出凶手,就不能让任何一个人察觉,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系。
谁也不知道藏在东方庄主身边下毒的人,究竟会是谁?
此时,靖远已经领着绿绮赶了回来。
有极吩咐穆管家安排绿绮的住处,兰缺主动说道:“安排她与我同一个院子里就好了,方便我照料她的脚。”
有极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但是见他对绿绮如此亲近,丝毫不见外的亲昵溢于言表,不由心上暗暗一阵莫名的情愫升上来,浑身不自在地看了他们两人一眼,默然点头,让穆管家着手去办。
傍晚时分,有极独自吃着晚膳,不禁想起前一天两人一起用膳时候的光景,心中不由一阵怅然。原本她大可去请兰缺、绿绮两人一起出来共膳,但是想到日间他们两人互相说笑时候的神情,想起兰缺对待绿绮那种细心呵护的搀扶,想起兰缺在绿绮面前那浪荡不羁,无拘无束的言笑眼神,她就浑身一个劲地冒刺儿,不想瞧见那样的情景。
若是瞧见了,她不能让自己当成什么也瞧不见。
为什么会这样?明明前些天她还和他背向而立,形同陌路,那时候他一直就是这样地对待绿绮,为何那时候她就没有一点特别的感觉,只觉得他这人是如此的无赖,如此的俗气?
哼着那样不入流的俚曲,对着姑娘家说着那样油腔滑调、不正不经的话,十分的不入流!
她那个时候还毫不掩藏地鄙视他的行径,对他有着十分的成见。
这一切到底是在什么时候给统统地转变了呢?有极迷糊了眼神,独自一人在饮酒,屋外孤月清清如人,人如清清孤月,一样的孤寂。
她负手悄声地走出了屋,不知不觉地就走到了望云院的拱门之外。墙内花木扶疏,青石嶙峋,芭蕉临窗,枯荷满池,人工雕刻与自然景致相映,令有一番别致的意趣。
有极正径自出神,便听见院子里有人在吹箫。箫声隐隐,曲调孤清,似乎在诉说着谁的寂寞——有极不由心感神受,只觉那人与自己是同病相怜。正待跨步入内,却听见箫声乍停。绿绮在温言温语地说话:“师父,你以后还回北方吗?还是就此留在了南方?”
“这里事情办完,我们俩还是回北方去吧!只要有小美人你陪在我身边,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快活。”兰缺依然是满口花哨地说道。
有极背在门外,可以想象到他脸上那种满不在乎的笑,颈子下的衣裳随意地扣了两颗扣子,衣摆在风中飘飘荡荡,连同一头乌黑的长发也是杂乱无章地用一支看不出是铜是铁的发簪子固定在脑后,松松散散,似乎随时都会随风一展,滑落下来,披在宽肩之上……浪荡之极!
绿绮却是轻泠泠地笑了起来,欢笑之声清脆如铃。
有极听着他们的对话,一时之间难辨真伪,莫名地心跳加速,怦然擂动起来,神志也为之动摇,只觉得胸口暗暗堵塞。双手握了一握衣袂,赶紧快步走开,恍如避若蛇蝎。
夜深人静之后,四处无语。
偌大的东方山庄只剩通明的灯笼在秋风之中飘摇,闪烁的火光里又似乎隐瞒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两个探求秘密的人,行走在曛色的夜间。
他们一间一间卧室地搜去。这两个人自然是东方家的少主人——有极姑娘,与自称有起死回生之术的神医兰缺。他们仔细而小心翼翼地翻着各人房中的事物,企图在其中找出下毒的凶手与那致命的毒药。
巡查的队伍一次又一次地在房外打着灯笼走过。明明是在自己的家里,有极却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每一次巡查的队伍走过,他们都停下来,不敢弄出半点声响,伸手将微弱的火光捂住。
这一次手快,是有极捂住了火光。
房门外的脚步声缓缓地经过。
火光正照在一旁兰缺的眉眼上,他的眉头凝着深思,不似平日的荒诞不羁。有极倏然失神,手指为灯火一炙,轻嗤出声。兰缺一转眼眸,瞧见她骤然缩手,唇角一笑,再自然不过地拿过她的手。有极心头一跳,她知道自己应该把手缩回,但是就是这么想着,手指还是被兰缺拿在他那略微粗糙而纤秀的手中……他低头往她的手指上轻轻吹了一口气,有极感觉到自己的心在他的这么一口气中悄悄酥融了开来——
不管在傍晚的时候,她是怎么看到了他浪荡不羁的浪子无行,她是怎么约束自己不要对这个少年产生任何的一种好感,她是怎么意识到他的轻浮是如何的不适合于自己——他就像是一条响尾蛇叮住了她的心,她的人在他的毒液里酥麻,她不要,她不要这样毫无落点的感觉,这样的虚无,这样的没有把握,让她一向踏实的生活为之失控。
他们是不适合的,她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
可是,他此刻笑得太真诚,太明艳,她下不定决心去摆脱他的蛇信子——有极的心跳得飞快,不知道他是否对任何一个在他面前的女孩子都是这样的漫不经心,这样地去挑拨别人的感情?
她咬牙一甩手,要在他手中挣脱。兰缺却是微微错愕地挑眉看住她的神色,依然是那样的笑,笑得让人心动神摇,不得自持。他邪气地一笑,紧紧握住她的手,另一只手从衣襟里拿出一只紫色小瓶子,用牙齿咬开瓶塞,一阵芳香在彼此相对的尺寸之地漫溢了开来,他犹似不自知地氤氲了别人一身一心的香气与迷惑。
兰缺将瓶子里的药水倒在有极的手指上,药水清凉如冰,覆在她被火炙伤的殷红处。他从她腰间扯下方巾,包扎在她的手指上。有极的脸色已然一直红到脖颈,从来没有人敢在她身上动手脚,别说拿她的方巾,就是敢如此轻易握住她的手的人,也没有!
她乌眸漆黑地凝视着他,兰缺不以为意地笑笑,俯唇悄声说道:“这样就不会留下难看的伤疤了!”
他还是这样的神情,一点认真也没有。有极骤然觉得心惊,自己已经渐渐陷于了他有意无意而为的泥沼,可是他——他却一直站在云清山高处。他在看着她吗?看着她一点一点地沉沦吗?他如此这般地对她,是恶意的吗?还是他一贯如此?从来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性情,不会向旁人显露出最真实的自己?
有极秀眉微愁,默默地收回了手。
兰缺听着外面的声响已经过去,他拍拍衣裳上的尘土,站了起来,说道:“我们到下一间去吧!这里是搜不到的了。”他说得这样的云淡风轻,仿佛刚才的事情一点也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她一个人,在多心了。
有极垂着头,难堪地一笑,而后,平静无比地站起来,说道:“走吧!”她不应该让自己对他有一点的绮念。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