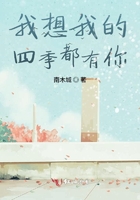他上得高峰,不再一味的面向北面远眺。他知道自己那样远眺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他看到的东西有限。他必须全神贯注补充自己散失的精力,让自己有限的功力发发挥更大的作用。他选了一处平坦的地面,放下身心,盘腿打坐。他一闭上眼睛,就有一股强烈的感觉袭上心来,瞬时间就忘记了自己的所在。他心中不禁大喜,知道这是一个练功的最佳处所。他从来就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好地方。他被舅舅接上山的那些年里,在舅舅安排的地方练功,也没有过这样强烈的感觉。这样的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立即摒弃这种沾沾自喜的意识,让自己进入平淡的心境,再进而忘我。他在恍恍惚惚之中感觉到了源源不断的力量进入他的四肢百骸。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他从一种混沌的状态中回转,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了。他立即跳起,面向县城方向,将内力注入视力。
暮春的雾霭似乎愈来愈浓了,太阳光也没有先前的亮堂。这时候应该是下午三点钟了,这是他对时间的一种把握和确定。他不知江冬琳他们三个人现在在做什么。他无暇为此分心。他当前唯一要做的,就是将他重新获得的功力发挥更大的作用。他的目力如一道看不见的闪电,从高高的登天门上射向遥远的天穹。那些薄薄的雾蔼无法阻挡它的穿透力。他一清二楚地看清了县城。县城的西南角的上还在过着日本鬼子的军队,不过已经没有了上午那样的连绵不断。断断续续的队伍还在行进。大街上的死尸仍然还在。燃烧的房屋还在冒烟。小股的巡逻的士兵没有上午多了,剩下的一些在游走。
他不管这些,他只关心他的房屋。他的房屋里有他生病的老父亲。他唯一比上午看得更清楚的,是家里的那扇大门被打开了。他心里咯噔一声惊跳了一下。他出门的时候,记得是将大门锁起来的,现在怎么被打开了呢?父亲即使要出来,不但他的身体不允许,就是允许,他也不可能从里面打开了啊。不过,他再认真地看看别人的房子,好像也有被打开的。冬琳家的大门也敞开了。他也记得清楚,当他背着江妈妈离开的时候,是江叔叔锁的大门。
不过也不奇怪,日本鬼子来了,他们要找吃的,更要寻找安全感。他们其实也是离不开人群的。他们以战胜者的姿态进入县城,他们不希望是一座空城。一座空城对他们无疑是一种耻辱,宣布他们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势必要冲进关门闭户的人家,要求得到人们欢迎和犒赏。让人们用他们的血汗来喂肥他们,然后更有力量来屠杀他们。
看起来,不是他一家的屋门被打开了。被打开的屋门虽然是不情愿的,但对于侵入者,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他离开父亲之前,曾经多次嘱咐过父亲,无论是什么人冲开了屋门,他都要安安静静地呆在地洞里,不要作声,不要让人发现。只要不让人发现就是安全的。屋子的大门虽然被打开,并不意味着地洞里的人就一定被发现。可以这样认为,大门被人冲开不可避免,而地洞里的人被人发现却也未必。他心里似乎稍稍安定了一点。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下心来。他想他必须要回县城一趟。他不能在数十里外忍受父亲有可能出危险的煎熬。不管县城现在是如何的危险,他也要冒险去看看父亲。如果有可能,他会将父亲背出城,住到周宇方家里来。
他在岭上看见周宇方三个人,已经坐在了之前他们几个人坐的那块大石头下上,正仰着头向上看。他们一定等得着急了。他必须赶紧下去,赶紧回家。他相信三个家庭的老人们一定等得急了。
冯奇飞飞身下岭,三个人迎上来。他们一边往回走,他一边将岭上看到的和想到的对大家说了,提出他明天一个定要赶回县城去。周宇方说:“那怎么行?你已经亲眼看见了,大街上杀死了不少的老百姓。日本鬼子有枪,人数又多,你回去是很危险的。不如再等几天,让日本鬼子退了再回去吧。你还告诉我们,日本军队正向西北方向开走嘛。”
“再等几天,我父亲怎么办啊?”
“你不是已经给冯伯伯准备了好几天的食物了吗?”
“房屋的大门已经被打开,说明日本鬼子随时都可以进入屋里,地洞也就随时可能被发现,我父亲也就随时都有危险。我不能再等了。”
丫姑这回不作声了。她也知道飞哥哥是个想做就做的人,别人的劝说似乎无济于事,她想根据他的性格特点达到自己的目的。
江冬琳听了冯奇飞的决定,在心里分析他的更详细的想法。日本鬼子进了城,就好像一群豺狼虎豹进了羊群,杀人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如果说冯奇飞不放心父亲,那么她对冯伯伯的担忧一点也不逊于他。她只是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现在就想回到县城去。冯奇飞说明天回去,难道他想到了可行的办法,既没有危险,又能顺利地见到他的父亲,最好背上他离开县城那个虎狼之窝?
“江冬琳,你怎么不说话?你是怎么想的?”周宇方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自己的好朋友,转而求助江冬琳。
“奇飞说得对,明天是要想办法去县城了。县城已经成了杀人场。冯伯伯一个生病的老人,既没有人照顾,又时刻处在危险之前。要去县城,只是要想一个好法子,不让日本鬼子发现,惹出麻烦来就好。”
冯奇飞高兴了,说:“冬琳说到了我的心里话。办法多的是,到时候灵机应变就行了。”
江冬琳说:“我们白天走路。还要绕开大路走小路。人多的地方不能去。到了城边,要等到天黑了才能进城。”
冯奇飞挥一挥手,说:“什么你们我们,你们都不要去,人多显眼,危险大。不如我一个人去,目标小,也容易躲。好,就这样说定了,你们再不要争了。”
他说完,就加快了脚步,好像现在就要甩脱这三个人似的。
三个人互相望望,使使眼色,也就不作声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眼色是什么意思,是无可奈何,还是不要惹冯奇飞生气?还是有别的想法?当着冯奇飞在这里,只能用一个莫名其妙的眼色互相安慰吧。
冯奇飞忽然又转过身来,对江冬琳说:“冬琳我教你一些简单的武术动作,也好保护自己,你看好不好?周宇方和丫姑都有本事,只有你,一点也不懂,万一你一个人碰到危险了,也好抵挡一阵。”
江冬琳笑了,说:“你现在才想到?我过去让你带我去看你练功,你都不答应。现在怎么又想到教我了?”
冯奇飞说:“唉,此一时,彼一时。我以前以为只要我练好了本领,保护你不成问题。现在我父亲一个人在地洞的事让我受到了启发。还是懂一点基本的套路保险。”
“好啊好啊,你现在就教我吧。”
冯奇飞告诉她,女孩子首先要了解一点脱险的技术,例如让对方的眼睛受伤,出其不意攻击对方的下体,用一双手拽住对方的一根指头,拼尽全力拗断它,必要的时候牙齿也起作用。如果觉得自己还有力量,就反剪对方的手臂,脚下同时使力,将对方打倒等等。他边说边做动作。有时候还将周宇方拉过来表演。不知周宇方是故意配合,还是禁不住冯奇飞几下简单动作的力量,几次扑倒在地。冯奇飞的动作之快捷有力,让江冬琳还来不及看清就过去了。
丫姑走过来,说我来陪师父练练。冯奇飞稍稍犹豫了一下也就动了手,照旧是他说的那个套路,也是以周宇方作为陪练的方式,但是丫姑不愿意配合,她要用另外的动作来化解,从而达到攻击对方的目的。但是,她的化解在冯奇飞的身上不起作用。冯奇飞似乎并不理睬丫姑的攻击,只轻轻地一带,不知用了一个什么动作,丫姑就仰天倒在地上。她立即爬起,嚷着,说她还没有注意,不行不行,再来一次,动作要慢一点。冯奇飞笑了,说再慢一点你也没有办法。边说边继续了原来的动作,丫姑又倒下了。丫姑再一次爬起,说飞哥哥你不要隐藏你的动作,我还是没有弄明白。你的动作再慢一点嘛。
周宇方说,你是一个蠢婆娘,他的动作太简单不过了,其实你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只是你的功力不够,你怎么能对付得了他呢?丫姑似乎明白了什么,微微地点头。冯奇飞肯定了周宇方的说法,说丫姑要想打倒我,还要加紧训练基本功。
冯奇飞问江冬琳看明白了没有?江冬琳说,这动作太简单了,不知道我能不能打倒你冯奇飞。她笑嘻嘻地让冯奇飞站过来,她仿照冯奇飞的动作演示,冯奇飞竟然乖乖地朝江冬琳用力的方向倒去,只是倒了一半就稳住了身子。江冬琳快活得大笑起来,说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练功原来这样的有趣,难怪你们乐此不疲!我也要好好练,有一天我要真正打倒你冯奇飞!丫姑立即响应,说万一打不过,我们姐妹俩一同上。
四个人一边说,一边走,一边演示,嘻嘻哈哈很是热闹。脚下时时惊起潜藏的野兔,如飞的掠过他们身旁。还有野鸡和飞鸟,扑喇喇从这一棵树飞到那一棵树。偶尔还有远处转过头来望着他们的野羊和别的什么野兽。有一群猴子,从他们的树顶上跳过去,就像天上洒下来一阵急雨。跳过去并不太远的猴群对着他们搔首弄姿态,做着怪相。
周宇方说:“这山里是有老虎和豹子的,不过很少看见,只是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出没。不比野猪,好像离不开人,就像家里的老鼠离不开人一样。这山里的人到了哪里,野猪就会跟着到了哪里。其实,野猪并不是非要依靠人不可,离开了人它照旧可以生存。在很古老的时候,人还不会种庄稼,野猪也没有饿死。现在也有许多野猪并不骚扰人,但是另外一些野猪就是要与人作对,好像真就是山神爷和土地爷派遣它们,要来享受人的劳动成果,或者就是来找人报复的。”
冯奇飞问他:“是不是每个晚上都有野猪来捣乱?如果是这样,晚上你们就总是不睡觉了吗?”
周宇方说:“也说不定,有时候它们一连几个晚上都来,有时候也不来。它们不仅仅是糟蹋包谷,也糟蹋红著和别的东西。从春季到秋季,山上窝棚里总也离不开人值班看守。大山里是树木的天下,找一块空地不容易,要开垦出来更不容易。种一点粮食还要与野猪的那只大嘴争抢。”
冯奇飞说:“今天晚上如果响锣了,我也与你一道去赶野猪。”
周宇方说:“你明天不是要去县城吗?你好好休息吧,你毕竟是客人嘛。”
冯奇飞说:“不行,现在你家就是我家。现在日本鬼子打进县城,占领了我们的家,我们只好以你们的家当作我们的家了。如果你们还是把我们当作客人,我们就不好意思住在这里了。”
丫姑说:“飞哥哥不是客人,我更不是客人了。我过去从来不起床赶野猪,以后我也起床。”
江冬琳说:“我也去。我也不是客人。”
冯奇飞说:“好了好了,我不去了,我还是把我自己当作客人吧。我总不会永远住在周宇方家吧。你们也就不要跟着我起来受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