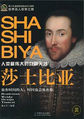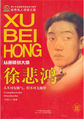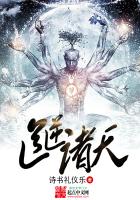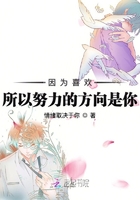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五日,道光帝驾崩,皇四子奕嗣位。
三月九日,奕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登上皇帝宝座,宣布改明年为咸丰元年。
新的君主,虚岁二十,虽然接手了父皇撂下的烂摊子,但毕竟有年轻人的朝气,极想打破死气沉沉的局面,革除积弊,重振朝纲。同时,有意回避受道光帝宠幸过的几个股肱大臣,倚重自认为忠实可靠的业师杜受田担当重要部门的高管。
很快地,杜受田由侍郎升官加爵到太子太傅兼署吏部尚书,复迁刑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随伺皇帝左右。
杜受田推崇儒教治国,极力维护封建纲常和大清祖制的思路与奕正相吻合。御极时间不长的皇帝,根据杜的建议,分别于三月二十日,三月二十七日和四月二十一日,连下三道谕旨求言求贤,并且命令各省督抚保举“才德兼优,诚心任事”的官吏,也允许九卿科道的普通官员皆可发表意见。
诏令颁发的当日,大小官员奔走传看,交口称颂,纷纷建言献策,上表陈情;其中,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折,实话实说,言之凿凿,引起皇帝的关注。杜受田推荐的林则徐和周天爵跃然出现在朝廷的用人名单上。
在此期间,冯志沂正奉命与几个朝廷大员去西陵勘验道光帝寝宫的修建工程,车至易州道中,映入眼帘的野景山色,分外妖娆,自觉有天意回春之象,吟诗曰:
北风为我扫黄埃,淡绿浓青泼眼来。
野色平沈千顷合,斜阳倒拥万峰回。
清时屡下求贤诏,物论应归命世才。
易水潇潇空往事,独驱羸马过金台。
——《易州道中》
途经陶家屯的小村庄,但见丛树掩映,绿水环绕,如逢世外桃源,乘兴又哦诗一首:
茸茸浅草带平沙,铁轮无声鸟语哗。
十里绿荫三面绕,不知林外有人家。
——《陶家屯》
勘验罢工程返回京城,适值礼部会试刚刚揭晓,有个与他很要好的本族兄弟榜上无名,心情多少有些不快。两人分析失败的原因,冯志沂指出:可能你疏忽了道光帝宾天,新皇帝继位的大事,策文中写及“皇上”、“陛下”没有在前头加上“当今”二字,以示区别,有混淆二帝之嫌。送别族弟回乡前,安慰说:文章事业固然关系到科名仕进,但也没什么了不起。回去以后,继续恪守孝悌的古礼,同样也是光祖耀宗的好事。今天,你切身体会到博弈贤关的艰难,不必因受挫而一蹶不振。人之立身处世,对富贵利禄应该看淡它,当以适志为好。“有荣华者,必有憔悴”,你慢慢领悟古人的这句话吧。
皇帝自登基以来,宵旰勤政,励精图治,不劳诸臣,亲自朱批奏牍,召见贤良,着手人事安排。济济众官,无不翘首“仰荷恩伦”。
应须提及的是,杜受田执掌刑部大权,成了冯志沂直接的顶头上司,有人撺掇他趁此时机请托堂官向皇帝保荐提拔重用;他丝毫不为所动,羞事“折腰干请”的行为,表现得格外谨慎、低调。
多数臣工们认为,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参政议政,是展示才德,博得好印象的机会。奕君临天下,有意起用忠良,诏求直言诤臣,这个得人心的举措,冯志沂是衷心拥护的,也和其他官员一样,似乎看到了大清振兴的希望。认为不应该再“缄默不语”,唯谨唯慎了,正准备写一篇有分量的建言,通过刑部汇综上表,希企得到采用。该从哪方面下笔呢?诸如:与英夷交涉通商问题,沿海各省加强设防的问题,平息粤西逆匪起事等等。写来写去,觉得件件都涉及治国方针,说深了不行,说浅了更不行,只好作罢。
又想写篇表白自己政见的文章,呈递给杜中堂,得到认同也可以;试写了几次,觉得用词激烈易伤文采,委婉含蓄不足以晓畅明白,良久斟酌之后,再次搁笔。
为什么顾虑重重,欲言又止呢?很可能他还存在着些许戒备心,以防不虞。因为穆章阿尚在军机大臣的位上,其党羽仍是潜在的邪恶势力,担心新的君主年轻稚嫩,不够持重,杜中堂缺乏政治经验,先生架子,一旦奈何不了这帮人,恐怕重蹈群奸乱政的覆辙。
愁思百结中,嗜酒善饮的他,丝毫尝不出酒味的醇香,任凭别人怎么招邀,一概摇头摆手谢绝。沉吟道:“平生好酒悲,意悔每自抑”。又“举酒不能饮,万感塞胸臆”。
光阴荏苒,很快寒露降临,阵阵霜风吹散了满天的繁阴,委庭的湿叶逐渐染黄变枯,发出飒飒的声响,秋籁之音把他带到了对国家命运的深沉思索和想象中来,写下几首《秋日杂诗》,其中一首云:
我游汤谷东,海水浴朝阳。
浮云从之起,宛转蔽其光。
当曙忽晦昧,万怪纷披猖。
流辉偶下照,犹使夔藏。
安得倚天剑,吾欲斫扶桑。
豁然披玄阴,坐使金乌翔。
却顾失归途,伫立心忧伤。
举世畏处明,吾谋诚不臧。
当他对国家命运担忧,又无可奈何的时候,突然得知朝廷于十月十七日下旨授林则徐为钦差大臣,促令赴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接着朝廷又一重大举措出台。
十二月一日,颁布朱谕《罪穆章阿、耆英诏》,诏称:“任贤去邪,诚人臣之首务也。”
“穆章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知遇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德同心,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章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
“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朕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章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耆英之自外生成,畏葸无能,殊堪诧异。伊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今年耆英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应事周旋,欺朕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尽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章阿暗而难知,耆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诏谕颁发,紫禁城内外无人不拍手称快,几乎都认为,过去力挺抗英的强硬派,大展雄风之日到来了。
笔下的“夔”灰飞烟灭,冯志沂满以为迎来了景运初开的春天,激动地写下四首诗志喜:
一
圣主持公议,严疆托荩臣。
才颂三殿诏,已觉万方春。
命将知神武,蠲租仰至仁。
微生逢景运,喜剧欲沾巾。
二
倏忽刀轮下,修罗技亦穷。
雷霆原独断,台谏莫言功。
元象中台坼,妖氛薄海空。
从知元治,不待温相公。
三
痛定思前事,安危势未分。
大星沉上相,横海出将军。
孤愤尸犹谏,遗章世未闻。
舟山遗垒在,战鬼哭愁云。
四
讳战争延敌,沿边尽撤防。
汪黄参密计,宗李入弹章。
天意非孱宋,宸谟迈古唐。
犹宽崇羽罚,至德感吾皇。
——《十月二十八日志喜》
穆章阿罢斥,耆英降革,两个妥协派的代表人物,灰溜溜的滚下了政治舞台。然而,沉浸在喜悦气氛中的冯志沂,却被突然传回京城的消息惊呆了。原来,林则徐受命出剿广西匪乱,路上仅走了十七天,于十一月四日猝死在广东普宁行馆。
京城的官僚士绅乃至平民百姓,无不为这位忠勇荩臣扼腕痛惜。冯志沂和林则徐是政治盟友,曾为林公在“虎门销烟”的正义举措而扬眉吐气,也为其后来的蒙冤黜革大鸣不平。这次,英雄出师未捷身先死,更令冯志沂悲伤,慨然写诗悼念之:
恩礼应无恨,民生剧可哀,
夺公何太遽,办贼正须才。
痼疾缘幽愤,高名集众猜。
故乡方款敌,魂去莫归来。
——《林督师薨》
时至今日,华夏儿女仍对林公“虎门销烟”,在侵略者面前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肃然起敬。林公“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著名诗句,抒发了他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不惜牺牲个人的崇高感情,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