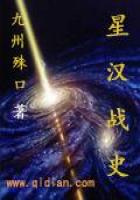场中一片寂静,只见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边从人群中一路挤来,边大声说道:“嗨,嗨!阿叔,阿婶,阿伯,别站着不动,光顾着看戏呀,先去救火呀!杨家阿公,你别挡住我呀!着火了呀,先救火再看戏呀!”好不容易,那孩子又气又急的挤到了场中,口中犹自说道:“你们怎么都站着不动呀?怎么都......”
“嗯?嗯......嗯?阿爸?阿妈?嗯?阿妈,你怎么了?”一回头才看见父母家人满身是血的躺在场中。小女孩顿时慌了神。“阿爸为什么躺着不动呀?阿爸,阿妈,你们流血了呀?”见还是没人回应她,小女孩口中已经带着哭音。一个军士嫌她碍事,看看温贺,又看看杨义满,犹豫了一下,咬咬牙,轻轻的将她推在杨义满的身边。柳小宛眼看着军士们砍下柳裁缝夫妇的首级,终于哭了起来。她抱头坐在了地上,抽泣着不停的哀求:“不要割掉我阿爸,阿妈的头呀,这样人会死掉的呀。”声音却越来越低,终于变成了哭泣。在房屋燃烧的哔啵声中几不可闻。
众官军取了首级,套好了车马,正准备列队离开,温贺突然狞笑着对陆居行说道:“斩草除根。这个小丫头多半是这家盗匪店里的女儿,若是抓起来严刑审讯,或许能得到海寇的消息。”陆居行心下恍然,这要下令。突然觉得一股杀气扑面而来,身上顿时寒毛倒竖。抬头一看,发现杨义满正狠狠地盯着这边,看来自己若是下令,只怕会立刻动手。再看周围,村民越聚越多,都是一脸愤意,有不少手持渔叉朴刀者更是跃跃欲试。不由得猛打一个寒颤。急忙大声笑道,“一个小丫头,随她去。”右手一挥,调转马头,往来时路上驰去。
转眼间,一众骑兵走的远了。只留下村民们看着柳小宛在烧成瓦砾的店门口,对着父母的尸体哭泣。看着孩子哭得可怜,一些女子也不由得轻声抽泣起来,更多的人或低声咒骂那些官军可恶,或叹息孩子可怜。
一个年轻人突然叫道,“这事情不能这么算了,定要报官,向那狗官讨回公道。”一位中年男子说道:“未必有用啊,你也听到了,那狗衙内的爹是个大官。”年轻人大声说道:“难道就这么算了不成?”顿时人群乱哄哄的议论开了。
杨义满见柳小宛还在哭泣,急忙招呼自己的妻子,“雪晴,快来管管这孩子。”没多久,人群议论不出什么头绪,又静了下来,众人不由得纷纷看向杨义满。临近几个村就杨义满一个秀才,杨家在杨家村又是大姓,因此平时遇上邻里琐事,不是找保长,保正,就是找秀才。如今众人知道了杨义满还是个修士,自然是更加敬重。先前那柳掌柜也颇受人尊敬,只是没想到会遭遇这等横祸。
杨义满沉吟半晌说道:“绝不能这么算了,我和诸位保长去告诉保正,待柳掌柜的儿子回来,然后去县老爷那里递状子。”说罢拱了拱手,“到时候万一开堂,还要请各位乡亲为我作证。”
众人纷纷应诺,渐渐散去。留下杨义满和几个保长收敛死难者的尸体,商议后事。
时至傍晚,回到家中,杨义满坐在案前,重重的叹了一口气。妻子走到他身旁坐下,轻声说道:“三个孩子都睡下了,柳家那孩子饭都还没吃呢,哭着睡着了。柳家的儿子回来了么?”
见丈夫默然不语便问道:“你怎么啦?”杨义满笑着说:“没什么。”脑海中却掠过了温贺临走前那仇恨的眼神,不由得皱了皱眉头。看妻子眼中隐隐有一丝愁意,知道她今日受了惊吓,正想安慰一番。忽然听到院子外有人喊道:“杨秀才在家么?我是东面祝家浜的保长,柳家的儿子女儿被你们保长找回来了,正在保正古员外的庄上呢。古员外想请你现在过去商议。”杨义满轻轻叹了口气回道:“稍候,我这就来。”
杨家村南十里处的古桥镇乃是县衙所在地。县老爷云焕自从二十三岁中进士,即刻上任到古桥县为官,至今已有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来,自己为官清廉,百姓安居乐业,古桥县开河六里有余,修桥三座,增设官渡码头三处,水力磨坊两座,一所官塾,一座书院。任内出秀才九人,举人,贡士各一人。虽不敢说政绩显著,也算是小有成就。每每想到此处,这位云知县总会忍不住洋洋得意一番。
前些日子镇上的酒商进了几坛绍州花雕,云知县闻得酒香,顿时食指大动,但看到价格,只得讪讪离去。犹豫再三,昨天傍晚再也忍不住了,咬咬牙,偷偷买了一坛回来。今天瞒着夫人起了个大早,去镇上切了一两羊肉,一两羊肝,三只肥鸡屁股,又厚着脸皮去东街林家的馒头店买了半笼小笼。此刻正在厢房里烫着酒,准备美美的小酌一顿。
闻了闻酒香,云知县挟起一片肥瘦适中的羊肉,正要往嘴里送。突然听到“咚”得一声巨响,只吓得筷子一抖,那片羊肉“嗒”的一声落在了裤裆上,赶紧伸手抓起,塞入口中。可那咚咚声还不停歇,犹自外面传来。云知县心中好奇,当下端着碗筷,走到堂中向外一张,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声响。却发现,竟是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披麻戴孝,敲着衙门外的鸣冤鼓。云知县不由得大惊失色,在古桥县为官二十年,从未遇过此等事情,击鼓鸣冤,难道竟是出了凶杀案?赶忙回房放下碗筷,穿戴整齐,喝令衙役大开衙门,即刻升堂。
门口走进来了四人,一站三跪,向知县行了一礼道:“见过大人。”云知县一看,认出了保正古员外,秀才杨义满和杨家村的保长杨兴,却不知那披麻戴孝跪在地上的少年是何人,于是对那少年问道:“方才击鼓的可是你?你是何人?有何冤屈?”
“禀大人,小人柳渊,是北面杨家村成衣店掌柜柳宜中之子。”随后,少年含泪将事情的来龙去脉,一一道来。云知县却是越听越惊。官府中的武将,竟有如此肆无忌惮的恶徒,所作所为简直惊世骇俗。待到柳渊说完,急忙问了一句,“这少年说的可是真的?”古员外急忙答道:“句句属实啊,大人,临近几个村上千的村民都看到了。”门外村民也纷纷大声作证。
这时杨义满又说了一句:“大人,听说这武将的爹叫温千宝,在朝中为官。”云知县一听终于想起了温贺是谁,不由得有些看不起的说道:“哼,我道是谁,原来是个靠父辈余荫才当谋得官职的一介白衣。竟然到这里来胡作非为,你们等着,本官这就派人快马加鞭,去请他过来询问,若是属实,必当告于知府,奏请布政使大人斩了他!”
话音刚落,只听见外面有人喝到:“嘿,好大的口气。”众人纷纷回头,只见一位服饰华丽的青年横冲直撞的纵马撞开众人,直至衙门方才下马,带着身后二十多位护卫打扮的男子,大步走来。云知县见他如此无理,不由得大怒,“什么人,胆敢擅闯公堂?”门口的捕快们听到知县喝问,急忙抽出腰刀拦住去路。
那青年见状,大声说道:“我奉我家少爷温贺之令,前来告诉大人,那杨家村口的众人乃是海寇,大人不必再审了,速速让乡民退去便是。”
云知县不由得怒道:“你说不审就不审,哪有这样的道理,本官不和你理论,快回去叫你家少爷亲自来解释。”
那青年推开拦路的捕快,走进大堂说道:“我家少爷没空,要知道,我家老爷......”
杨义满见这奴才如此嚣张,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喝道:“公堂上见了大人为何不跪?你可有功名在身?”
云知县见状也不由得问道:“对啊?你为何不跪?”那青年一愣,随即怒道:“你可知我是温家的人?一个小小县官,也敢叫我跪?”
这一句可当真把云知县气得不轻。本来,顾忌温家势大,因此心中强忍怒气。不料这一个家奴,也敢对自己如此轻蔑,顿时书生脾气上来,再也忍不住了。云知县大声喝道:“我不知道什么温家,我只知道朝廷律例,只知道要秉公执法。来呀,先让这大胆狂徒跪下。”那青年家奴跟随温贺,向来骄横跋扈,大小官员见了他,也大多给他面子,不料今日竟然碰到这个认死理的愣头青,心中一急,叫道:“大胆!”知县闻言,怒火更炽:“究竟是谁大胆?扰乱公堂,还敢口出狂言,来人呀,给我拉下去打二十大板。”那家奴闻言破口大骂,转头对护卫喝到:“快点上,给我打死这芝麻官。”众护卫不由得蠢蠢欲动。云知县急忙一拍惊堂木,嘶声喝道,“谁敢?本官就坐在这里,我看谁敢殴打朝廷命官?来人,给我堵住这狂徒的嘴,再打三十大板!”云焕在古桥县为官二十年深得人心,众捕快见那家奴对知县如此无礼,心中早已愤愤不平。再看到那些护卫似乎还敢造次,纷纷拔出腰刀,与他们对峙。
衙役打完五十大板,才把晕死过去的青年扔出大堂,温家护卫赶紧接过青年,上马一溜烟的去了。云知县坐在堂上,见温家众人去得远了,才吐了口气,赫然发现一身官服已被冷汗浸得湿透。心里明白,自己这次恐怕闯下了大祸。那家奴如此骄狂,必然有所倚仗,温千宝官至文渊阁大学士,门生众多,权倾朝野,深得皇帝倚重,更有兄弟在都察院作巡查御史,自己得罪了温家,那是凶多吉少。但如今已是骑虎难下,不能回头了。
定了定神,让堂下围观众人散去,留下胡员外,杨义满,杨兴,柳渊四人。沉声说道:“那家奴都敢如此猖狂,温贺仗着父亲权势,必然不会认罪。多半还会倒打一耙,诬蔑本官与你们。我这就把本案的卷宗移交给知府大人。温家想要在两江道一手遮天,也没那么容易。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写一封信让衙役连同卷宗一起带往柏江府。你们也跟着去吧。”
云知县踱了两步回头问到:“杨秀才,听说你是修士?”杨义满点了点头道:“回大人,正是。”知县点点头说:那好,此去柏江府,我正担心温贺会不会在路上拦截。有一个修士,那就放心多了,古员外和保长就不要去了,人太多引人注目。等我写了信,你们即刻动身。”说完便挥了挥手,四人行了一礼退下,各自回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