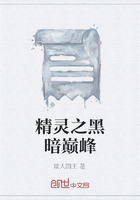焦元在回忆村委会大院演出那天晚上,蔡宝华本不想去凑那份热闹,可是,焦元超出这十来年的温柔,一反常态,在蔡宝华那张脏兮兮的脸上狂吻一顿。
嘻笑颜开的哄着蔡宝华说:“他爹,一晃有十年你都不亲我,是不是把我忘了,我可是你媳妇儿呀。顿顿给你做饭吃,天天给你捂被窝,今晚媳妇儿要你坐在我身边看节目,好吗?什么都不用你做也不用说话,你媳妇儿就想让亲老公陪着,省得别人乱猜疑瞎心思。有你在身边,那些骚爷们也免得动心眼儿!”
“我说焦元,咱都四十多岁的人了,哪有那份闲心发的那份干巴贱呢?有啥亊你就直说吧,别象小青年那样腻歪好不好!我******受不了女人起腻。”
“真没劲,亲近还分岁数大小,盖嫂都五十好几的人,文礼大哥又是那样,有人看见说,盖嫂经常亲文礼大哥那张干瘦的脸呢。那还是个瘫了十五年的男人呢,我家宝华又没老,亲近亲近还有啥说的?今后,我让我家宝华好好享受,每天晚上准给你做两个好菜,再喝上贰两,一辈子辛苦你了。”
“别说了,陪你就是好了吧?许下那些愿不还,让人空欢喜,更难受。好吧,今晚上我抱着你看节目,这样总可以了吧?”
焦元一个人在平江市,在她和夏明海那套专用住宅里,在回想亊发那天晚上,她的仲林儿一些细节,他和马兰之间,马兰与盖振东之间,总之,这三个人是早早晚晚会有这一天的,早晚都会搞成这样。
想起儿子拨打电话,每次问到在哪时,儿子总是把电话挂断,心里知道蔡仲林恨她这位妈妈,可是,她心里也有好多苦衷。借种生子的事和自己儿子实在难以出口,她估计乡亲们的传闻,仲林一定能够听道,无须细说。现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儿子对自己恨之入骨。
焦元在呈祥出来六七天的时间里,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孤寂,他拨通了夏明海的电话。
“明海哥,你在听吗?能来平江吗?我一个人实在熬不住了,能来快点吧!”电话说到一半,焦元哭的说不下去,索性挂断。
夏明海出差昨天刚到家,昨晚听说马成龙大哥病的历害,只因女儿没和蔡仲林在一起,和盖振东私奔都是猜测,谁都沒个准信,唯一的女儿出来这宗事,光明磊落一生的马成龙一股暗火,六天内米水未尽,夏明海去看望时,已是弥留之际,于今日早晨驾鹤西去。昨夜,今天一个上午,都在忙于马成龙的葬礼——
夏明海接完电话,到堂屋和正在玩麻将的张敏撒个谎说:“哎!张敏,公司那头出点差头,我得马上去一下,太晚就不回来了,不必等我。”
他媳妇儿忙着和六并,哼儿哈儿的应着。她根本不管夏明海做啥,早已沉迷于第二国粹——麻将牌之中……
夏明海的城市猎人停进车库,三歩并作两步走进房间。
“元妹子,我是你哥,别这样,我们己经耐过来二十年的纯洁友谊,别这样毁掉好吗?”
“不好!从今天起,我不做妹妹,我要一个孩子,晚年时我不能一个人过,你听明白了吗?我再说一遍,儿子恨我离我而去,我算好日子,我再生个孩子,到六十多岁他二十左右,正好给我作伴,你这回听明白了吗?”
“元妹子,我夏明海可以为你做一切,但这种亊你万万想不得,你明海哥和你虽然没有血缘关系,可是,在元妹妹叫我第一声哥哥那刻起,我就给自己约法三章。简单说吧。尽到一个做兄长之己任。一定保护元妹一生平安,这就够了。”
“明海哥,焦元原想从现在起我不叫你哥了,情愿做你的性情中人,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意已决,你酌量,你的元妹子太苦了。
有个词你该不陌生吧,“******”,元妹是******时才想到的。死鬼活着时他是个废男人,他不在了,在世时他也不管这类事,明海,只求你帮助,以后你愿意我随时接受,否则,不缠着你!”
“明海,从现在起我真不想叫你哥哥了,是从內心情愿做你的性情中人,不管你答应不答应,我意已决,你酌量,你的元妹子并不是性保守女人,但也不是太随便放荡女人。以后你愿意我随时接受……”
“元妹妹,我不能顺从你的意愿,现在不能,永远都不能。咱毕竟不是二十多岁青年人。沒有那份火热的激情。
二十年前的冷面西施焦元,仍然光彩照人,二十年的君子哥哥此刻没有失去理智。他知道元妹妹很苦,现在还是哀期,他不能脱去正人君子外衣,更不能和心中敬重的义妹媾合与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