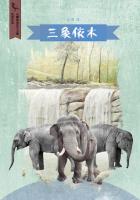她让我想起了家楼下的傻妹。傻妹的头发和她一样长。
其实傻妹已经五十多岁了,因为大家一直这么叫她,也就叫成了习惯,仿佛本来就是她的名字一样。听母亲说她嫁过来的时候,傻妹已经傻了。傻妹的故事只有那些白发苍苍的老人才知道,传到我耳朵里的都只剩概要。我只知道那天傻妹的父母吵架,本来她妈准备给她剪头发,手里还拿着剪刀,她爸撩起手掌要打她妈,她妈情急之中拿剪刀向前一捅,她爸就倒下了。她妈一边哭一边关照她在家里什么地方都不要去,自己带着丈夫去医院抢救,可是都没有再回来。从那以后,她一看到剪刀就害怕,人也变得痴痴呆呆,整天捧着头发自言自语。开始的时候她见人就躲,等完全傻掉后见人也不害怕了,反而会迎上去,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说是回来就会给她剪头发了。
关于傻妹的故事有很多版本,我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我记得的只有这一个。
乌子镇是一个贫穷的江南小镇,随着紫红色的晚霞退去,镇上就昏暗起来,知了的叫嚷渐渐微弱,几欲消失,除了偶尔传来一两声蟋蟀的鸣叫,便只有河水流过石缝时擦出的哗哗声。烟囱吐尽了灰烟,蝙蝠撑着翅膀哑哑乱飞,拼命扑赶着最后一丝光线。
小巷疲倦地向着黑暗铺去,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散发着泥土的焦味,家家户户的门都敞开着,门板上的油漆大多已经剥落,塑料纱窗中嵌满了油黑的污垢,有的挂不住一头耷拉下来,无力地晃动着。老人们坐在门口,摇着蒲扇,男的光着膀子,一身褐色的油腻,女的穿着宽松的衬衣,漏着两粒干瘪的乳房。屋子里几乎都是空空荡荡的,除了巨大的落地柜和短小的日光灯,一无所有。孩子们坐在地上,一身泥泞,自娱自乐地用手指在地板缝中乱抠。大人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孩子玩耍,有的抬起头望我,直到我收回视线,都没有一点神色的变化。
我从小镇的一头走到结束,直到被河流阻隔,没有看见一个鲜活的人,也没有再看见那个拖着长发的疯女人。
这是来到乌子镇的第二天,第一天下雨,我们便在小镇一头的宾馆里休息,今天雨过天晴了,胡老师让我们在镇上先逛一圈,熟悉之后明天再去乌子园测绘。乌子园我从没听说过,就连乌子镇也是名不见经传的,我只知道那是一座荒废的私家园林,原本住在里面的家族历史上是当官的,****的时候一家人全被整死了,留下了园子几经转折竟无人管理,任凭风吹雨打自生自灭。不过里面的建筑却是货真价实的清代式样,建造至今也有三百多年。我本以为那里会是杂草丛生一片狼藉,没想到却花团锦簇树木蓊郁;池水也不是想象中被浮萍掩盖的样子弥漫着臭气,而是微波粼粼,甚至有五颜六色的金鱼穿梭其中;飞挑的屋檐没有被蜘蛛网尘封,反而精神抖擞闪着金光;柱子上栏杆上楼梯上没有一丝灰尘,再抬头看看,连天花板也一尘不染。
测绘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要把整幢几百平米的房子浓缩在几张纸上,每一个细节的比例都要保留,画一条几厘米的直线,我们要拿着皮尺从一头奔到另一头,画一扇窗,我们要里里外外上上下下测量二十几个相似但又不能混淆的数据;这些房子造得很是奇怪,一堵连续的墙,室内和室外的厚度竟然会不一样,有的柱子嵌进墙里面,只露出一小部分,还要根据几何原理计算出它的半径;天花就更难测了,不但有倾斜角度,而且够不着,拿着卷尺徒手笔画又失精确,想踩在桌椅上也不行——它们也是被保护的测绘对象。
胡老师说这里面的家具都是古董,只能看,最多摸,千万不能坐上去,更别说当其他用途了。刚开始几天我们不知道,测累了就往椅子上一坐,甚至有些人还躺在榻上,但后来他们都受到了惩罚。事实上,我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坚固的椅子会变得如此娇贵,难道它们被造出来不是用来坐的么?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只能坐在地上,贴着炎热的地砖,还要抵抗爬虫的侵扰。
梦中的我正在测量一扇窗,卷尺上的数据是三厘米,我在纸上写五厘米,卷尺上的数据是六毫米,我写十八毫米。我很痛快,但又很慌,担心被发现。正当我把最后一个数据测完的时候,突然听见一个尖锐的声音:“你在测些什么东西!”惊慌失措间,一失手,记录册从窗口落了下去。我怕她赶在我之前捡到,立即飞奔下楼。
狭窄的弄堂,两边肮脏的墙面向上延伸,挤出一条灰蓝的天空,原来不是乌子园,而是我的家。
测完了?母亲一边把楼梯踏得咯咯响,一边质问我。
记录册落进水沟里,我不测了!我用脚尖把本子捅进了阴沟。
今天不测就明天测,总归是你的任务,逃也逃不了。
我就不测!我鼓起勇气,怒目瞪着她,这个地方我再也呆不下去了!
说完这句话,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还是半夜,李丹心轻轻地打着鼾,月光从窗帘缝中照进来,在墙上拉出一道湿润的黄光。
我讨厌这个家。从小到大就一直窝在这十平方米里,三个人,两张床,还是上下铺的,挤得像最劣等的火车车厢,一张桌子又吃饭又写字还放物品,窗口望出去,一米半开外就是石墙,从来就没有阳光。本来去年年底说要拆迁了,我兴奋了几天几夜。动迁组迟迟没有出现,却又来了消息,说不拆了,而且还要重点保护起来,因为是上海仅剩的几幢石库门建筑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无法安静一秒,母亲也心情极坏,我们就每天在这个装满火药的弹丸之地摩擦火花。测绘前一晚,我要看电视,她要我早点睡觉,我不肯,于是她一伸手把电视机关了,我再一伸手又把它打开,就这样开开关关几十下,电视机突然呲的一声寿终正寝了。母亲上前敲敲打打也无济于事,我不敢再发出一点声音,转身就闭上眼睛。黑暗中听父亲说,别弄了,明天去修修看,修不好就买一个新的吧。母亲带着哭腔说,买!买!现在哪还有这么小的电视机卖,买大了放什么地方!
薛刚架着木梯去测屋顶,正爬到一半,被搭着的窗户突然豁开了,木梯向一边滑去,薛刚哎哟一声从半空坠落下来。当大家再把视线移回窗户时,它已经关上了。
你没事吧?陈洁把薛刚从地上扶起。
薛刚试着走了几步,摇摇头说没事。
这个园子有点不正常!范学中说。
他这句话说出了大家的心事。
是的,我昨天早上把测绘记录的本子放在桌上,回头就不见了,今天竟然在大门口的垃圾桶里找到了,我本来以为是哪个同学作弄我呢,但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很蹊跷,现在看来……
对了!会客厅里本来有一只大花瓶,昨天我还和蔡薇薇说这个花瓶雕刻得那么精细,肯定很昂贵,但想不到今天就没了,这绝对不会是我们拿的,那么大的瓶子又没地方藏,捧在手里,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这里有鬼!我昨天测窗户的时候,看见对面房间里飘过一个黑影!
啊?大家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是真的,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敢肯定他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因为他走路的样子很怪,好像是一跳一跳的。
听说这里住的人在****的时候都被整死了。
别吓唬人!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第一天下雨你们都在宾馆里休息,但是我闲着没事做,就撑着伞来这里看看。当时雨很大,我浑身都湿了,就走到会客厅避雨,我坐在太师椅上,明明看见对面房子二楼的窗户是打开的,等雨小一点,我就逛了一圈园子,再回来的时候,那些窗就关上了。我本以为是风吹的,但是整整一排,都关得严严实实,这风也太邪门了吧。
你的意思是这里有人住?我也不知道,那时天暗了,我觉得有点害怕就回来了。
这里怎么会有人住呢?我们都测两天了,每个角落都被我们测过,如果有人住着,还不被发现?
这时程晨从房子里走出来。陈洁指着那扇窗户问他,是你前面在二楼么?
程晨一脸迷茫,说,没有,我一直在会客厅,怎么会跑到那里去?
那你看见有陌生人走到会客厅里来么?
没,怎么回事?
陈洁拉了拉薛刚的手说,我们上楼去看看吧。
大家纷纷说要一起去看。
可是当我们走上去,才发现根本没有人,连影子也没有。一束阳光照射进来,窗框的花纹安静地斜躺在地板上。
我又一次看到长发女子时,她正在乌子园门口向内张望,看见我就惊叫一声逃开了。她一边逃一边回头望,见我没有追过去,就慢慢停下脚步。她的眼睛很大,但是毫无神气,嘴边还挂着饭黏子。她的双手紧张地捂着肚子,歪着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我,长发从一侧垂下来,看上去像有两个身体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