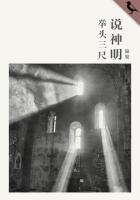“想不起一件事的英语怎么讲的时候就讲法语,走路要脚尖朝外,还有,记住自己是谁。”
——红心皇后《爱丽丝镜中奇遇》
乔伊
圣保罗姐妹济贫院[1]。
我想我的工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必须时刻鞭笞自己容易变易的软弱灵魂。我内心深处——与所有纯洁羔羊们的内心深处一样——确然有炽热的红炭。但死灰同样堆积,所以大多数时候只能冒一点烟,火是轻易燃不起来的。也许我应该常备一把扫帚。永葆心灵洁净是何等困难,每当意识到这一点,我都感到惨然得很。
我从书桌对面打开的窗户向外眺望,严冬已经降临,壁炉里空空荡荡,一丝火苗也无。我活动活动手腕,埋怨自己思绪迟滞,希望能继续奋笔工作。空气凛冽,手搁在稿纸上,仿佛触着冰面似的。太阳很快沉落,白昼的光亮向夜晚的昏黑过渡,窗外世界恍如静悄悄沉入幽深海底。
已而下起雪来。寒风裹挟细细冰屑敲打我的窗子,一个劲簌簌作响,低声细语一般。我所在的济贫院位于城市偏僻的巷落群里,这会大概不会有客人造访。这么一想,顿时被更深的凄寂感笼罩。我别起十指,对着圣像祈祷:
“上帝,请让我从蚀骨的孤独和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吧……”
很多年后我偶尔会后悔当时的祈祷。
因为下一秒,我扣锁不牢的房门就被撞开,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我。
“不用害怕,亲爱的神父。”
对方喉音低沉,简直和女人一样柔弱,身形被笼罩在斗篷之下。他闯进门来,我顿时感到麻烦像裹挟雪片的穿堂风一样吹过整个房间。
“我身上一个镍币都没有。”我说,从上到下扫视他。
“没关系,没关系。”他用亲切的老朋友般的语调回答,“我只想找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为了避免麻烦,我需要暂时把您捆绑起来,我很抱歉。”
“难道你不是麻烦的源头吗……”我咕哝了一声。他装作没有听到,持枪轻捷地靠近我,从斗篷里掏出绳索,动作熟练地为我全身绑上菱形束缚。随后坐在我的床边,卸下落了细雪的斗篷。
他是一个身材瘦长、蒜头鼻、其貌不扬的青年——与其说是青年,不如说更像一个闷闷不乐的少年,可能小时候深受神经性官能症苦恼。他两颊凹陷,右半边脸孔上划着一道泛白的疤痕。我平时爱读侦探小说,心想这样的外形可以算是歹徒标配了——不过既然敢露出斗篷,应当也经过一番伪饰。他脱下上衣,露出腹部缠着的污浊绷带。
“神父,您这里有医疗用品吗?”
“在壁橱里。”我用下巴指给他看。
“神父,您好像并不紧张。”他一边简单收拾自己的伤处,一边露出古怪的表情注视我。
“上帝与他的子民同在。”
他嗤笑了一声。
“……您的名字叫什么?”
“乔伊。”
“那我就叫您乔乔好了。”他亲切地对我道,“不要露出这么苦涩的表情。记住,上帝与您同在。”
“那么,我的孩子,你叫什么?”
“请不要称呼我为您的孩子,乔乔。不过出于礼貌我还是会回答您。您可以叫我莱昂。”
“是真名吗?”
“当然不是……”他手法快捷地处理完伤口,脸色微微发白,但仍然轻快地回答,“我们这一行遇见外人问名字,都这么回答。”
“您是杀手吗,莱昂先生?”
“您可以这么认为。其实这只是我的副业。”
“那么主业是……”
“我很荣幸地告诉您,身在您面前的是一位未来的画家。”
“冬天的夜晚是枯燥乏味的。”莱昂用唱歌般的音调说,“不如这样,我让您看看我的习作好了。”
他不等我同意,变魔术般从怀里抽出一张又一张画来,一股脑儿推到我面前。油画与水彩画混杂在一起。他目不转睛地盯住我。
“……”我承认我当时出于职业偏见,对他的作品满含轻视。然而出于自身安全考虑,我还是认真打量起他的画作——他的小口径手枪还在大腿上搁着呐。
然而一眼望去,我不得不感到吃惊了。这些虽然是技巧幼稚、一点没经过系统训练的画作,却孕育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怪力。它冲我直奔而来。我不禁移开目光,重新将莱昂打量了一番。莱昂凝视着我,眼神竟然有点不安——我想是我看错了——兼有强烈的自负。
“您觉得怎么样?虽然都是些不值一提的东西……”
莱昂故意用不屑一顾的口吻问我。坦白说,我对他的画之出色感到怪异的赞叹的同时,也被他佯装傲慢的举止搞得哭笑不得。真想故意回答“确实不值一提,您的定位很准确”之类讥诮的话。
——不过,幸好我在刹那之间避开了这种有损人格的行为。这一方面是我灵魂原本高尚的缘故,另一方面也由于他的画确实拥有魅力,将我的反感情绪瞬间压制。
好吧,我承认手枪也起了一点作用。
“画得挺不错。”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莱昂带来的画大多是景物画,偶尔有人像。其中有一幅至今我历历不忘。那是一幅少年的肖像。神态傲慢,身形挺拔,眉眼和莱昂有几分相似,不过清秀得多,脸孔也光洁。身穿笔挺深蓝制服。整幅画的背景都是奇妙调和的淡淡蓝色。画者用蘸着单色的笔,笨拙地往画布上拓,我看那粗放的笔触,好像他只管把颜色粘上去就算数似的。那种蓝是自然界并不存在的色泽,完全率性涂抹而成,然而仔细观察便可想见作者是有敏锐的色彩感的。另外他的整体观感都十分调和,我几乎立刻被那种汩汩流动般的优美的郁悒打动。
“这幅尤其好。”我不得不坦率直言。
一定是我的错觉……莱昂听了我的赞美,脸色竟然微微发红。随即露出不信任的、自嘲般的冷淡表情,望一眼画又瞥我一眼,似乎在公平地作比较。我们一时相对沉默。我百无聊赖,只能继续盯着画瞧:“这个孩子是谁?”
“……我弟弟。”
他生硬地回答。之前流淌在我们之中近乎戏谑的气氛因为这个词而僵化了一般。碍于这种气氛,我不好意思再开口。但是莱昂的表情仿佛期待我多做一点评价。并且眼神锐利,明显在说:“敷衍的话有你好看的。”
既然这样就只能……我硬着头皮开始发表意见。绑在身后的手拼命画十字,希望他不会因为我可能的用词失误给我来一发。
当时我信口说了什么来着?我已经差不多忘光了……我想大概是把在神学院里学习绘画课程的时候那一套术语拿出来应付。什么技巧很靠不住啦,观察细节不够认真啦,主题过于矫情……啊,上帝保佑。莱昂一声不吭地听我讲,目光炯炯。当我口干舌燥地说完一套之后,他依然缄默不语。我吓得心脏差点儿停跳。过了很久,他终于弯起嘴角,露出比哭还难看的微笑——与其说是微笑,不如称作讥讽的痉挛更恰当。
“我弟弟在战争里死了。”
他说。我一时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安慰他一番。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出奇地天真无邪。我竟莫名其妙被他的音调打动,半安抚地问:“您的职业大概也很辛苦吧?”
“没错,至少我是。”
“你是怎么受了伤?……”
“暗杀失败啦。”他耸耸肩,“说实话,我觉得那个老恶棍即使我不杀,也很快就要死了。”
“……谁?”
他说出一个闻名遐迩的财阀集团首脑的名字。
“那么你退休之后想干画家这行?”
“您看我能干得了吗?”
他一瞬间又恢复了嬉皮笑脸的表情,凑上来问。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答不上来,作为一个只在神学院里学过几年艺术课程的老神甫,哪里有资格替别人做职业规划?何况莱昂这一行是否真的能平安退休还是个问题……不过他的神态越来越认真,我提心吊胆,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
“我明天早上离开这儿……运气好的话,这一单做完我就试试能不能金盆洗手。”莱昂思索了一会儿,“我可能会回家……我家在一座港口城市,具体在哪儿您就用不着操心了。总之,景色相当秀丽。我可以多练习风景画……现在我画得不好,还不行。可惜不能再找您指教啦。”
他见我答得不情愿,便用一种略带自责似的腔调说。该死,一定是我看了太多情节离奇的犯罪小说的缘故。或者他故意做出这样的语调来逗弄我也说不定。
雪片纷飞的暮色里,一位想当画家的杀手闯进我萧条的济贫院,逼我为他做艺术鉴定。我感到一阵眩晕,不可思议的非现实感从脑髓一直蔓延到指尖。
“我来给您讲一点我以前的事吧?特别是我从何时起开始想当画师的——长夜漫漫,用来消遣是不错的故事呢。”他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倚坐在床边便开始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