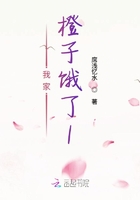客厅透明玻璃的茶几上,钥匙安静地放着,下面压着一张粉红色的信纸。予之的行李还未来得及放好,这一幕便迫不及待地闯入他的眼帘。
他大踏步地走过去,拿起那张纸,上面是简文工工整整的字迹,他曾经嘲笑她的字就像是一个被罚抄作业的小学生,一笔一划,格外工整,但是却显得幼稚。
此时,这些幼稚的笔迹清晰地落在粉红色的信纸上,每一句都看得予之心乱如麻。
予之:
亲爱的,请允许我最后一次这么叫你。我想,这把钥匙不论我多么依依不舍,最终还是要还给你的。虽然那天夜里你最后还是接纳了我,但是我心里却非常明白,我并不曾真正走入过你的内心。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只是我一厢情愿的爱情。你从头至尾都不曾对我付出过爱情。
可是,我却并不苛求,我曾经就那么卑微地想过,只要你对我好,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是同情还是慈悲,我都接受,我都愿意假装你是真的爱上了我,我们可以是很好很和谐的一对。
但是,那天晚上,你将我拒之门外,然后又开门温柔地收留了我,你以为我是瞎子吗?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我能够感受到你内心的那份煎熬,也能够体会到你对我的纠结和挣扎。一份好的爱情,怎么可能是这样?一份为你所接纳的爱情,怎么会令你如此痛苦。
回想这么一段时间以来,你对我的点点滴滴,想必就是一份慈悲而已。你感激我对你付出的,你亦愿意付出你的真心,但是无论你怎么努力,你对我都没有爱,不是吗?予之,你不需要像你的名字一般给予,你在我心中,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你需要的就是接纳,而不需要任何的给予。
原谅我的爱如此卑微。
一直以来我都以为自己是一个骄傲的人,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只是人世这般,所谓一物降一物,一点不假。我还记得第一次你出现在我的面前,你到报社来找我,在报社门口的紫藤花下,你远远地站着,我远远地望着你片刻,觉得这就好像是上天赐予我的机会,让我这颗已经不再有激情的,几近僵硬的心又重新恢复了活力。
我曾经不止一次的这么想过,如果我能够再年轻十岁,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你离开。
我们之所以悲哀,是因为我们留不住岁月。而更加可悲的是,在留不住的岁月里,遇到了想留而留不住的人。
除了一声叹息,我还能做一些什么呢?
关于健慈妇幼保健院的事情,我已经追查到国恩医院关于1980年~1985年之间早产儿的记录和档案遗失的事情,我感觉这份档案遗失的时间非常蹊跷,就在韩志庆辞职后的一个月,国恩医院档案库突然遭遇了一场大火,而目前电脑上存有的档案,只是从1990年才开始电脑建档的,我不敢确定这场事故是否与你的身世有关。……我一定会倾尽所能为你找出身世之谜,找到健慈集团那些谜题的解法,相信我,这或许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也是我最后为你做的事情。
你不必感激,也不必内疚,爱情本身就不应该有任何的负累,我为你付出,是因为我爱你,这么做我很开心且轻松。
予之,收起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做回那年紫藤花下洒脱不羁的男子,这便是我所想往的全部。
爱你的
文
予之跌坐在茶几前面的沙发里,双眼发直。原本想好的要对简文解释的话,现在看来完全是多余的了,她好像已经完全想明白了,予之觉得一阵轻松,但是轻松之后又是一阵空虚,空洞,最后脑子一片空白。
事情的转变实在太快,快得让他感觉到眩晕。飞机上的一路,予之都在打着腹稿,组织着语言,计划对简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就像是一个训练有素,准备充分的上阵将领,带着千军万马计划打一场硬仗,结果,却一兵未出,一弹未发,对方便将整座城池拱手相让,最后,反倒衬托出对手的成人之美。看似胜利,但其中失落难以言明。
予之为自己煮了一壶胶囊咖啡,窝在沙发里,让那一点点的焦苦味道浸蚀到自己的全身,他随手拿起手边的电视机遥控器,花花绿绿的画面令沉默的斗室突然喧闹起来,而他也在这种呱噪中慢慢让自己从这种突然逆转的关系里适应过来,他觉得这样也好,省去了自己解释的麻烦,而再次见面的话,自己也不用因为愧疚而觉得尴尬。他想着第一次见到简文时,自己的样子。他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也记不得那报社的门口是不是有紫藤花,亦记不得自己的穿着,甚至连那一天简文的面目都已经模糊了。
她却还清晰的记得那天紫藤花下的自己——爱与不爱的差距如此之大。
他不能勉强自己,他叹了一口气,在心里不停地对简文说着“对不起”。
窗外的太阳一点点往下沉,就像是予之的一颗心,升起来,又慢慢地向下滑,说起来,和一个不爱的人分手,原本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往往因为伴随着对对方的伤害,伴随着内心的负疚,而让一场分手看起来像是对负心汉的讨伐。
此时此刻,予之就在内心讨伐着自己。
“昨日下午5时许,正值下班高峰期,一起乘客跌落地铁轨道身亡的惨剧在陕西南路站上演……”此时,电视里的新闻画面一转,地铁下班高峰期的嘈杂和混乱充斥着整个屏幕。
这种事情好像隔一段时间就会爆出一起,予之对这种新闻已经有些麻木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媒体会反复报道这些“负能量”的人间惨剧。
他举着遥控器试图转台,突然新闻画面变成一张死者生前照片的特写,虽然在眼睛部位打了马赛克,但是予之依旧辨认出这张脸——简文?
予之举着遥控器的手僵在空中三五秒,霎时间,因为惊恐和紧张,令他的脸色变得惨白,难道真的是简文?他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他待细看时,画面已经转到了别的新闻上。
算一算时间,这新闻是转播头一天的,那么这里说的“昨日”也就是前天了,很难想象,他与麦子在三亚的海滩边上享受浪漫和暧昧的同时,简文却在这里经历了如此悲惨的一幕。
他拿起手边的手机,摁下优先联系人的号码,简文的手机通了,彩铃的歌声令予之内心一阵抽搐,那首去世了的歌手的声音很悲戚的传来,“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设置的,予之竟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听过简文的手机彩铃。
手机接通了,予之松了一口气,“这是不是意味着新闻报道的主角并不是简文?”
“喂?”声音苍老而干涩,并不是简文的声音。
“简文,是我。”尽管听出来这不是简文的声音,予之依旧很不甘心地这样回答对方。
“您是杜予之先生吧?我是简文的爸爸,我们今天试过联系您,但是没有打通您的号码。简文……遇到地铁事故……意外身亡了……”
“意外身亡!”这四个字犹如洪水猛兽一般瞬间将予之淹没,至于电话那头又说了些什么,他完全没有听清楚。一瞬间,比先前更大的惊恐和紧张,夹杂着悲哀,愧疚,懊悔,愤怒和绝望,各种心情一并涌上心头,予之眼前一阵天旋地转,胃里陡然抽搐,翻江倒海起来,他呼吸困难,喉咙“咯咯”作响……
终于,他奔将到卫生间里, 如同一个醉酒的人一般,趴在马桶上不停地呕吐,直到将胃里的所有内容都吐了个一干二净,他还不停的干呕,吐出黄白色的胃液,夹杂着嗓子眼里的一点点血丝。
“你就是杜予之?文文的男朋友?”
显然,简文没有少在父母面前介绍自己,当老人听见“杜予之”这三个字的时候,便很自然地将“男朋友”挂在了嘴上。
予之很尴尬地微笑了,他的这个笑容反而增添了他在老人面前的好感,在对方看来,他尴尬的笑容,正是因为简文的去世而强颜欢笑的表现。
说是男朋友反倒更好,予之心里还惦念着简文生前对健慈集团的调查,据他所知,简文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健慈集团,许健慈、韩志庆的调查,按道理说,在她的电脑以及笔记本上都应该有相关的记录的。作为“男朋友”的身份与她父母套近乎,拿到她生前的这些资料也就顺理成章了。
但是当他问及简文的遗物时,简文父亲的回答着实令他吃了一惊:
“在你来之前,文文报社的同事来过了,带走了她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东西。”
予之心里“咯噔”一下,到底是谁捷足先登了?虽然不抱希望,但是他依旧问道,“电脑呢?”
“他说电脑是报社配的,我们想着我们老人也不太懂那个东西,而那个人看着也彬彬有礼,所以也就没有怀疑,让他带走了。”
予之眉头紧锁,那台电脑并不是什么报社配置的,而是前一年,他为了答谢简文为自己身世奔波,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大约看出了予之的表情不对劲,简文的父亲紧张地问。
为了不让老人担心,予之微微一笑,摇摇头。“没有什么,只是想到电脑里有我们一起出游的照片,感觉很可惜。”
“您或许可以找到文文的报社要回来。”老人很热情又带点歉疚地说。
予之暗暗叹了一口气,他们对自己女儿的事情真是了解得太少了,而对于她遗留下来的物品又是如此的不谨慎。
“这两天来了多少人?就她那一个同事吗?”
“说起来确实很奇怪,在那个同事来了之后,就今天早晨,又来了好几个她们报社的人,有一位还是他们的领导,送了一些钱和简文在报社遗留的东西。”予之点点头,这群人看来才是正牌的“报社同事”。
“还有一个人来过。”
“也是同事?”
老人摇摇头,“他只说是简文的朋友,听见简文的电脑被人带走以后,那个人也问了跟你差不多的话。”
“他长得什么样子?”
“你别说,他举手投足跟你有几分相似。个子跟你差不多吧,国字脸,大眼睛,我开始还以为他是你。”
看来,该来的人都来过了,不该来的也都来了,他杜予之其实是最后一个来的,他在心里暗自苦笑。
“他带走了什么吗?”
“他什么都没有带走,还留了一些钱。我觉得这样不太合适,他却说和简文都是好友,叫我们一定要收下。”老人若有所思地说,“他问了一些很奇怪的话,譬如警方对文文的死是不是确定是意外,地铁站有没有录像,还问了一下那个最早来的同事的相貌,但是我实在想不起那个人的相貌。”
这个人,不用说,予之也知道是谁。只是为什么连生对简文的死如此关心,难道他也在追查健慈集团?又或者,他对简文的死有些什么疑问?
“能跟我说一下,这三拨人来这里的先后秩序吗?”予之心下一动,又抱着希望追问了一句。
虽然不太了解予之的目的,但是老人还是很仔细地回忆,然后说:“她的同事最早来,然后是那个跟你长得有几分似的人,最后是她报社的一群人……”
予之脸色舒展了一些,如果是这样,报社送来的简文的遗物还没有被人领走。或许这些遗物里有什么线索也未可知。
“能让我看看报社送过来的遗物吗?”
予之看到这些遗物,终于明白刚才老人为什么说,差点将连生认成了自己。因为在偌大的纸箱里,有一沓自己的照片,这些照片有的是他们一起出去旅游拍的,有的是她偷拍的,照片里的自己,有的是在伏案工作,有的是在看球赛,有的是在打游戏,甚至还有一张是自己在出庭……
想不到她竟然对自己如此用心,予之蹙眉叹息,眼泪差一点要夺眶而出。
除了这些照片,纸箱里还有一本厚厚的名片本,他随手翻来,竟然“赵连生”三个字落入眼底,予之有种被下了蛊,永远逃不掉的感觉。
他合上名片本,又看了简文的采访本,着实就像天书,所有文字都是“鬼画符”。也难怪,记者采访时为了要迅速记录对方说的内容,所以写字速度要快,很多内容都用符号来代替,大部分内容都只有记录着本人才能看得懂,外人看来就是一团乱麻。
简文的办公室遗物并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信息,予之拿了名片本想走。但是就在转眼的瞬间,他瞥见一个小破孩模样的钥匙扣,在印象里,简文并没有对他说过有这么一个东西。这个钥匙扣很有趣的模样,小破孩滑稽而有趣,予之看了忍不住喜欢上了。
为了表示他这个“男朋友”的眷眷之情,予之将这个小破孩钥匙扣带走了,说是生前两个人感情的纪念,带回去做个念想——予之觉得,这么做似乎会给老人一点点安慰,至少,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个人对女儿的死是惦记的。
从简文的住处回到家,一路上,那个小破孩钥匙扣都躺在予之的上衣口袋里。虽然不是什么特别有故事的东西,但是予之一直都在惦记着这个小东西,心里模糊地想着与简文的相识与相处的点滴。
他依旧不喜欢她,他不愿意欺骗自己,亦不能因为她的死就凭空将她在自己内心的地位拔高。但是他也不能将她忘记,那些在一起的光景,她对他的好,她对他的付出,则是他永远都弥补不了的愧疚。
就这样一直到家,走过小区的绿化带,穿过那个小竹林,进了家门,予之的手里都紧紧地攥着这个小破孩的钥匙扣。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东西,简文居然没有告诉自己。予之将小破孩钥匙扣拿在手里反复把玩,心里充满了好奇。“难道这仅仅就是个钥匙扣?上面为什么没有钥匙?她没有用它来挂钥匙?”
予之将钥匙扣放到眼前仔细观察,最后发现小破孩的下半身有两处“裂缝”——与其说是裂缝,不如说是设计成这个样子的接口。他手一用力,裂缝处往上一翻,居然是一个U盘!这个突出的USB接口往上翻出来,倒是有几分像小破孩的******,配上那小破孩滑稽的表情,真是有趣极了,令予之忍俊不禁。
他将U盘插进电脑的USB接口,里面的内容并无特别之处,都是一些诸如上市公司的调研报告,这些报告并不太像是简文为了工作而收集的,倒是更像是一些“半成品”——譬如海叶医疗的调研记录,瑞和制药的研究报告写作框架,2012年医药行业年报数据分析……这些内容都非常专业,看起来应该是某个证券公司从事医药行业分析的研究员的工作调研报告。
最后予之打开了一个已然完成的研究报告,在报告的旁边,有几排用加粗的楷体记录的小字:“分析师:李云志 执业证书编号SA####### 工作邮箱:[email protected] 联系电话:021-xxxxxxxx”。
李云志!
就是前一阵被传畏罪跳楼自杀的新泰证券的研究所副所长,予之模糊地记得好几个关于李云志的新闻和微博,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关于李云志自杀的新闻。新泰证券,这不是麦子所在的证券公司吗?
即便真的是新泰证券与简文有些不愉快的过往,她也不至于对这家公司耿耿于怀,以至于连一个副所长的自杀都纠缠不清吧。予之对于简文这种睚眦必报的态度一直都报以不赞同的态度。
不过,待予之将U盘中的内容一一过目之后,发现事情似乎并不那般简单,一个叫“深度调研”的文件夹里,有一个名称是“健慈股份”的子文件夹,予之有些明白了,简文应该就是冲着这个“健慈股份”收藏这个U盘的。
这个李云志生前似乎对健慈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健慈股份非常感兴趣,他对这家公司的关注已经明显超出了一个正常的研究员调研的范围了。从健慈股份上市之前两年到最近一年的财务报表,都一一在列,而一些涉及关联交易、企业并购等敏感数据,都一一用红笔标注。但是奇怪的是,这个名叫健慈股份的文件夹里只有李云志搜集的数据和背景资料,却没有一篇关于健慈股份的调查报告,甚至连一点自己的评价内容都看不到。
予之认为这并不寻常,或者说,是李云志非常谨慎,并不将自己的调查结果和文字放在这样一个容易被遗落的小钥匙扣里。
总而言之,这个钥匙扣U盘储存的都是调研的素材和上市公司的背景资料,以及一些已经公开发布的研究报告,这些内容随时随地携带,方便自己在哪里都能够工作。予之也有这样的习惯,贴身带一个U盘,便于工作时及时取材。
简文是怎么得到李云志的这个U盘的呢?她又是怎么认识李云志的呢?
予之心底疑窦丛生。
畏罪自杀的研究员,意外身亡的记者,他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对健慈股份的调查,而从连生对简文父母的问话上,他在怀疑简文身亡的原因,很有可能他一直在对李云志的死亡原因进行调查,因为予之记得,第一篇关于李云志死亡的报道就是新时代财经连生的杰作。
自杀?意外?看似正常,但是予之嗅到了一点点与众不同的味道。
对于张若离发出的邀请,予之有些犹豫,因为他对上电视这种事情并不感冒,将自己推到台前,说一些可有可无的观点,也看不到观众的反应,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欢迎抑或就像是一个小丑。
而且,予之听说,一般人上镜头会变得比平时胖一倍,而他担心自己的国字脸到了屏幕上,就直接塞满了电视机的边框,要是这样,还不知道那些认识自己的财大学生,还有律所的同事,妇幼保健院的小护士们怎么嘲笑自己呢。
“你不要急着拒绝,你能不能先与我见一面,听一听我目前策划的选题?”
咖啡吧就在广电大厦的一楼大厅里,予之对这种建筑格局颇感新鲜。若离煞有介事地从随身的挎包里取出一个记事本,翻到某一页,递给予之。上面是一串人物的名单。这些名字,有的是予之认识的,有的是予之不认识的,他皱了皱眉,“这是什么?”
“你看觉得是什么?”
“嗯……这些人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嘛?这个黎家桓不是之前被查出老鼠仓的基金经理么?还有这个顾玉丽也是被查出IPO财务造假,被判市场禁入的。”
“你说对了。我是想综合近两年金融圈子的违规操作行为,做一期监管方面的节目。这个名单都是违规被查处的人。”
“这类节目,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呢。”予之皱着眉头,他不希望在电视节目中锋芒毕露。
“很简单,我不需要你来单个对他们行为做出什么评价,只需要你从证券法的角度谈谈目前我们的法律对从业人员有哪些约束,而现在市场中,容易越界的地方有哪些。”
予之点点头,听了若离的需求,他觉得就泛泛一谈,倒是也还可以接受。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名单。”若离伸手,在予之眼皮底下将记事本往后翻了一页。
这个名单进入予之的视线之后,他浑身便不由自主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这……这都是这两年金融圈子里非正常死亡的人?”其中,李云志的名字非常扎眼,予之看到这三个字,心里猛地一缩。
“你还是很有新闻敏感性的嘛,”若离对着予之微微一笑,“确实,这些人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人,但是你不要忽略了,他们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些违规的背景。”
“也一样的点评?”
“我们想了解,如果当事人违规,他们如果身亡了,那些利益受损的投资者的利益该如何维护。总不能因为人死了,这过错就不追究了吧。”
“当然,一般来说,需要偿还的债务,会让他的继承人偿还。”
“但是据我们了解到,这些非正常死亡的人中,大部分在身亡之后,他们的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个也需要我动动嘴?对这一现象进行评价?”
“其实不算是现象的评价,就是最直接的介绍适用哪些法律法规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鼓励他们在事件追诉期内维权。”
“你们的财经栏目倒是可以改成财经法制节目了。”予之开玩笑地说。
“我还真的想策划这么个法制栏目,其实很多投资客都是法盲。看着是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却不懂得运用法律知识。”
予之没有说话,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就像前几天在地铁站被撞的记者一样,完全可以找地铁站维权。”
予之听到她说起简文,心情不禁又黯淡了下来,“你怎么知道她不会维权呢?”
“就她父母那样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模样,怎么可能会想到维权?”
“你见过她父母?”予之眉头一皱,对若离的话有几分怀疑。
若离面上一红,“你还真够敏感的,地铁站出了这么一个大事儿,列车都延误了两个多小时,人山人海的,我们电视台自然要带着摄像机去现场了,我那天跟着摄像师一起去参与了现场报道,后面几天的追踪报道我都有份,我还亲自采访了她父母。”
“你们记者总是这么不近人情,人家越痛苦,你们越兴奋。”予之话音里的责备之意非常明显,令若离非常尴尬。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呀,如果没有我们的兴奋,你们这些观众也不可能知道别人的痛苦,更不可能去了解别人的痛苦,进而伸出援助之手。”
“但是更多的时候,你们的兴奋都像是在人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
若离眉头一皱,但是依旧耐着性子说,“这些不过是表象,我们的工作主要是一个信息的传播的平台和中介,谈不上伤口上撒盐。倒是律师这个职业,人家越痛苦你们还越赚钱。”
予之不经意地一笑,这美女伶牙俐齿不好惹呀。
“你也别顾着讨伐我,这节目你接是不接?”
予之沉默了半晌,“说起来,你们不会把我拍成个猪头三吧?”
若离“噗嗤”一声笑了,“你要是总说三道四,鸡蛋里面挑骨头,我们就把你拍成猪头三。”
“你的这些名单可以给我一份吗?我今天回去也多看看这些人的背景资料,第一次上电视节目,多少还是有些紧张的。”予之说着,也不等若离答应,便拿出手机对着她笔记本上记录的名单“咔嚓”“咔嚓”地拍了起来。
“你还有事的话,可以先走,我还想在这里坐坐。”予之看到若离不停地掏手机发短信,便不失礼貌地提议道。
“可以吗?我下午还约了一个人,他快到了。”
“请便。我第一次来电视台,有些乡巴佬进城的感觉,什么都觉得新鲜。”予之喝了一口咖啡,眼睛瞄着正在等电梯的一位浓妆艳抹的女人,如果没有看错的话,她应该就是他最爱看的纪实节目的主持人,想不到本人如此花里胡哨。
“那是要上节目的装束,别看了,你这表现实在太明显了。”若离说着推了予之一把,戏谑地说。
“这不算明显,我还想问她要个签名呢。”予之放下咖啡杯,站了起来。
若离心下一阵吃惊,“你真要去要签名?”
予之哈哈大笑,“我站起来是想各处走走,逛逛这大观园。你不是还有人要见吗?”
“你怎么总是这么出人意料?”若离松了一口气,然后指着右面的裙楼对予之说,“你往那边走,演播室这个过道,那边一楼就有我们的一个全透明演播室。”
全透明?
予之顺着若离的指向往裙楼方向走,果然,在大厅的正中央,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圆形全透明建筑,就视线上来说,这个演播室可以分成台前和台后两个部分,台前是镁光灯聚集,一个相貌姣好的主持人正在主持台前整理着文件,节目直播还没有正式开始,她与摄像师正在交流着什么。而后台则是各种予之叫不出名字的机器,还有工作人员与一位西装革履的人在交流着什么,予之料到那位西装革履的应该就是节目的参与嘉宾,那人长得眉清目秀,宽额头,尖下巴,咋看之下眼熟。
不过这种地方,应该会有很多眼熟的人吧?平日里都是在电视上晃动的人。
予之觉得很新鲜,不由地在这演播室外多逗留了一会儿,还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留念。
逗留片刻,予之便原路返回,穿过裙楼和主楼连接的长廊,又回到了原来的大厅,咖啡吧里的人明显多了起来,予之眼睛不由自主地被吸引着在人群中的每一张脸上搜索,不得不承认,在电视台这样的地方,人们身上的八卦特质很容易被唤起,总觉得会遇到哪一位常上电视的名人,或者是来做节目的小明星。
最后,他的目光停留在了某一处,心里暗暗吃了一惊——不是名人也不是明星,他看到在原来他坐的位置,已经被人给“填充”了,那人穿着一件白色POLO衫,头剃得很短,侧影看,脸显得瘦长,皮肤黝黑——这不是许由缰又会是谁?在他的对面依旧坐着张若离,谈笑风生的模样,满面春风,带着些许讨好的笑容。
他狠狠地深呼吸一口,看来这张若离与许由缰的事情是坐实了,之前在三亚刚刚发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非同寻常,这一次在电视台居然又能碰上。
她与许由缰的关系看来并不是那么简单啊,虽然听不见他们在谈论什么,但是能感觉出他们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点龃龉。张若离的表情明显很僵硬,而许由缰不无讨好之意。
予之无心再对两个恋爱中的人的纷争八卦做更多的关注,只是在内心里生出了一点点奇怪的想法——作为一个围绕在身边,依赖着自己,又很呱噪的朋友,竟然没有跟自己提及过张若离这个人,在予之看来真是难以想象,因为在他看来,许由缰事无巨细都会与他分享,哪怕是哪天晚上在夜店认识了某位援交妹,他都会与他津津乐道。
但是,对于张若离,他却保持了奇怪的沉默,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这花花公子这一次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