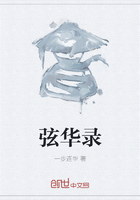云琰突然被一个响雷惊醒,虽说是午后,天色却暗如黑夜。
他发现自己仍待在静谊轩里,这几天哪儿都去不成,可把他憋坏了。外加根本没客人光顾,更是在百无聊赖中倍受煎熬,他着实体会到了曹静开店不易。
他看了看时钟,一心念着此刻正在玄林游玩的两人。这几天夕拾不在身边,总感觉少了些什么。
正当他哈欠连天之际,无意间发现中午吃剩下的盒饭居然出现在茶几上,他明明记得吃完之后把盒饭放在柜台上。说来也奇怪,自此他接管铺子以来,他也觉得这里阴阳怪气的,总感觉店里有人在走动,不是店堂有响声,便是里屋发出动静,时不时老有东西掉落或被换位。云琰整日疑神疑鬼,总把这些奇怪现象归咎于老鼠。
此时,外面传来几下敲门声。云琰只觉有些诧异,大门明明敞开着,怎么会有人如此有礼貌地敲门呢。
“里面有人,直接进来好了。”
户外阴云密布,室内更是光线昏暗,云琰一时看不清来人长相,但见门口那身影盈盈走入店堂。仔细一看,居然是曹静。
几日不见,云琰对曹静感到有些陌生,连打招呼的勇气都没了。两人四目相对,呆立良久。
不知为何,云琰刚想张嘴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倒是曹静先开了口,柔声道:“这几……天你过得还好吗?”
“也就那样,只不过有些无聊。你……不要这样看着我嘛,怪不好意思的!”
被云琰这么一说,曹静这才意识到自打进门后,目光未曾离开过云琰。随后她转移视线,顿感双手无所适从,不知放哪儿好。
“都老夫老妻了,还整得跟久别重逢一样。”
“你说什么?”曹静神情陡变。
“不用这么认真吧,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你现在没对象吧?”
“你今天怎么了?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曹静清了清嗓子,扫视了一圈店铺,续道:“这几天店里生意怎么样?”
“你觉得好得出来吗?我真不知道这几年你是怎么养活你自己的。对了,小夕人呢?怎么没看到她?”
“我已经把她送回去了!”
“看来这丫头是玩累了,不然早跟过来了。给,这里有两千,算是这次你带小夕出去的吃用开销,里面包括上次欠你的八百!”云琰从兜里掏出了一叠钱。他本来只想给一千五,见曹静开店不易,故意又多给了五百。
曹静迟迟没有接受,眼含泪光,杵在那里。云琰强行抓起对方手臂,硬塞到她手里。
“我真对你那么重要吗?”
“至少排前四。”
“那前三个是谁?”
“夕拾、沈琼、高琳!”云琰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看来你还真没忘记她。”
“你指的是谁?”
曹静低头不语,用食指轻拭眼中的热泪。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我可好久没见过你掉眼泪了!”
“是吗?或许是我们分开太久了。”
“是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俩起码有九秋没见了!”
“差不多吧。”曹静顿感失落。
云琰伸了个懒腰:“既然你回来了,我也该走了,这几天困在这儿闷都闷死了,我也该出去透透气了!”
“等一下,难道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
“说什么?咱俩都已经交接完毕了。还有,你的盆栽我也按照吩咐每天浇水,晴天摆到窗外晒太阳,至于其他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在两人对话过程中,曹静洞察机敏,好几次发现架子上的古董摇摇欲坠,不过均被她用气诀弹回原位。云琰却聊得很投入,毫无察觉,双眼始终专注于对方身上。
“可是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
“那你说吧,我听着呢。”
“算了,还是改天说吧,你先回去好了!”
“你啥时候变得那么矫情了?跟沈琼一个德行,有话直接说。”
“我……沈琼矫情吗?”
“相当矫情,不然我怎么会和她闹掰!”
“既然如此,你可以走了。”
“你这啥意思嘛?”云琰不明所以,觉得对方在无理取闹。
“我的意思是我要休息了,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曹静不耐烦道。
“好吧,我走了,最后还是要跟你说一声‘谢谢’。”
“不送!”
云琰将外套甩于肩上,手插裤兜,潇洒离去。曹静嘴上说不送,最后还是跟了出去,撩开门帘,目送云琰的背影渐行渐远,心情久久无法平复。
直到望不见云琰,她才放下帘子,随手关上了门,狰狞道:“小畜生,坏我好事。”
她发疯般步入店堂,右掌一推,从掌心中射出一道幽蓝色符文无形咒(无形咒,有字无符,相当于铭刻符文的掌风),穿过古董架,打在了墙上,登时化作黑烟。然而那东西身形敏捷,一闪而过。
“我好不容易才跟他重逢,要不是你在这儿给我捣乱,或许我俩还能多聊一会儿!”话音刚落,曹静不顾那些古董,直接将一个架子打烂,珍宝碎了一地。
曹静瞳仁一变,开启灵视,眼前的景物看上去就像开了夜视仪一样。只见一个神似佐伯俊雄的小孩正蹲在另一边的架子上,手里拿着一个花瓶,正要朝曹静砸去。不等对方出手,曹静一咒将其连人带瓶从架子上打落。只听得小孩一声惨叫,随即化为一滩人形血水。
曹静切换回肉眼,发现那滩血水看起来就像普通水渍一样残留在地面。她掌心向下,对着水渍念咒。过不多时,那滩水渍便蒸发消散。
……
云琰刚回到家,外面就下起了倾盆大雨。他庆幸自己早走一步,不然又淋成了落汤鸡。
他进屋一瞥,只见夕拾正躺在自己的床上呼呼大睡,身上的襦裙都未换下。
“这丫头估计真的是玩累了,好羡慕啊,我也想和曹静单独出去,可惜人家不给我这个机会。”云琰喃喃道。
此时,他突然想起早上晾在阳台的衣服还没收进来,于是赶忙出去收衣服,却发现所晒的衣物连同晾衣杆均不见了踪影。他不顾瓢泼雨势,探出身子,往阳台下俯视,却什么也没见着。他寻思着那些衣服或许已被大风刮走,对此心疼不已,表示又要花钱重新买过了。
正当云琰失落地回到屋里,无意中发现那些换洗好的衣服正叠放在沙发上。他登时喜出望外,心想这肯定是曹静帮忙收进来的,活像一个管家婆。他睹物思人,意淫了老半天,把自己给逗乐了。
这两天他闲得出奇,人一旦无聊到极点,同样会感到身心疲惫。他躺在夕拾的床上,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想着想着,他便睡了过去。
窗外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屋里却睡着两个雷打不动的人儿。
……
夕拾渐醒,发现自己竟已回到了家。她以为这又是在做梦,故意捏了捏自己的脸蛋,却着实有疼痛感。
窗外红透了半边天,她也不知道究竟是早晨还是傍晚。她缓缓望向客厅,只听见厨房传来噼里啪啦地烧菜声。她习惯了睡觉醒来第一眼看到的人是云琰,如果看不到便会显得焦躁不安。她此刻心里十分不畅快,连呼小云子。
“我的大小姐,你醒啦?有啥事?”云琰一听夕拾在叫自己,第一时间冲进房间。他手拿锅铲,腰系围裙,一副家庭主妇的模样。
“小云子,我是怎么回来的?”
“那要问你啦,连你都不知道我又怎么会知道。”
夕拾眉头微蹙,拼命回忆前几天所发生的事情。可想了好几遍,记忆总是停留在她与曹静一起喝酪酒上,之后便一片空白。她一度认为是自己醉酒后不省人事。
“你们中途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夕拾回过神来,不想让云琰知道自己喝酒的事,连忙矢口否认。
“嗯?不说实话?”云琰脸色一变。
夕拾知道瞒不过去了,只好嬉皮笑脸道:“你可别骂我,我和静姐姐一块儿喝酪酒去了。”
“要死了你,不是跟你说嘛,酪酒的度数相当于烈酒。平时喝点啤酒葡萄酒我也就不来说你了,现在居然瞒着我去喝酪酒,是不是翅膀长硬了?”云琰用锅铲一拍房门,如同父亲教训女儿一样正颜厉色。
“是静姐姐让我陪她喝的,不信你去问她。”
“就你这编谎话的水平还想蒙我?曹静不是不知道我禁止你喝度数高的酒!”
“是我要喝那又怎么样?来打我呀。”
云琰一听,立马火冒三丈,冲上去就是一巴掌。当他掌心快要糊在对方脸上时,忽然手速陡缓,轻轻捏了一记夕拾的脸蛋。他坐到床边,语重心长道:“这次就算了,记住下不为例,喝多了酪酒会伤肝!”
“我就知道小云子不舍得打我,么么哒。”披头散发的夕拾跪在床上,从后搂住云琰的脖子,脸贴脸,心中甜腻腻的。
“嘴巴臭死了,还不快去刷牙洗澡。待会儿吃完饭,咱俩出去溜达一圈!”
“好咧。”
说完,云琰回厨房继续烧菜。夕拾则换下襦裙,去卫生间洗漱。
还没等云琰站稳,只见夕拾惊恐地逃出卫生间,双目圆睁,牙关打颤,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你怎么了?”云琰一脸懵逼。
“他们……来了!”夕拾竟被吓得哭了起来。
“谁来了?”
“鬼冢晦明。”
“你怎么知道?”云琰登时警觉起来。
“厕所里的伞!”夕拾指了指卫生间。
云琰不明所以,于是过去瞧个究竟,原来夕拾是被放在马桶边的黑伞吓到了。
“你说的是这把?”云琰还特意拿了出来。
夕拾不敢直视,闭着眼睛点了点头。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鬼冢晦明的鬼魂来找你了。原来你说的是这把伞啊,这把伞是别人借我的,有空我要还回去的。”
“这把伞是谁借给你的?”
“那你先告诉我,为什么一把黑伞把你吓成这样?”
“小云子,难道你忘了?当年鬼冢晦明撑的就是这把伞!”
被夕拾这么一提醒,云琰还真觉得有些眼熟,难怪起初有种似曾相识的味道。他撑开黑伞仔细观察,确实给人一种沉闷压抑之感,乌黑的伞面居然不透半点光,像是把所有光线全都吸收进去,而且伞骨末端尖锐无比。他无意中还发现伞柄底部是空心的,正如一把剑鞘,想必插在里面的短剑早已被榎卸去。
“你怎么一眼就认出这把伞?”
“这是鬼门一族独有的形象用品,我记得小时候我和一个最要好的玩伴一起去参加鬼冢奶奶的葬礼,他们整个家族都是撑这种雨伞的。她还特意跟我介绍过,鬼冢家的伞面大、骨尖、底部有暗鞘,还有就是伞柄上印有般若鬼纹。”说到这里,夕拾想起了她那儿时玩伴,心头一酸,有种莫名的伤感。
云琰打量一番,虽未找到般若鬼纹,但却发现伞柄上有块凌乱的刮痕,像是有人故意为之。经夕拾这么一说,云琰回忆与榎两次接触下来的细节,不得不开始起疑。试问一个中国人怎么会取“榎”这样的名字,这个字他也只有在***的片子里见过,有几个“老师”的姓氏就叫“榎本”。
云琰此刻只想知道榎的真实身份,也许她真的是鬼门一家派来监视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