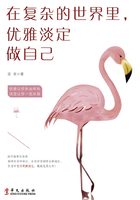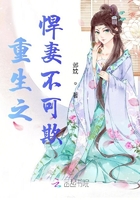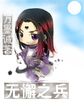《人间词话》乃王国维平生影响最大之一部作品。在中外学界可谓人人皆知矣。这部作品是王国维进入而立之年时,在他自称“因填词之成功”而“志于戏曲”之转折期中写成的,于两年前在《国粹学报》上陆续发表,此时之编撰只是一个修订稿,共六十四则。以后传世的就是这一稿,可以算作一个定稿。但在王氏去世之后,又有人从王氏原稿未刊出之部分中挑出四十四则,复增入其他词评四则,凡四十八则。此四十八则与王氏自己定稿之六十四则,加起来就是一百一十二则,被收入《王国维遗书》中。后人又继续搜集整理遗稿,使《人间词话》达到一百五十多则。版本较多,亦较复杂,此处不赘。无论如何,王氏之《人间词话》乃一部厚积薄发之作,叙述极为洗练精辟,总共万字左右,而其容量却大得惊人。从《人间词话》看,王氏不但精通文学及其理论,而且能将古今中外美学思想融为一体,穿梭往来,游刃自如,从文学、美学而至于广阔人生事业,多有点拨,令人深思。此种诗话形式并没有影响王氏之博大精深。在中西方人文史上,诗话(当然包括词话)这种论著形式并非鲜见。中国不用举例,西方就有柏拉图之文艺对话录与歌德之文艺谈话录,并享有很高之声誉。可见,诗话是源远流长的,是具有人文特色和艺术风格之文论。中国诗话,自古以来蔚为大观,更是数不胜数。此种文论之形成,王国维尝谓:“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王国维论学集》第386页)但除王氏所说的这一特征外,恐怕还是与中国文学演变和发展的历史特征有不可分割之关系所决定。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叙事文学如戏曲、小说之类从来被视为“小道”,亦被“正史”排除在外,除了散文以外,不过是诗词歌赋而已。当然,不仅诗词,就连关于戏曲乃至小说的某些论评及艺术见解,亦往往被写入诗话,故,诗话成为中国历代文学批评之重要形式。著名文学批评史家朱东润尝谓:“文学批评,古无定名。隋书经籍志于文章流别志论、翰林论、文心雕龙等诸书,皆附列总集之后。所谓解释评论,总于此编者也。”(《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12月第一版,第1页)朱东润还批评四库总目诗文评类提要对“文学批评”之划分过于狭窄,将很多诗话类排除在外的现象。可见,借评述正统之诗词的形式来阐发对文学之见解是历代诗话的重要功能。诗话文体,当始起于钟嵘之《诗品》。朱东润说:“论文之士,不为时代所左右,不顾事势之利钝,与潮流相违,卓然自信者。求之六代,钟蝾一人而已。”(同上注,第54页)可见钟蝾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地位不可动摇。到了宋元明清,词话之作更加繁盛起来。王国维所说的“光宣以来,士大夫流寓之地。惟友朋文字之往复,差便于居乡。然当春秋佳日,命俦啸侣,促坐分笺,壹握为笑,伤时怨生,追往悲来之意,往往见于言表。”(《观堂集林》外两种,下册,第722—723页)说的即是词话写作。清季民初之时,除了文艺杂志以外,就连综合性之刊物如《国粹学报》亦辟有诗词话专栏。王国维之《人间词话》即是在诗词复兴时产生的。《人间词话》之刊行与出版,可以说将近世中国诗学理论推向了一个高潮。见于国内外王学界诸多学人如周锯山、佛雏、傅杰、叶嘉莹等对《人间词话》皆有较深入之论析,此处不再赘述。
五、探戏曲之源流
王国维在学部工作时,交游之范围亦在逐步扩大。经罗振玉之引荐,他结识了以军机大臣领学部尚书之荣庆。王氏的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编译局编译之职,乃荣庆赏识其才学而委任之。加上结识的柯绍态、缪荃孙、傅增湘、刘世珩、吴昌绶等人,对于王氏由西学转入国学之学术转向期,相互切磋,相互问学,或借阅藏书,尤其是对学术研究帮助甚大。此时之王国维,除自号“人间”外,又名其书室曰“学学山海居”,开始了词曲特别是戏曲史资料之搜集与研究。
王国维由西学转为国学研究的一个显著标志,即是开始了他的词曲研究。罗振玉在为王国维的《观堂集林》作的《序》中说:“戊申以后,与君同客京师,君又治元明以来通俗文学,时则有《曲录》之刻,而《宋元戏曲史》亦属草于此时。然君治哲学,未尝溺新说而废旧闻;其治俗文学,亦未尝尊俚辞而薄雅故。”(《观堂集林》外两种,上册,第3页)罗氏所谓“通俗文学”对王国维而言,即是指他由词而曲。王氏既熟悉中国诗词歌赋,即所谓“雅故”,又广涉西方学术,他深知,自古及今由中而西,大诗人复往往乃大剧作家。在西方,有莎士比亚、歌德、席勒;在中国,有王实甫、关汉卿、马致远、汤显祖、孔尚任等,无一不是诗人兼剧作家。关于曲,在王氏同一时代人中关注者非他一人,如梁启超、吴梅等,吴梅还是曲学大师。但明确提出“戏曲”这一概念名称,并用西洋之戏剧来反观中国之曲,复用“戏曲”来称呼西洋之剧者,则是王国维。此说法起始于王氏1904年撰著的《红楼梦评论》中第三章《〈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开篇便说:“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予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厌阅者之心难矣!”(《王国维论学集》第358页)1905年,王国维又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论述到抒情叙事之作品时说:“甚至戏曲、小说之纯文学,亦往往以惩劝为旨,其有纯粹美术上之目的者,世非惟不知贵,且加贬焉。于哲学则如彼,于美术则如此,岂独世人不具眼之罪哉,抑亦哲学家、美术家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葸然以听命于众故也?”(同上注,第296页)王国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登上了学术舞台,从撰著《哲学辨惑)一文开始,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学术研究皆注意正其名,非常重视与强调范畴之准确与科学。他把小说与戏曲并列,则是从文学出发,并作为“纯文学”之一个门类提出,故强调“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此乃以前及王氏同时代之“曲学家”从未使用过之新范畴。
从1908年起,可以说王国维的全部精力皆投人词曲尤其是戏曲研究之中。王氏有志于戏曲研究之雄心完全可以由他自题其书室“学学山海居”窥见。此名称之典出自西汉著名辞赋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杨雄的《法言·学行》一文:“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不至于山。”(《诸习集成》第十册,杨雄著《法言·学行卷第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3页)意思是学海有涯而学无止境。经过几年之深入研究,王国维于“壬子(1912年)岁末,旅居多暇”(《宋元戏曲考》自序,《王国维论学集》第349页)时,寓居日本京都期间写成了中国戏曲史专著《宋元戏曲考》学),这是王氏一生中影响巨大的一部学术专著。此专著在发表之初,题为《宋元戏曲史》,连载于1913—1914年上海《东方杂志》,旋列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为此,在1913年1月5日,王国维给好友缪荃孙写信谈到:“近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将近脱稿,共分十六章润笔每千字三元,共五万余字,不过得二百元,但四五年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克期告成。惟其材料皆一手搜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月版,第33—34页)王国维撰著《宋元戏曲考》只用了两三个月时间,但酝酿之过程是长期的。王国维在《自序二》中写道:
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田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日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理想及结构,虽欲不谓王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固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王国维论学集》第411页)
由此可知,假若没有长时期之搜集整理工作,这些“幼稚”而又“拙劣”之材料怎能变成有用之学术资源呢?通过整理准备阶段,王氏亦深感中国戏曲之“不振”,根本不能去与西洋名剧相比;其原因亦在于中国戏曲曾长期被排斥在“正统”文学大门之外,故王氏有“不振”之感慨。王国维是大学者,他以科学的思维与渊博之学识,对中国的戏曲史资料进行深入的研究,做出了中国戏曲史与中国文学史发展相适应之判断。这是王氏深层人文情怀在审美文化中的直接反映,亦是人本—艺术美学价值观念的重大转折。关于此种转折,王氏在《宋元戏曲考》自序中有着独到的见解。王国维写道:
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而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予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者。遂使一代文献,都堙沈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词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髣髴也。(《王国雄论学集》第349页)
王国维对戏曲艺术形成的此种看法,是建立在深厚的学术基础之上的。王氏是通过占有大量戏曲史料并加以研究分析才认清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中国戏曲史上,绝不缺乏与西洋名剧相媲美的优秀作品,之所以形成戏曲“不振”之看法,那实在是由于“后世儒硕”之偏见。“儒硕”们站在“正史”之价值立场上,“鄙弃不复道”。对历朝历代之戏曲不屑一顾,故“正史”从来不记载戏曲作家,文学史也从来不论及戏曲作品。再者,王氏通过对《曲录》六卷、《戏曲考源》一卷、《宋大曲考》一卷、《优语录》二卷、《古剧角色考》一卷、《曲调源流表》一卷等史料之整理研究,王氏发现元剧实在乃一代之绝作。那么元曲之佳处究竟何在呢?“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载《王国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2月版,第153页)王氏评价汤显祖才思敏捷,为一时之冠,“然较之元人。显有人工与自然之别。”(同上注,第185页)王氏认为,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学问也;其作剧也;非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之意也。”(同上注,第153页)王氏的意思说,大概元代写剧之人皆不是有“名位”之人,故才写戏;若是有“名位”就不写戏了,而是去写诗词歌赋了,但王氏认为,恰恰是这些没有“名位”之人才写出了与西洋名剧相媲美之佳作。故王氏评价说:“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调用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同上注,第153页)此乃王国维怀抱振兴戏曲之愿望,决心治戏曲史之发现与学术转折。他从中国传统戏曲史料中探其源流,边搜集、边整理、边研究、边写作,潜心研读历代诸家剧本,以崭新的艺术美学观究其特色,为最终撰写《宋元戏曲考》而奠定了雄厚之学术基础。
六、《宋元戏曲考》之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