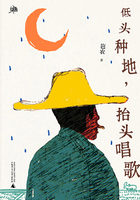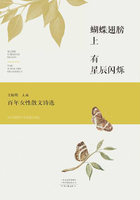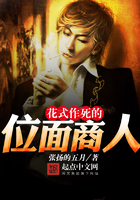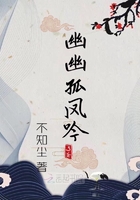蒋天枢对于他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极其尊敬,陈寅恪对这位学生也极为信任。在他目盲不能观书之后,就把许多书交给蒋天枢。蒋天枢家中放不下这些书,便寄存在复旦中文系办公室,蒋先生则几乎每个星期天皆到中文系整理陈寅恪的藏书。蒋天枢先生平时非常和气,但为了维护老师的学术尊严,有时却难免动怒。有一次,蒋先生在校园路上碰见他的学生吴中杰,老远就把吴中杰叫过来,板着面孔问道:“《解放日报》上那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蒋先生指的是那篇署名“吴中”的批判王国维的文章。那篇文章是中文系五年级一个写作小组所写,他们将“中五”二字倒过来,再将“五”字谐音为“吴”,变成“吴中”这个笔名,遂使蒋先生误以为是吴中杰所写,故对吴中杰满脸怒气。吴中杰细说实情后,蒋先生这才转怒为喜,笑着说:“那好,那好。”
在蒋天枢身上。我们看到朴学家的治学精神,也看到了中国传统的尊师思想。这在过去,本也不足为奇,但在经过这么多年历次运动之后,蒋先生仍能保持这种思想精神,却是十分难得的了。若从情感、气质到安身立命的学术思想,把蒋天枢归入到陈寅恪这一类知识分子中是合适的。有些细节的确能直见人的精神。在1956年5月21日陈寅恪填写的《干部经历表》上,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里,陈寅恪谈到蒋天枢,“一九二八年在清华是师生关系,最近数年因托他在上海图书馆查材料,故常有信来往”。无独有偶,1958年,蒋天枢在其《履历表》中“主要社会关系”一栏里这样写道:“陈寅恪,六十九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复旦大学档案)谁都知道,1958年批判资产阶段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炽,蒋天枢在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生平敬重之情,则蒋天枢为人的笃忠执著与表里如一,直见在当代已变得很陌生的士人精神。
关于蒋天枢先生,还有一事不可不说。1958年搞“大跃进”,人人高唱赞歌。在一次会议上轮到蒋天枢发言,蒋天枢只说“你们说的都是吹牛皮的话”这么一句便拂袖而去。结果弄到中文系众老师要保蒋天枢才能过了此险关。文化大革命中“无知”整“有知”。高等院校盛行考教授,不少老教授通不过“考试”,被评为“不合格”。蒋天枢却故意交白卷,临走时还扔下一句话:“路线决定一切,但路线不是我等人能制定的。”此话令极“左”的人哭笑不得,但也无法辩驳。以上这些,皆是复旦大学传说的佳话;不“曲学阿世”的蒋天枢,其耿介与清高,在复旦大学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是复旦中文系最傲慢的教授。正是因为有了蒋天枢这样的弟子,陈寅恪所以才倾心相诉。师生最后一次见面时,陈寅恪作了题为《甲辰四月赠蒋秉南教授》三绝,就是他们师生二人心灵相知的明证;从诗中足可见出蒋天枢是肩负陈寅恪先生的重托启程返沪的。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了蒋天枢1964年南^下广州的真正原因了。
五、蒋子凸现非偶然
蒋天枢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界的著名学者,他还是清华大学复建文科的首倡者,而且实实在在地催生了清华大学的文科。在清华档案馆的文科复建的文件中,有蒋天枢1981年1月16日致党中央副主席陈云的一封信,信中建议两件事:一是恢复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二是建议以清华大学为基础创办综合性大学。中宣部把蒋天枢教授的信转给了教育部党组,并有邓力群、王任重、郁文等领导的批示,要求教育部研究蒋先生的建议;蒋南翔也作了圈阅并转到了清华。由此可见,蒋天枢先生致陈云副主席的信在周转过程中,有关领导皆很重视。清华党委多次讨论,听取各种意见,终于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并且较快地付诸实施。但为什么当时很长时间没有人提到这件事呢?这主要是同蒋天枢的信中对旧清华的评价有关:“清华大学在旧社会原本有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为全国大学之冠。尤其文学院的历史、语文、外文各系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布及全国,为其他大学所不及。理、法科亦均各有特色,所培育人才多蜚声国际。目前的清华大学虽已成为工科大学,但一则它有以前的多科性综合大学的传统,再则以设备及人力等条件说,在工科大学的基础上增设文、理、法等学科较为容易,在文理大学的基础上增设工科则比较费事。所以,以清华大学为基础来创办,似可收事半功倍之效。”(见徐葆耕:《紫色清华》,民族出版社2001年4月版,第172页。)这段话现在看来很平常,但在1981年,思想解放运动刚刚兴起,“左派”势头还相当强大,谁都怕戴上“复旧”的帽子,蒋天枢先生写这封信的勇气可见非同寻常。蒋先生对清华文科的复建可谓起了“第一推动力”的作用,但他并不知道。如今,蒋先生已经仙逝,同他的业师陈寅恪共享天堂之乐了。
蒋天枢不仅学问博大精深,而且忠诚、厚道的人格也为后人所敬仰;他在陈寅恪晚年心目中的凸现并非偶然;陈寅恪晚年以其人生的通识,对世事与人事有精确的分析与预见;他将“生命之托”于蒋天枢,无疑是其晚年最完美的人生一幕。
陈寅恪与蒋天枢师生,他们若知道自己的文化学术思想正在为人们所理解,并成为中外学术界所尊奉的一代宗师,一定会感到几分欣慰。历史已经能够给他们的学术著作罩上未来的感受,他们遂可与自己的思想学术一起进入历史,同时步人未来,这应当是一种幸福与光荣:
已经变老的两位朋友坐在窗前还是觉得,心灵的这种自由来到了,正是在这天晚上,在他们脚下的街道上已经能感触到未来了,而他们自己也步入未来,今后将永远处于未来之中。想到这种神圣的城市和整个地球,想到没有活到今晚的这个故事的参加者和他们的孩子们,他们心中便感到一种幸福而温柔的平静,这种平静正把幸福的无声的音乐撒向周围。而他们手中的这本书仿佛知道这一切,支持并肯定他们的感觉。(引自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
撰成《学术的双峰———王国维陈寅恪与中国现代学术》一书,本想请一位严肃尊崇的学界前辈赐一序文。俟后沉想,使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请人作序,固能看出虚心求教之意。对方若能给予中肯之批评,当可受益匪浅。倘故而激发前辈之意兴,引出对有关学术乃至更为广泛的学术领域之宏谈高论,就更喜出望外了,这可能是求序之本意。
不过,就求序者之心态言,也未始没有请出尊神来为己作助阵之意。当初左思作《三都赋》,不就因为“时人互肖讥訾,‘请出“高名之士”皇甫谧为之“作序”,“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见刘义庆《世说新语·文学》)的么?这对于不重作者实际水平,徒以名声高下取舍之可悲世风来说,天疑也是对付的一大高招。但倘若并无左思那样的卓荦之才,偏要皇甫谧之辈为之鸣锣开道,岂不也太“颜,”且教“高名之士”连带受讥天下么?至于真有才学志气者,其实也未必需要高名者助阵。司马迁作《史记》,就并无自惭形秽,倒是精神抖擞地大声宣告:“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如此之创造气概,才真是自信自立者当有之气概。至今谈此数语,仍不禁令人敬佩和悠然神往。
余也不敏,所从事的也只是人文领域中之局部研探而已,自不可为前人之天造草昧大业相提并论。而且很需要前辈、同行之指点、批评。不过在研探之态度上,还是力求严谨,并希望有所弋获。而在志气上更不须借他人之颂谀,装饰自己之门面。倘只是谫陋之识,也不肯累高名者蒙羞。故考虑再三,终于决定不向前辈求序,由自己写一跋语交待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