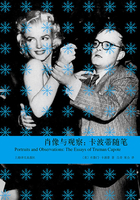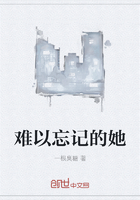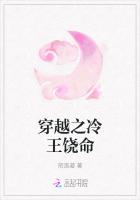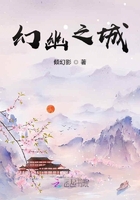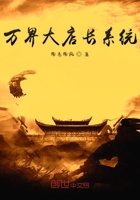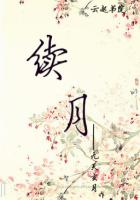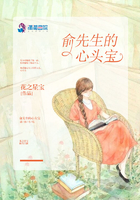陈寅恪之分析使南北朝末年宗教思想界一重要公案迎刃而解,理清了此时期佛道思想发展及其相互交融之脉络,其理论价值不言而喻。
六、订正千年误舛
佛教从西域传来是铁的历史事实,而这个学术判断在现代佛教史研究中也似乎得到了相当之支持,除梁启超、伯希和等少数学者外,大多学人相信佛教东传的路线与古代丝绸西去之路线系重叠;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则非常坚定地说佛教“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之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507页)30年代,当汤用彤撰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已捎带批评了梁启超和伯希和,说佛教入华,主要为陆路……据此,则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也。……而法人伯希和谓早期佛教有扬子江下流教派与北方教派之分,亦均不可通之论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重印本,第59、60页)还有学者认为,尽管佛教从西域传入之路线确信无疑,亦是不言而喻之历史存在,但不可忽略的是早期中印之间还存在着另外之通道,如佛教从南方海路传来,从西南通道传来,殷商时期可能有云南向中南交通之通道,佛教由此可向中土传播,等等。(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第508、509页)但通观陈寅恪之佛教史研究考证,中亚为佛教传入中土之主要媒介地,陈寅恪早已言之。因而,他于研究佛教史之际,对中亚史地,亦多有考证,所见迭出。比较具体的是对《蒙古源流》一书所做的一系列考证。《蒙古源流》凡八卷,为蒙古人小彻辰萨囊台吉所撰著。乾隆年间蒙古亲王喀尔喀以此书上于朝廷,并奉敕译进。全书以喇嘛佛教为纲,以各汗传统之世系为纬,并上及蒙古种族之起源。此书之重要性不仅由于出自蒙古人之手,而且由于记载首尾赅备,于国中治乱兴衰之迹,亦多按年胪载。但乾嘉学者病其音译难读,研治者甚少;直到道咸年间,边疆史地渐受重视,魏源、张穆等始引此书。嘉兴沈子培对此书尤勤,尝撰写《蒙古源流笺证》一书。沈子培研究此书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未解决之问题尚多,张尔田在沈子培著作弁言中尝谓:“此书叙述繁复,又经重译,非熟于史学,善用钩稽之术者不能通。像鞮之宾苦于不知史而治史者,又以其难读而弃之。今兹所校,阙疑尚多,固不能无待于后人继续。”(汪荣祖:《陈寅恪评传》第95页)不料,陈寅恪竟成了张尔田所期待之最佳“后人”。陈寅恪不但阅读了汉译本,并且找出满文、蒙文以及德文本,互勘比证,纠谬正误,此外还有很重要之发明。陈寅恪在《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一文中判定《蒙古源流》一书作者为库图克台彻辰洪台吉之曾孙,并作一世系简表说明满汉两译本皆误。《(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40-142页)他又推论出此书与《彰所知论》一书之关系;《蒙古源流》之作,在元亡后三百年,而其书之基本观念及编制体裁,实取之于《彰所知论》(《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28页》)陈寅恪从比较各种蒙古旧史和对民族起源之观念入手。《元史》所载,如阿兰果火不夫孕事,大抵皆与夫馀、鲜卑诸民族之感生说相似。《元秘史》所载已采用突厥神话,而《蒙古源流》所记则更增添天竺吐蕃之佛教神话,形成若顾颉刚所谓之“层累式地造成”之民族起源观。其所以如此,陈寅恪以为不得不诉源于《彰所知论》:
此论论主既采仿梵文所制之吐蕃字母,以为至元国书,于是至元国书遂为由吐蕃而再传之梵天文字。其造论亦取天竺吐蕃事迹,联接于蒙兀儿史。于是蒙兀儿史遂为由西藏而上续印度之通史。后来蒙古民族实从此传受一历史之新观念及方法。蒙古源流即依此观念,以此方法,采集材料,而成书者。(《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36页)
陈寅恪这一段话对全书作了精彩的概括,然后复指出成书之背景以及写史之方法,俾人原来困惑不解之难题,得以了然于心,大有拨云雾而见青天之感。在细节上,陈寅恪对人名、地名、时间进行了考证,为前人如王国维等所不能及。例如王国维校《蒙古源流》一书时,不知lrgai是何地,而陈寅恪考证“lrgai之为宁夏,可无疑”。陈寅恪说:“观堂先生谓衣儿格依城lrgai即元秘史之额里合牙,其说是也。”但元秘史续集“额里合牙旁注宁夏二字,如朵儿篾该旁注灵州二字者相同”。“西夏国都名lrgai,蒙古人谓之lrcaya,lrcaya与额里合牙对音适符,而西夏国都即宁夏”。陈寅恪说王国维在校雠《蒙古源流》一书时“未见蒙文满文诸本,故不知lrgai即宁夏”。(《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文载《金明馆丛稿二编》,第122、124、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