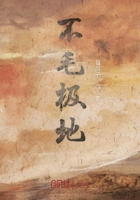十
成了夜府里的木槿华妃,待了小半年的光景,其实是很无聊的一件事。于是再不能想吃圆子就和莺儿跑出去大街小巷的瞎逛、再不能随随便便说话、再也不能累了乏了便寻个床榻上去躺躺,似乎人越是到了高位便越越逐渐靠近荒废,太子妃的唯一用处似乎只剩下当太子妃本身,这样的日子着实是很乏味的。
还好离安一直待我很好,他会每天喂我吃亲手煨的八分熟的水蒸蛋,会跑好多地方去寻我喜欢的花给我闻。只是到底离安不太会这些,所以水蒸蛋里常常会有没剥干净的蛋壳,挑花的时候会常常扎到手上呲牙怪叫。我是很幸福的,很多时候我都会去想,离安不该是夜君——现在不是以后也不该是。
又过了挺长一段时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便挑出一日,支开了离安,喊着莺儿打算易装出游。于是包了头发,带上十几两碎银子的盘缠,又给离安桌子上留了条子说是去阳平关见个老朋友,让他不要担心,估摸着三两日便能回来,这才蹑手蹑脚的溜出了夜府。
很多时候人真的是没了身份才能最开心的,走出了夜府,十八街的铺子各式各样的吃食儿油炸货,我又变回了曾经那个落萱,麻糖串子、炸肝溜肚,没了莫离宫里的那些禁忌,我和莺儿体验了一回久违的自由感。看了灯会、听了湖女唱腔,忘乎所以的玩了三天,才想起这算是到了跟离安约定的回家时间,这才和莺儿折道回了夜府,当然还是蹑手蹑脚的。
进了夜府的大门,才觉得似乎这几日并不太寻常,路上公公侍女走的也比平日里都很急,我自然也觉得不太妙,心里暗暗担心莫不是我偷偷溜出去的行为让这夜府上下寻我寻得急了。细细想想却也否了,一来即便如今我成了倍受尊宠的木槿华妃,但单纯是我丢了似乎不至于让整个院子如此的戒备,我知道这时候再不赶紧回太子府该不当了,便往着莫离宫紧赶慢赶。
一推开房门,离安正坐在房里。看见我也不知发了什么狂,先是大声的质问我去了哪里,语气是那种严厉的有些令我害怕的,严厉着然后又突然开始哭,趴在我身上哭,问他什么他也不说,我可真是慌了神,实实在在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许哭,我不过是出去了几日,又不会出什么事。”
这话说的似乎是不管什么事儿的,离安依旧啜泣的厉害。
“那我、我答应你,以后都不偷偷出去了好不好?”
“君父…他病了。”
我这才知道,这些日子夜国里出了这样的大事。夜君是沙场将军出身,体格向来很好,武功又高,他病了实在有些出乎我的意料,而且看离安的样子,决计不像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
“君父病了,病的好重,你又不在,这宫里连个能给我主意的人都没有,请了大夫,又说摸不清楚是得了什么病……”
等我真的到了夜君跟前,才知道竟是病的那么严重,虽然我看不见,但夜君一阵阵猛烈急促的咳嗽和一次次大口的咯血似乎在提醒我,他的日子并不多了。今天前还好好的一个人,还巍峨的站着、还是一句话就能左右人生死存亡的枭雄,怎么就突然这样了,我是想象不了的。
“夜君在上,竹青子堂外候诊。”悠悠然的听到大殿外面的请奏声。
“君父病了,宫里的太医师傅们都没法子,我便连夜差人发了求医的布告,许是竹青子正好仙游到这,想来天不亡君父!”
我一听离安广发了征医的布告,心里暗道不好。君王病危,宫里向来该要守口如瓶,太平的世道还好,若是搁在乱世里,有哪一国哪一君有冒犯之意,趁乱犯上,国真是危险了。
宣了竹青子进来,自然是常规的诊脉、闻声、听气,折腾了有一会儿,又是砸了砸嘴巴,我记得半年前竹青子给我瞧眼病时也是那么的砸吧嘴,以为夜君的境况未必太好,但起码有救,却听见竹青子踌躇的站起身来,”难——难啊!”
离安一听慌了神,赶紧拉着竹青子出了内殿,我自然是在一边跟着。
“竹师傅,我父君得的什么病,可还有救?”
“离安公子——老夫行医数十年,说起来见过的病也是无数了,江湖上说但凡是病,老夫都还算是能治,虽是有些夸张,但也还算贴切。”
“如此说,君父的病是有救了!”
“若是病,自然有救,只是——”
“只是什么?”
“夜君的脉相平稳康复,并无病症,但神志模糊又时常咯血,我刚才看了夜君咯出的血色,红里面带着黑丝,依我看——这是被人下了盅,不只是盅,还是这世上最毒的丧国盅,古语说‘丧国出,国丧不久’,夜君恐怕……”
“下盅,是谁那么大胆,我若知道必将他千刀万剐!”夜君从小宠着离安的,如今夜君被人下了如此恶毒的盅毒,离安自然是极愤怒的。
“恐怕公子现在要想的最重要的,未必是夜君的病,这丧国盅来自北国,据我所知北国的凌绝宫中可是有丧国盅的方子。安顿夜君自然重要,只是离安公子可真要提防着北边的苗头,若是趁夜君大病的时候,凌绝大兵压境,恐怕……”
“不、不会,夜国和凌绝宫刚刚才签了万世修好的折子,万不会是凌绝的主意,万不会……不会的。”
竹青子自知此时说什么都没什么用,便拱着手退下了。我知道离安心里很乱,凭他的才智,该是清楚的。国无永修好,何况是这样割据的年代,一切决定国家间关系的便只剩下利益,突然间夜君就中了凌绝宫里的盅子,前些日子恰好上官凌绝来了这夜国大殿待了不短的日子,若说这盅不是凌绝宫下的,恐怕自欺欺人了。
“离安,你不能慌。夜君倒了,你便是这夜国的主子,你是主子你若慌了,夜国便慌了。你之前发了求医的帖子,若是凌绝真要作乱此时大抵已经得了消息,你该赶紧遣便兵北上,加戍边疆,万一凌绝真的大兵压境,要好有个对策不是。”我一介女流,打仗的事自然是不懂的,但起码的国危聚兵的道理我该明白,离安没经过事儿,他慌了,我既然是他的妻子,我便得想着法子的不让他慌。
“好,快遣人、遣人喊龙虎将军来。”
只是——似乎我们还是慢了些,这边宣着将军殿前授命的招子,那边小太监便火急火燎的跑进来。
“离安公子,不好了,凌绝大军南下压境,北方七城相继沦陷,说是凌绝的兵已经到了临安。”
这一年离安刚满二十岁,眼看着不行了的夜君下了平生最后一道诏书,太子离安继任夜君,举国当兵甲刀戈,北抗凌绝。史书这样记载:
夜君衰,凌绝罢约,操戈南下,颁诏令太子离安领国,举国抗、死社稷。
——《夜史》
大殿上的事,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清楚了,离安一直忙着领国抗敌,临危受命自然战战兢兢,只是老夜君留给他的底子还不错,于是即便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即便离安还从没经历过什么像样的历练,仓促之间集结的夜国大军竟也抵抗住了凌绝的袭击,只是北边战事自此胶着,离安只好托付好了夜府里的事,以御驾亲征的名头,领兵北上,君王死社稷,离安这一步终于稳固住了夜国摇摇欲坠的边防城池。
我便还想讲讲殿外的事儿。听说离安终于守住了国,老夜君似乎终于安稳些,虽然依旧时常呕血、有时也还神志不清,只是总算靠着竹青子的药吊住了命。离安去了边境,这殿里的繁琐小事便依托了我,竹青子说听琴可以安神,我便常常拿着琴去弹给老夜君听,他也爱听我弹得鸢尾折,也总听不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