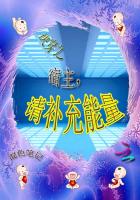一段时间后,发现工作都是差不多的性质,好像做什么都没有差别,有什么学历也不那么重要,一切还是要靠努力,靠激情。
早上从单位到二院去处理一些路倒的人员,总有一些人喝醉酒,然后倒在路边,最后就被警察送到医院,对于那些无名氏,只有我们来帮助他们处理了。
由于之前几天比较忙,二院这边已经有好多材料我们都没来得及处理。这些人主要是一些流浪汉和醉酒者。
接待我的是医务科的杨科长,毕竟我是第一次来,也许以后就我跑这条线了,科长特意让我来找这个领导。
杨科长是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人,大背头,讲话声音特别洪亮,语速也比他这个年纪的人要快很多。
“小商啊,我可是和你们救助站打了二十多年的交道了,以前是你们施站长,那时候我老是被她骂,后来我就自己学习,现在我也是半个医务社工啊!”
听完他的介绍,我只能报以微笑,我这样的年轻人能怎么样呢。
“小商啊,你们现在对于那些醉酒路倒的人究竟有没有什么政策啊,或者权利啊?”
“怎么了?我没听我们科长说过这方面的事情,你告诉我什么事,我回去给你问问。”
“是这样的,现在常常有人把那些醉酒路倒的人送到医院。之前我们都会给他们挂水,醒酒的。但前段时间,有个地方的医院因为这样的事情,把人挂水给弄死了。你不知道一般酒喝多了的人,不给他挂水醒酒,他可能会有生命危险,但有的因为自身身体过敏,挂了也会有生命危险,可是他醉的不省人事,我们也问不到他是不是过敏啊。更重要的是,那帮醉酒的人,我们救了他,要么连谢谢都没有,起来就走了,要么还要责怪我们,太寒心了。”
听了他的介绍,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不住地点头,算是对他的精神支持吧。很多政策的制定者,他们自身并没有在基层做过,所以很多问题,他们考虑不到,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到急诊看了下,一般外伤的,治好了都走了,现在就留下一个老头在这里。
那老头整个脸瘦的都凹了进去,短发,全身都是那种暴晒过的漆黑,腿上都是小伤痕。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总觉得他上气不接下气。问护士他的情况,护士说没事,就是饿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病。
我试着询问道:“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啊?”
他喉咙吞咽着,但发出的声音却很细微,我把耳朵贴上去,还是听不清他说什么。
我又问护士,他真的没事吗?护士还是很肯定地说没事。看见我还是不相信的样子,护士走过去把他扶起,坐在了床上,一股臭味袭来。
“你知道你是哪里人吗?”
“东长湾!”他说的很轻,而且还是方言,但很庆幸,这方言是我家乡的。
我兴奋地问道:“你是下面县的人啊?”
他无力地点点头,脖子仿佛支撑不住脑袋的重量。
“那你叫什么名字?”
他说了他的名字,而他所在的那个村子,是我小时候常常去玩的地方,所以我知道在哪里,回去应该可以很快地找到。
从二院回到站里,把大概的事情处理情况向科长汇报了一下,然后就开始联系那个老人的家里。毕竟是一个地方的,派出所,村委会,很快就找到了他家里人。老人已经走失2天了,家里人得到他消息后,离开就叫车来站里接人。于是我又赶紧去医院将人接来站里。
我刚将人接回,老人的家人也来了。看到老人又黑又瘦的样子,老人的儿媳当场就哭了。交接完后,因为是同一个地方的人,所以就多聊了几句,原来这老人的一个女儿竟然就住在我家楼下。世界真的太小了,所以我们要多做好事。
从知道这个老人,到帮他找到家人,前后一共就3个小时。科长说,我这是找人的记录了,还没有比我这更加快的了。也许是虚荣心作对吧,我竟然很享受这样的感觉,做起事来也更加的有兴趣。
如果名利可以带来好的发展,那名利又有什么不好呢?
下午原本是要上街救助的,但市人大好像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我从小就厌倦这样的检查,很多时候,检查的根本就不是工作,而就是卫生,就像数学考试,永远不是考解题能力,而是计算能力。
科长他们都开始忙活起来了,我有点心不在焉,我主要自己主观上排斥的东西,就绝对不会认真去做。人大代表,真心不知道这算是个哪门子的领导。
千呼万唤后,终于在快下班的时候,他们出现了。我对他们的意见更加的大了,做事根本就不人性化,更加没有时间观念,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坐上代表的,就像永远弄不明白大学里那些考试作弊的人是怎么拿到奖学金的一样。
领头的是一个女主任,小贡就带着她参观了一下整个救助站,介绍了一下相关的情况,回到接待室的时候,她指着救助区的房间说道:“给那些外流住这么好的房间啊?”
站里面的领导都不说话,施站长脸上惊现一丝的惊讶,转瞬变成了一种不屑。终于有人开始牛头不对马嘴的和这个女主任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
我远远地看着她,就那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样的人还配做领导,简直就是浪费社会主义的粮食。
什么叫外流住这么好的房间啊?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允许政府盖豪华的大楼,那当然就允许我们为救助对象谋福利啊。各国的救助,都强调一个,让救助对象有尊严的活着,我们有这样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在硬件上给他们营造更好的氛围呢?中央领导都说,要给中国人一个中国梦,难道这些受助者就不是中国人吗?他们的中国梦就应该是噩梦吗?
我实在想不明白,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混进我们伟大祖国的人大系统中去,那不是玷污我们国家的形象吗?
一肚子的气,但也就只敢在心里嘟囔,谁让我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小员工呢。
送走了那帮人大代表,大家又回到了各自的岗位,只有我还内心愤愤不平。有一种想要抱怨一下的冲动,但最后我还是选择了忍住,有些话,说不得,工作不是大学课堂,能够畅所欲言。
就在这时,科长接到一个电话,说一个女的被抢劫了,后来被送到了三院,医院希望我们能够去看一看。因为快下班了,所以科长就想自己去。
三院是传染病医院,而我还从来没有去过,虽然这名头让人有点害怕,但还是想去见识下。于是就和科长说了,和他一起去。
进入三院的病房后,医生给我们发了手套和口罩,这些都是二院和四院没有的。那气氛一下子就让人紧张了起来,我开始回想我上一次甲肝乙肝接种是什么时候,越想,人越是悚然。
三张床的病房里,有两张床上都有人,其中一个老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整个房间充斥着药水的味道,我能清晰地听到呼吸的声音。医生叫醒了那个被抢劫的女人,她看起来有点害怕,但却又给人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她没说几句就哭了,让我们一定要帮她把钱要回来。我们当然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又不是警察。但为了安抚她的情绪,我们还是满口答应了。
她说自己是云南人,家里有丈夫和孩子,后来认识了我们这边一个在云南打工的男子,男子妻子死了,常常找她倾诉,后来她可怜那个男子,就和那个男子好了,然后就跟着她到了这边。后来因为一些事情吵架了,他们就分开了。那天晚上,她打工完准备回家,然后在过一条巷子的时候,就被人用绳子勒住了脖子,最后抢走了她身上所有的钱。
科长安慰了她几句,关照她要听这边医生的话,我们会帮助她解决困难的。
说完就赶紧从病房出来了,这样的地方,能少待一刻,就一刻,心里恐惧太难受了。
科长向医生询问了一下她的病情。医生说他们现在还在等化验结果出来,是传染病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很可能是她被抢劫的时候把打伤了,应该不会是肺有问题。
科长一下子就紧张了,让他们一有结果就赶紧通知他,千万不要没有传染病的,结果在医院待出了传染病。
回去的路上,科长问我是不是刚才在三院很害怕,我不是个喜欢说谎的人,尤其是面对我尊重的人。他说他第一次也是这样的,但后来想想,做我们这行的,又不害人,做好事,应该是会走运的,所以所有不好的都会绕着我们走。
我想想,其实这不就是社会学上的风险社会理论嘛,做了什么,都会对将来的自己有影响,而且这影响,很多时候是蝴蝶效应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