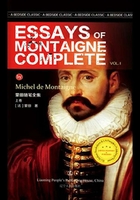演罢了戏,柳如是寇白门少不得夸赞一番,又点拨了三两处。待众人都走了,嬛伶正要进舱,却见李渔远远地站着,就走了过去。
“真要走?”李渔开口便问。嬛伶不答,只是点点头。李渔叹道:“这西湖美景,人间天堂真留不住你?”嬛伶道:“不是我,是我们。婳伶虽然嫁了人,现在看着也挺好的,但是姐妹们心里到底不是滋味,不想再待了。”“那你自己呢?”李渔追问道,“你自己没有一点儿留恋之心吗?”
嬛伶听出话中别意,却不露形容,只是道:“天下的好风光那么多,怎么留恋地过来?该走的时候,自然要走。”李渔点头叹道:“回了江宁府,还会演《怜香伴》吗?”嬛伶道:“自然会演的。将来有机会,我们还会回杭州来找先生,演先生的戏。”李渔忽然笑道:“你这辈子,只怕是个戏精了。”说罢,两个人同时轻叹一声,也不多说,默默站了一会儿,李渔便告辞了。嬛伶在船头上看着,风轻轻吹过,心里生出一丝丝难言的感伤来。
次日近午十分,倾月班收了招牌,就要开船。柳如是和寇白门赶来相送,佟国器也陪着婳伶来了,独不见李渔。婳伶交过两张银票,道:“不许推辞。我知道,我走了,你毕竟缺个人。一路上留心,要是遇到好的苗子,买两个。”于是姐妹们相互劝慰一番,含泪挥别。姝伶拉了婳伶的手,滴泪道:“姐姐,我们以后还来杭州看你。”婳伶含笑,送着戏船离了西湖岸边,飘然而去。
六十里常州府毗陵驿,一百一十里镇江府,九十里龙潭驿,船头一转,江宁府金陵城又在眼前了。
嬛伶走向船尾,在姜伶身边坐下,望着木桨划出的波纹发呆。姜伶问道:“想什么呢?再半日,就要到了。”嬛伶道:“姐姐,我们不进城了吧。”“不进城?”姜伶疑惑道,“不进城,去哪里?”嬛伶一叹:“现在城外待着吧,不拘哪里。想进城时再进去,咱们先在别处歇歇。”姜伶答应着,只是摇橹不停。
半日到了金陵城外,船在长干桥下停住了,姜伶因问道:“到底将船拴在哪里呢?”嬗伶望着聚宝门外大报恩寺塔琉璃圣光,浮屠崔嵬,一片祥云袅绕,便道:“姐姐,我们不如就在大报恩寺旁的渡口靠了船吧,这里要进城容易,要出城也方便,往来的人口又多,想要演戏搭台就演,挺好的。”嬛伶想了想,觉得也挺好,便命靠了岸,将船拴拢。众女伶出得舱来,也不顾往来行人,纷纷伸展腰肢,疏松筋骨。嬛伶道:“你们若想出去逛逛的,就自己去吧,小心点,早些回来。”
虽然年年都要回江宁府,可每次回来女孩子们都忍不住还要去逛一番,尤其是那旧院风景,总带着那抹不去脂粉浓香,清曲优雅。
嬛伶在舱内转了一圈,见嬗伶和嫱伶两个还坐着说闲话,便问:“你们不出去逛逛?”嫱伶道:“那些街市什么的,不太想去。”嬗伶道:“我正怂恿她去大报恩寺看看呢。”嬛伶道:“是啊,自从到了戏船,每年回来也只是灵谷寺、鸡鸣寺走一走,竟再没有逛过大报恩寺。”嬗伶忙道:“要不我们一起去吧?”嬛伶道:“罢了,还是你们两个去吧。我有些累了,想歇歇,顺便看着船。”嫱伶道:“好吧。那我们两个去了,逛完了就回来,你好好歇着吧。”
嫱伶和嬗伶两个出舱上岸,沿着秦淮外河的南岸往大报恩寺去。只见处处人头攒动,香烟弥漫,诵经声不绝于耳。嫱伶道:“这大报恩寺竟然这么热闹,上香的人也太多了。”嬗伶道:“快到浴佛节了,自然人多。”嫱伶一想,道:“果然是。我竟然都不知光阴了。”“何止你?”嬗伶笑道,“这一船的姐妹们常常都不知光阴,只有嬛伶姐记得清楚,为的是根据日子安排戏目。”
两个人一面说着,一面登台阶进了山门,仰颈遥望,琉璃宝塔耸入云霄。嬗伶忽道:“听说那琉璃塔下还埋着金棺银椁,佛骨舍利。据说是南梁朝武帝时就有了,也不知道真的假的。”说着又问道,“姐,你是学武的,你说说,当年达摩一苇渡江,行得通吗?真有这绝世轻功?”嫱伶并未答话,只是微皱着眉头看嬗伶道:“你这小丫头知道的倒也不少啊?”嬗伶咧嘴一乐:“跑了这么多年的戏船码头,这些事早听了百十遍了。”嫱伶听了,不再多问。
两个人一同看了天王殿,赏了石坛栏楯,饶过大殿,来至琉璃塔下。塔前塔后都是等着砖塔祈福的人。嫱伶仰头细观宝塔,白瓷贴面,琉璃拱门,五色的琉璃砖雕成各种花鸟虫兽镶嵌门上,九层八面的檐角下上百铁马随风叮咚,犹如西天梵音,声闻数里。虽是白天,塔内仍燃着数百盏长明灯,灯火辉煌,油香四溢,遥想塔顶高处,定供奉着稀世珠宝,以配这塔底深处埋藏的佛顶骨舍利。
嬗伶问道:“姐,我们要爬塔去吗?”嫱伶笑道:“人家爬塔凭的是一片诚心,我们两个,却是凭蛮力。”嬗伶道:“那就爬了再说。”于是随着人群往塔上走去,每到一层,都停下来观摩各色琉璃雕刻,凭栏看景。只见城内城外,闹市之景尽入眼底。江宁府热闹繁华,果真是一方富庶之地。
越往上去人就越少,许多体力不支的人都歇了下来,也有一些干脆放弃了,独嬗伶和嫱伶两个人兴致勃勃,一直登到塔顶,却见两个小沙弥守在那里,正盘坐蒲团,闭目诵经。嫱伶不由轻声道:“好了,也是头了,该回去了。免得人家以为我们是来盗宝的,当我们是奔波吧和霸波奔呢。”嬗伶歪嘴笑道:“错了,我们是来登塔的,不是守塔的。”于是附在嫱伶耳便道,“他们是奔波吧和霸波奔,我们是唐僧和悟空。”嫱伶也忍住笑了:“少胡说。我反正不是唐僧,你么,倒是个活悟空。太闹!”说罢,两个挽着手下塔而去。
正出了塔门,忽听一阵捉贼,嬗伶和嫱伶回身望去,只见两个莽汉推开众香客,往这边跑来,后面追着几个小沙弥。嬗伶冷笑道:“还真有奔波吧和霸波奔呐!”说着两个莽汉已经到了眼前,嬗伶和嫱伶猛地转身,脚下一抬,一个人绊倒一个。嬗伶忙上前,一屁股坐在一个莽汉身上,脚下使着千斤坠的功夫,压得那人动弹不得。嫱伶则趁另一人爬起时抓了胳膊,只一拧,那人便被反锁住。
小沙弥和众香客都围了过来,忙七手八脚的扭过两个贼人,嚷嚷着送到衙门去。只见一个法师模样的走上前来,稽首道:“多谢两位女施主擒贼。”嬗伶笑道:“举手之劳,长老不必客气!”法师道:“哪里,两位姑娘年纪轻轻就一身侠气,有此义举,实在难得。哦,三日之后就是浴佛节,届时寺中有浴佛庆典,二位姑娘若有暇,还请前来结缘。”嬗伶忙答应道:“长老既然相邀,岂敢不来。”说完稽首告辞。那法师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看着嫱伶,嫱伶恰好回头看他,那法师便微微一笑,点头去了。
回到戏船,嫏伶等出去游逛的也回来了。娑伶道:“可回来了!等你们开饭呢。街上新买的乌米饭,拌了糖,快来吃吧。”原来江浙一带百姓都有浴佛节前后吃乌米饭的习俗,乃是用乌饭草舂成汁,泡了粳米或糯米煮成的,色成紫黑,清香可口。
众人吃着饭,娑伶道:“哎,都说这乌米饭是从目连救母的故事上来的,如今又是浴佛节,我们不如演几出教化的戏吧,也应应景。”嬛伶道:“你说的轻巧,这些年我们一直演风月戏,这些戏,只怕都荒疏了。”
娑伶道:“我也说了是应景。每年浴佛节的时候,各大寺院前都有戏班子搭台,不过是热闹热闹。”嬗伶插道:“《目连救母》我以前倒是学过,这样吧,我和娑伶姐姐搭一回戏。”娑伶道:“行。我虽然多年不演了,但这点老旦的功夫还是不曾丢的。”妖伶一旁帮衬道:“《西游》里的戏不是也行么?这个交给我们几个小的吧。”
众女伶都说好,嬗伶忽然捅了嫱伶一下,道:“你怎么了?我们这边说的热闹,你却发呆?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乌饭吗?”嫱伶回过神来,眨着眼睛道:“没什么,我在想些事情呢。你们要演戏,我自然说好。”嬗伶并不饶她:“哎,还说戏。你的《昭君出塞》和《挡马》什么时候能见啊?”嫱伶尴尬道:“我……你就饶了我吧。”嬛伶却道:“嬗伶你急什么?你学了多少年才练出来的?别催她。我看她那日练功,倒有悟性,过了一个坎儿,就好了。”
隔日,女伶们便忙着浴佛节的戏,却独不见嫱伶。待她回来问有什么事情,她也不说,只是笑笑掩过。这天正是浴佛节,大报恩寺内人山人海,拜佛的,观礼的,敬香的,熙熙攘攘只进不出。寺前摆满各色货郎摊,各处戏班子也来搭台唱戏,百步之内倒有七八艘戏船,船前也都是人头攒动,看戏取乐。
嫱伶来至浴佛的礼台前,四下观望,果见那日的法师在一旁站着。他见嫱伶来了,抽身便走,嫱伶忙跟了上去。行至一处寂静寺院,法师转身道:“姑娘缘何今日才来?”嫱伶未解其意,便道:“大师不是要我今日来的吗?”法师道:“人称姑娘机敏伶俐,为何故作痴呆呢?”嫱伶警惕道:“大师究竟是何人?”法师道:“姑娘不必担忧。贫僧法号妙空,是两江总督马国柱大人在大报恩寺的替身,却也是姑娘的同道之人。”
嫱伶心中大惊,只是面上不露,道:“大师此言怎解?”妙空道:“贫僧自幼皈依佛门,算来也有四十年了。马大人上任金陵后,贫僧便为其替身,来至大报恩寺。然而,贫僧要做的,除了早晚诵经外,便是与姑娘一样的事情了。”嫱伶哪里敢轻信,因道:“那大师说的是什么事呢?”
妙空从袖中取出一枚印信,道:“姑娘身份乃是福建陈复甫转由镇江平一统告知贫僧的。”嫱伶见印信与自己所携一模一样,知道妙空是亲信之人,又想起杭州陈复甫所提之事,这才放心,因道:“但不知大师有何事交待?”妙空道:“姑娘想必知道,福建那里为着卖不出海盐,筹不到银两之事发愁?”嫱伶点点头:“怎么?大师有法子?”
妙空含笑:“这大报恩寺琉璃塔里,现有无价之宝。”嫱伶一惊,道:“大师,你……”“这世上的善男信女前来供养,不知捐了多少金银珍宝在塔内。”妙空接道,“这大报恩寺乃永乐大帝所建,如今这些珍宝取来用于复明大业,岂非理所当然!”
嫱伶不由倒吸了口冷气,妙空继续道,“贫僧苦熬多年,总算做了琉璃塔的值守,目下是浴佛节,寺内闲杂人等较多,若是事发,也容易做遮掩。”嫱伶思忖道:“大师这主意可与上头商量过?既然有此决定,但不知要我做些什么?”
妙空道:“陈义士告诉贫僧,有难处或可向姑娘求援。贫僧知道姑娘所在的戏船就在寺前停驻,便有大用。这塔内珍宝虽不多,可若是悉数运出,过关盘查,恐露嫌疑。贫僧意欲将部分宝物先藏于船上,待日后慢慢送出去。那戏船往来江宁府多年,又是一船女伶,自然不会引起官府主意……”
“不行!”嫱伶断然回绝道,“若是要我赴汤蹈火,我自万死不辞。可无端牵扯无辜之人,是万万不能的。”妙空忙道:“她们都是我汉家子民,为反清复明大业尽些力是应当的。”嫱伶定了目光,道:“大师身在佛门,为何不讲慈悲。我等沉沦苦海便也罢了,何必连累他人?”
妙空哑然,欲笑不能笑,只得道:“没想到姑娘心中竟有此慈悲。”嫱伶低头叹道:“此事还请大师谅解,再想他法吧。”妙空急道:“贫僧已做好谋划,就在这几日,姑娘若不帮忙,只怕夜长梦多。”嫱伶道:“戏船到来,不过是机缘巧合,我不信大师事先没有其他安排。”妙空顿时哑口无言,知道嫱伶意志坚决不好强求,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