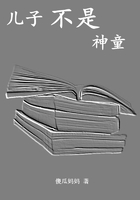过年里维尘在家没呆上几天便又要赶往在邻省开机的新剧剧组,他打算开着车去,临走那天早上,他给宫兰打了个电话,她忽然问他,能否顺便捎带她到一个叫岭头的地方,她把聂拓在那山上造了所房子的事告诉了他。
“你怎么不早说,真想跟你一道上去看看。”
“你那么忙,好不容易有几天假,再说我不太确定上山的路,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她安慰他。
他来接了她,按着她的指示,把车开到了岭头镇,问她接下来怎么走,她凭着记忆给他指路,但都弄错了。也停下来问过好些路人,他们所指的方向,确实可以到达山下,但没看见那作为标志的水库,她找不到上山的路。
好容易打听到往水库怎么走,开到那儿时,他载着她已在镇上绕了快一个小时,她下了车,无比抱歉地让他快赶路,他笑着摘了墨镜,往山上看了一眼说:“路真不好找,可这山看上去倒挺有些神秘感的,下回你一定得带我上去一趟。”
她点头同意,嘱咐他路上小心,然后便站在一边看着他把车重倒上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车开出一小段,忽然又停了下来,他从车窗口递出一瓶矿泉水来,她跑上去感激地接了,一直目送着他把车开出那尘土弥漫的小道。
虽然到了记忆中的山下,但只来过一次,并且是跟着聂拓来的,她还是花了一会儿工夫才确认上山的路。
她在蜿蜒的山道上努力走着,不敢多停歇,不知过了多久,终于看到了村口的竹牌坊,这才怀着一种胜利的喜悦慢下了脚步。也许过年走亲戚去了,村子里今天像是个安静的日子,村口没见到玩耍的孩子。走进村子,一个大概见过她的妇女朝她笑着打招呼,熟稔地询问聂先生怎么没来,她微笑着回答说她自己一个人上来的,那妇女热情地领着她走到上山顶的小路口,她谢了她,只身又往上爬。
到了山顶上,一见到那跟图纸上形状一样的一座小房子时,胸腔里一股气流便不由得涌动起来。那房子背靠着一处避风的山崖,朴实而并不让人惊艳,然而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瞬间便深深刺痛了她的心。
她来到门前,从背包里找出一片钥匙,却立刻发现门没锁。推门踏进里边时,一股柚木的清香扑面而来,她的眼泪这时抑制不住地流淌了出来。
屋里也和想象中一样,并不很大,没有间隔的底层最多四十平方,地上放着两张木凳子,此外没有任何家具,她下意识地在墙壁上找了找,找到了一个开关,摁下却没有反应,这才想起这儿不通电。一个角落里倒是放着一台小发电机,大概盖房子时用来切削木头的。房间最靠里的一扇小窗旁,有一段上二楼的楼梯。
上楼前,她不得不狠狠地抹净泪水,以便看清脚下的台阶。
斜顶的关系,二楼比楼下更小些,分成两个隔间。在作为卧室的那间里,她看见一张由两张小木床拼拢的大床,只是床架子,是分别为他和她的将来准备的。她想起他曾不无打趣地说过:“总有一天咱们的激情会退至握手的距离的。”
她走去将窗户逐一打开,一扇窗户开在南面,另一扇西窗开在倾斜的屋顶上。房间里立刻涌进了清新的微风,光线也明亮了好些。她站到窗口旁,这时已到了午后,由于爬山和饥饿的缘故,她突然觉得很疲倦,地板很干净,像用水清洗过,她直接在地板上躺了下来。
房顶上裸露着坚实的柚木横梁,倾斜的西窗里映着蓝天,她闭上眼睛,感觉这房子和他多么相似,理性与简朴,同时又具备抵御一切困难的能力与智慧。一种平静的忧伤又向她袭来,但在眼泪再一次涌出前,她睡着了。
她后来是有些被冷醒的,发觉自己蜷缩在呢大衣里,一阵阵的凉风,把丝丝寒意沁入她的身体。但一束斜阳照在她身上,在那奇异的红黄色光线中,她眼睁睁地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身在何处,也才想到要赶在天黑前下山去。她站起来,重新去把所有的窗户关好,走下楼梯,出了门。房门口那平整的廊道,木围栏才修了一小截,等着主人回来完工的状态。她有些恋恋不舍地离开房子,朝着山下走去。
再下到村子里时,她碰见了阿花,他也笑着问她聂拓怎么没来,她把噩耗简短地告知了他,他听后十分愕然,连声问着:“啊呀,怎么会这样?两个月前他还好好的呀,他说年后会回来开工,将房子收尾,我还等着帮他的忙哩,唉!”
她没再说什么,忍住了又要流泪的冲动。阿花兀自叹息着,见她要下山,才醒转来,当即说送她下山去。
阿花陪着她一同下了山,一路送她走到镇上,直到把她送上进城的大巴。
她上车前谢他,并说以后还会再来的,阿花听了,似乎想再问些什么,终没问出口,只眼露惋惜地点了点头。
日色已显得黯淡,大巴启动了,阿花在车下朝她招着手。
车子在大路上飞跑起来后,她的额头抵着车窗,窗外似曾相识的景物逐渐消融进初降的暮色里。他们的房子盖好了,她的生日也过去了,和他的只相隔七天。
她听见肚子因没吃午饭而响起的辘辘肠鸣,饥饿和悲伤一样真实。她手里仍拿着维尘留给她的那瓶水,拧开瓶盖,她抿了一小口。前座的后椅背上插着一本不知谁留下的杂志,露着轿车的广告词:“以你为家,以我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