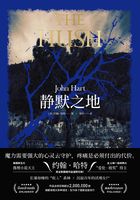秋天是生疏的。
午夜里并不严厉的凉意,正午时近乎暑热的犹疑,日晒的炫目与柔和,云朵的轻倩,阴影处的轻寒与爽利,微妙的绿,初浅的褐,纯正的金,冷的红,厚重的桂香,炒栗子的清甜与沙糯,突然高远起来的天幕,街道呈现久违的松快,归家路上出于自怜的抱臂,莫名而起的感喟,毛毯陌生的触觉,丝巾令人不安的光滑,棉布过水后柔净的细腻,新晾衣裳清冽的湿气,梨子表面的颗粒,翻毛靴面的生涩,黄叶红砖参差的质感,轻拢慢捻的碎影,都是生疏的。
生疏不是从未经历,而是每年都来一回,被冲淡,再唤起,反复淘洗,只余一些简约的芯。久别重逢的快乐,都因着秋的落寞况味,被压制了些,变作一种正经的愉悦。冬春夏这条上坡路线就此打住了,要慢慢撒把,放手了。汗液充沛的夏悄然遁去,灼热与迷狂不再恋战。万物有归意,人们开始轻手轻脚,像是怕惊扰了什么。秋天是悬空的,悬在极热与极冷之间。它要尽量平滑,尽量不动声色,完成这艰难而隆重的过渡。层层秋雨筛过,颓败相更加明显。一夜星斗炯炯,第二日,又反弹出鲜明的、若无其事的蓝天。傍晚的冷风拂过白日里被痛晒的路面,乱穿衣的行人,三三两两,避过纷飞的落叶。大娘便混在这行人中,去干儿子家吃小孙子的生日酒。
抄近路,经过一片老居民楼,颜色灰败,毫不起眼,因得了光线指点,竟富丽堂皇起来。通体镀金,暗处被掩了细节,变得单纯。亮线滚边,阴影描形,大娘绕路口半周,专为看它。之后,像是一种色彩弥补,一家幼儿园出现了。隔了漆了七彩的栏杆看进去,真是个叽叽喳喳的小人国。大门是一只开屏的绿孔雀,满身睁着椭圆蓝眼睛,嘴上叼着锁。路边的银杏叶集成小堆,大娘一脚踢破一个,一路行来,碎金四溅,如腾祥云。与此同时,一枚扇形小叶,亮如金箔,自高处跃下,赖在她新染的黑发上,穿街过巷,在阴凉与曝晒中交替了几回,顺利进入小区,最终被抖落在玄关处。
照例被不相干的眼泪涮一遍,她只当洗了个热水澡。有人撕开人墙,杀到跟前。黑脸膛,大块头,自称是舅舅,过来就要跪,她一把没拉住,差点被拽趴到地上。劝了半天,才想起人家手腕子还被自己攥着,赶紧松了,一看,两圈白印子。来人红着眼圈,深深鞠一躬,一头扎入人海,再寻不见。
女眷们陪她说话,有几个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干脆互相揭丑,话里带荤。一看就是临时起意,未笑先闹个大红脸。眼风呼呼飞,大娘回头去逮,总是被一张艳如春花的笑脸截住。人人都捡好的说,怕把她情绪弄上来,不好劝。眼见人家一大家子,齐心合力,大娘黯然了。
地上一块簇新的婴儿爬行毯,蓝天白云绿草羊群,永远晴空万里,永远鸟语花香。沙发上搭着一只奶黄小肚兜,肚脐的位置绣着硬邦邦的小鸭嘴。小寿星在练习走路,胎发细软,颅壳幼嫩,扶着茶几醉步向前。被手机相机围剿许久,好容易突围。转头看见大娘,毫无芥蒂,露出二枚小牙,粲然一笑。
大娘心头一热,蹲下身来,张开两手,拍一拍,软乎乎的小身体欣然入怀。沉甸甸的,没有毁坏的,生的重量。她把脸埋进奶香味的脖颈里,嗅个不停。婴儿伸出小手,宽容地拍拍她的头,力道颇像早逝的老父。大家看着这一对,愕然之余,放下心来,觉得刚才的一番心血没白费。
人群突然静了,大娘慌忙正襟危坐。男人被轮椅推了来,皮相败了,骨架还在。一张脸兜在大手里,嗷嗷哭。指缝里泻下一截幼细的金链子,像是粗黑桃树皮裂开,渗出一丝明黄桃胶。他肩膀一抖,金链子尽头的小金锁就随之一颤,锁身錾四个小字:年年有余。
怎么着,嫌晦气呀?一天没带过!大娘笑眯眯,把着豆豆的小手去够。奶奶给豆豆的,你们管不着。小金锁映在婴儿乌黑的瞳仁里,摇摇晃晃,像一盏渔火。
干妈哎!要是我父母还在,早把我打死去陪余磊了!男人急得直捶腿:现在我再收你东西,不要说这辈子,永生永世,也还不起了!
婴儿在翠绿小斗篷下仰起脸,望向嚎啕的父亲,抽抽搭搭的母亲。鱼缸里浸着几团金红色绉纱,皆空游无所依,像一碗巨型花茶。
到了高新区,处处横平竖直,人也严苛起来,稍微一点杂乱,就看不顺眼,恨不得斩尽杀绝。为了杜绝分心,高楼们一丝花纹也无,纯色,笔挺,冷峻,把人身上的懒劲都削服帖了。有的楼群用了玻璃幕墙,像巨大的电视屏,一格一格,同步播放着蓝天白云。
两步之内,大娘跟不锈钢门框上的倒影飞快地汇合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闭着眼都知道,24号收银台,红帽子,红围裙。脑后一只韩国鬏鬏,又叫丸子头。
也遇到过熟人,没关系,就说来买东西的,一次也没露馅过。以前怎么看她都不顺眼,眼珠上戴假眼子,眼皮上粘假睫毛,像苍蝇排队伸脚做操。现在看着她麻利地扫描、装袋,大娘总觉得,一下班,她又会跟往常一样,坐在余磊电瓶车后座,嘴里嚼着旺仔奶糖,或者油炸里脊,手里悠着一把野花什么的,咋咋呼呼回家来。
才回过神,大娘就发现那边有点不对劲。一位中年妇女指着李亭大声喝问,隔得远,只看得见凶狠的口型。被她一衬,李亭小得可怜。大娘跟一只警察真人模型公示牌并肩站着,动弹不得。
天花板垂下无数小红灯笼,底部淌下一穗细流苏,一只只排着队,奔向24号收银台。日光灯贴着缝隙走,亮成一条条虚线,照得天花板像游泳池的泳道。人群乱哄哄,拢成一只红毛丹,始终看不到李亭的正脸。小风暴附近是冷冻柜,货架上装饰着绿得令人生疑的塑料藤蔓。一头大汉以手掩口,在兰花指的遮挡下优雅地剔牙。一张减价牌挂在他脸旁,剪成爆炸形,上书:猪头肉,39.8元一斤。
入口处一家卤味店,白天也点着小红灯。一只小风扇慢慢转,下头系着红飘带,悠成一只软弹簧,赶苍蝇。大娘刚瞄一眼,就被伙计逮住了:大姐,鸭脖子打八折,来一斤?
鉴于小伙子眼色活,也考虑到她还要在这里站一气,大娘点头一笑:帮我称半斤。
耳光来得太突然了,大娘一个激灵,两颊烧得通红。血管里发洪水了,太阳穴突突,跳出一种可怕的平静。伙计觉出异样,主动弃了这笔生意。右手边一家服装店,通体都是心平气和的藕粉与鹅黄。已经走到服务台了,又折回来,如此三个来回。大娘问了自己好几个问题,答案都是不。
有人在发瑜伽舞蹈小广告,看看她,迟疑一下,把名片塞向她身后的一对小夫妻。粉红气球拧成的拱门下,一列手推车开始过隧道。蛙绿鱼嘴高跟鞋上站着颤微微的牛仔裙少女。栗色卷发,皮粉风衣,灰咖羊毛开衫,卡其小脚裤,褐金亮片鞋,香风过后,女子身形修长,像是打树林归来,沾一身掸不掉的典雅秋色。男人把烂旧皮夹克搭在肩上,背上像是伏了只野狼。有人斜挎包随着臀部起伏。有人T恤侧面的条纹没对齐。有人头盔未摘。有人对着垃圾桶练习三分球。有人丢弃赠品券。有人打抱不平。有人在自动扶梯上跑动。有人公然看热闹。有人鹤发苍颜,背着瓦蓝机器猫书包。有人踩了她一脚,忙不迭抱歉,她浑然不觉。无数不相干的人,她本该是他们中的一个。大理石柱子冰着掌心,正好治她的高烧。捂热了一处,换另一处,越来越亲切。
终于,中年妇女被几个主管模样的人用肉身隔开。李亭下巴直挺挺地仰着,肩膀一抽一抽,两手一左一右,掸去眼泪。
晚了,最佳时机已经错过。大娘出了门,背对着这一幕,孤零零站着。自动门合上,又开,太过灵敏,让人烦恼。三级台阶之下,几条电动车长龙臣服在脚边,她变成寂寞的女皇。
天上有云,发着银光。门口撑起几柄广告伞,毒蕈样鲜艳。可乐啪一声被拉开。车声像永不停息的呼噜。人来人往,她鬓发拂动。身后一把女声,醇厚洒脱,像饮酒半醺,带着一种中年式的欢快,伴随大减价的巨浪,覆盖了整个商场:
风再冷 不想逃 花再美也不想要 任我飘摇
天越高 心越小 不问因果有多少 独自醉倒
今天哭 明天笑 不求有人能明了 一身骄傲
歌在唱 舞在跳 长夜漫漫不觉晓 将快乐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