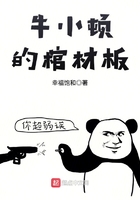梵高死后,提奥对着虚空高喊,“文森特,你在哪儿,救我!”
此时,暴风雨正在来临,人们毫无准备,许多年来,人们都在雨水和干旱中寻找一个支点,试图撬动他们的人生以避免虚空。但虚空无所不在,五脏与五官之间都有它的罅隙,虚空将赢得一切。
马夫点上一根烟,昔人已乘黄鹤去,他挥手让一辆奥迪倒往指定的停车带,往左,往左,左边是抒情,右边则是理性。马夫的手向着夜空挥动,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星辰为之一振,军气已经遍布宇宙,他们把战舰开到了其他星系,有什么迷离惝恍的事情正在发生。
今天我想到了死亡,我想去死,只是因为我疲倦了,只是因为大教堂的玻璃窗上,天使们的画像让我出于爱和悲而颤抖,只是因为,而今我温顺得像一面镜子,像一面不幸而忧伤的镜子……
马夫吟唱着他的影子般的马雅可夫斯基,快要死去一样大哭一场,阮步兵在夕阳的尽头赶他的马车,哭他的穷途,穷尽一切可能的途径只为了回来,奥德修斯已经搭上船只,艰难的旅行足以延长一个旅行者的梦,在梦里换算时间是划算的,马夫经常潜入梦境,做他们的时间生意,帮助别人缩短每一个奇迹。
奇迹在频繁地发生,如同淋巴在生发。马夫的过去已经割除,他记得那个给他奇迹的女人从此像烟一样消散,在某个夜里从床上失踪,但烟味始终弥漫在房间里的每个角落,他在任何一个出乎意料的角落都能听见那个给他奇迹的女人在跟他说“嗨”,在她的唇舌之间有一个大海如此汹涌,以致浪花从墙壁上翻起,天花板上有一位圣母俯临马夫,试图让他明白人子也从子宫中来,并没有任何奇异之处,真正的奇异要在以后的历练中获得,但时间不可能给予重复,覆辙一旦重蹈,前人的印象未必适合我们今日的脚踵?
马夫看着一辆辆形同棺木的汽车,这些形同鬼魅的铁壳使城市不断地失去下限,一日日沉沦如泥沼,人们如泥胎木偶,坚硬的灵魂上面镂出了繁复的花纹,那个给他奇迹的女人就在这些枝叶间闪现她的面容,她狡黠而无辜的眼睛,每天都在扑闪一个秘密,到底是什么诱使他,“又要来歌颂,像医院似的让人睡坏的男人,像格言似的被人用滥的女人”,一切都是向着黑暗缴税,风把屋顶吹到了半空,阁楼里的老鼠成群结队着咬开圣经,每一句先知的话语都在每一只幼鼠的肚子里生长,它们会在每一条街上得到石头和棍棒,或者在每一间仓库里得到捕鼠夹和毒药。始料不及的总归始乱终弃。
此时,马夫正和一只硕鼠对望,他认识这只硕鼠,花白的胡须已经令他生出敬意,在厨房间讨生活的日子,这只硕鼠日渐庞大,它更像一只龙猫,飞快地跳过那些隔离带和闪射的车灯,马夫目送这只硕鼠的时候,想起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谁许我一纸繁华,胡为乎来哉。那些饮醉的人们很快就会成为硕鼠,在他们的南瓜车里子夜正在降临,神甫躲在他的忏悔室等一个女郎前来报到,她有如簧的巧舌可以拨动他的指针。钟声不论远近,都在奔袭送葬。
无辜的人们已经永垂不朽。
每一座钢筋水泥房里都有他们自制的纪念碑,如同他们在这个国家已经领到了奖赏,一张廉价的通行证,通往各自交换而来的地狱。马夫在他年轻的声音里时常灌注了太多苍老,有鹰隼的锐利,乌鸦的聒噪,一种锐利的聒噪,形同电钻在头颅上打开了一个洞眼,并且在这个洞眼里安装了一个手电筒,以示佛的事业在于见钱眼开。那些沸腾的颅腔产生了词语,听他吟唱,“我爱每一样东西的普普通通的生命”,马雅可夫斯基已经举起了手枪,海明威正把枪口塞进嘴巴,轰掉的大脑像毁坏的蜂巢,蜜蜂“嗡嗡”地围绕着这个世纪,马夫把每一只蜜蜂都钉在十环以内,那个给他奇迹的女人正裸露着身体,娇小的乳房跳起来像受惊的鹁鸪,这饥饿的小鸟,正咕咕地叫唤,鹁鸪声起晓耕云,马夫已经缓辔徐行,这辆年轻的保时捷,灵巧如蛇,甩动它的尾巴,狠狠地抽向虚空,虚空将赢得一切。
马夫醒来的那一刻,太阳正在融化,像一颗过于甜蜜的奶糖,滴淌着芳香。另一个枕头上凹陷下去的印记似乎证明夜里确实有人睡在左右,还是自己曾经翻到另一个枕头上睡过了几个时辰?可这缭绕的烟味尚未散去,不是去年的,不是数个月前的,此时此刻尚有一个影子在点起纸烟,从虚空中吹来一口黄鹤的唳叫,玻璃窗上叠映的面孔,远天密布的阴云,大地正在吞咽那些葱翠的草木,而人们就在草木中突起,“千百只眼睛的大火从码头上扑进发抖的人们的寂静的住宅里”,从此水光潋滟,晴日挂失在日历上,人们要在雨水的喧嚣中长出鱼鳞和双鳃,鲸鱼占领天空的时候,人们骑着海马去上班。
汽笛声已经将一条大街扭曲变形,马夫习惯在窗口顺手将一条大街卷起来,如同卷起皮尺,用来丈量这座城市的皮尺也早已失去了尺寸,人们仰仗什么生活,从来不需要明说。马夫需要记忆,但记忆从来不是可以凭借需要就可以复制,无数个日夜,他靠歌唱来引领自己走回困境中去,困在那个房间里的人使他相信,人们善于画地为牢,每一座牢狱不在建筑,而在人心。文森特画出来的那颗太阳,或许更值得生活在那颗太阳的底下,向日葵和星辰都是柔软多汁的,咖啡座和顶棚从来不在意雨水敲打。人们穿上厚厚的大氅,冬天里的马铃薯如此烫嘴,穿上军靴的男人和轻摇小扇的妇人,后来都剪作纸片,在文件夹中日益泛黄,时光抵上春光,无限往往限制了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