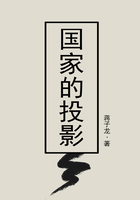我们从海参崴跑出来的时候,随身带了有相当数目的财产,我们也就依着它在上海平安地过了两年。至于伯爵夫人呢,我没便于问她,但她在上海生活开始两年之中,似乎也很安裕地过着,没感受着什么缺陷。但是到了第三年……我们的生活便开始变化了,便开始了羞辱的生活!
当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经济将要耗尽的时候,我催促白根设法,或寻得一个什么职业,或开辟一个什么别的来源……但是白根总是回答我道:“丽莎,亲爱的,这用不着呵。你没有听说波尔雪委克已经起了内讧吗?你没有听说谢米诺夫将军得了日本政府的援助,已经开始夺取西伯利亚了吗?而况且法国……美国……英国……现在正在进行武装干涉俄罗斯的军事联盟……丽莎,亲爱的,我相信我们很快地就要回到俄罗斯去的呵。我们没有焦虑的必要……”
但是白根的预言终于错误了。波尔雪委克的俄罗斯日见强固起来,而我们的生活也就因之日见艰难起来,日见消失了确定的希望。
我们静坐在异国的上海,盼望着祖国的好消息……白根每日坐在房里,很少有出门的时候。他的少年英气完全消沉了。他终日蹙着两眉,不时地叹着气。我们的桌子上供着尼古拉皇帝的肖像,白根总是向它对坐着,有时目不转睛地向它望着,他望着,望着,忽然很痛苦地长叹道:“唉,俄罗斯,俄罗斯,你难道就这样地死亡了吗?!”
我真是不忍看着他这种可怜的神情!他在我的面前,总是说着一些有希望的硬话,但是我相信在他的心里,他已是比我更软弱的人了。我时常劝他同我一块儿去游玩,但他答应我的时候很少,总是将两眉一皱,说道:“我不高兴……”
他完全变了。往日的活泼而好游玩的他,富于青春活力的他,现在变成孤僻的,静寂的老人了。这对于我是怎样地可怕!天哪!我的青春的美梦为什么是这样容易地消逝!往日的白根是我的幸福,是我的骄傲,现在的白根却是我的苦痛了。
如果我出门的话,那我总是和米海诺夫伯爵夫人同行。我和她成了异常亲密的,不可分离的朋友。这在事实上,也逼得我们不得不如此:我们同是异邦的零落人,在这生疏的上海,寻不到一点儿安慰和同情,因此我们相互之间,就不得不特别增加安慰和同情了。她的大耳环依旧地戴着,她依旧不改贵妇人的态度。无事的时候,她总是为我叙述着关于她的过去的生活:她的父亲是一个有声望的地主,她的母亲也出自于名门贵族。她在十八岁时嫁与米海诺夫伯爵……伯爵不但富于财产,而且是一个极有教养的绅士。她与他同居了十年,虽然没有生过孩子,但是他们夫妻俩是异常地幸福……
有时她忽然问我道:“丽莎,你相信我们会回到俄罗斯吗?”
不待我的回答,她又继续说道:“我不相信我们能再回到俄罗斯去……也许我们的阶级,贵族,已经完结了自己的命运,现在应是黑虫们抬头的时候了。”停一会儿,她摇一摇头,叹着说道:“是这样地突然!是这样地可怕!”
我静听着她说,不参加什么意见。我在她的眼光里,看出很悲哀的绝望,这种绝望有时令我心神战栗。我想安慰她,但同时又觉得我自己也是热烈地需要着安慰……
虹口公园,梵王渡公园,法国公园,黄浦滩公园,遍满了我和米海诺夫伯爵夫人的足迹。我们每日无事可做,只得借着逛公园以消磨我们客中的寂苦的时光,如果我们有充足的银钱时,那我们尽可逍遥于精美的咖啡馆,出入于宽敞的电影院,或徘徊于各大百货公司之门,随意购买自己心爱的物品,但是我们……我们昔日虽然是贵族,现在却变成异乡的零落人了,昔日的彼得格勒的奢华生活,对于我们已成了过去的梦幻,不可复现了。这异邦的上海虽好,虽然华丽不减于那当年的彼得格勒,但是它只对着有钱的人们展着欢迎的微笑,它可以给他们以安慰,给他们以温柔,并给他们满足一切的欲望。但是我们……我们并不是它的贵客呵。
在公园中,我们看到异乡的花木——它们的凋残与繁茂。在春天,它们就发青了;在夏天,它们就繁茂了;在秋天,它们就枯黄了;在冬天,它们就凋残了。仿佛异乡季候的更迭,并没与祖国有什么巨大的差异。但是异乡究竟是异乡,祖国究竟是祖国。在上海我们看不见那连天的白雪,在上海我们再也得不到那在纷纷细雪中散步的兴致。这对于别国人,白雪或者并不是什么可贵的宝物,但这对于俄罗斯人——俄罗斯人是在白雪中生长的呵,他们是习惯于白雪的拥抱了。他们无论如何不能身在异乡,忘怀那祖国的连天的白雪!
有一次,那已经是傍晚了,夕阳返射着它的无力的,黄色的辉光。虹口公园已渐渐落到寂静的怀抱里,稀少了游人的踪影。我与米海诺夫伯爵夫人并坐在池边的长靠椅上,两人只默默地呆望着池中的,被夕阳返射着的金色的波纹。这时我回忆起来彼得格勒的尼娃河,那在夕阳返照中尼娃河上的景物……我忽然莫明其妙地向伯爵夫人说道:“伯爵夫人!我们还是回到俄罗斯去罢,回到我们的彼得格勒去罢……让波尔雪委克把我们杀掉罢,这里是这样地孤寂!一切都是这样地生疏!我不能在这里再生活下去了!”
伯爵夫人始而诧异地逼视着我,似乎不明白我的意思,或以为我发了神经病,后来她低下头来,叹着说道:“当然,顶好是回到俄罗斯去……但是白很呢?”她忽然将头抬起望着我说道,“他愿意回到俄罗斯去吗?”
我没有回答她。
夕阳渐渐地隐藏了自己的金影。夜幕渐渐地无声无嗅地展开了。公园中更加异常地静寂了。我觉得目前展开的,不是昏黑的夜幕,而是我的不可突破的乡愁的罗网……
六
客地的光阴在我们的苦闷中一天一天地,一月一月地,一年一年地,毫不停留地过去,我们随身所带来到上海的银钱,也就随之如流水也似地消逝。我们开始变卖我们的珠宝,钻石戒指,贵重的衣饰……但是我们的来源是有限的,而我们的用途却没有止境。天哪!我们简直变成为什么都没有的无产阶级了!……房东呈着冷酷的面孔逼着我们要房钱,饭馆的老板毫不容情地要断绝我们的伙食……至此我才感觉得贫穷的痛苦,才明白金钱的魔力是这般地利害。我们想告饶,我们想讨情,但是天哪,谁个能给我们以稍微的温存呢?一切一切,一切都如冰铁一般的冷酷……
白根老坐在家里,他的两眼已睡得失了光芒了。他的头发蓬松着,许多天都不修面。他所能做得到的,只是无力的叹息,只是无力的对于波尔雪委克的诅咒,后来他连诅咒不也不诅咒了。我看着这样下去老不是事,想寻一条出路,但我是一个女人家,又有什么能力呢?他是一个男子,而他已经是这样了……怎么办呢?天哪!我们就这样待死吗?
“白根!”有一次我生着气对他说道:“你为什么老是在家里坐着不动呢?难道说我们就这样饿死不成?房东已经下驱逐令了……我们总是要想一想办法才行罢……”
“你要我怎么样办呢?你看我能够做什么事情?我什么都不会……打仗我是会的,但是这又用不着……”
我听了他的这些可怜的话,不禁又是气他,又是可怜他。当年他是那样地傲慢,英俊,是那样地风采奕奕,而现在却变成这样的可怜虫了。
有一天我在黄浦滩公园中认识了一个俄国女人,她约莫有三十岁的样子,看来也是从前的贵族。在谈话中我知道了她的身世:她的丈夫原充当过旧俄罗斯军队中的军官,后来在田尼庚将军麾下服务,等于田尼庚将军失败了,他们经过君士坦丁堡跑到上海来……现在他们在上海已经住了一年多了。
“你们现在怎么样生活呢?你们很有钱罢?”我有点难为情地问她这么两句。她听了我的话,溜我一眼,将脸一红,很羞赧地说道:“不挨饿已经算是上帝的恩惠了,哪里还有钱呢?”
“他现在干什么呢?在什么机关内服务吗?”
她摇一摇头,她的脸更加泛红了。过了半晌,她轻轻地叹着说道:“事到如今,只要能混得一碗饭吃,什么事都可以做。他现在替一个有钱的中国人保镖……”
“怎吗?”我不待她说完,就很惊奇地问她道,“保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不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在此地,在上海,有许多中国的有钱人,他们怕强盗抢他们,或者怕被人家绑了票,因此雇了一些保镖的人,来保护他们的身体。可是他们又不信任自己的同国人,因为他们是可以与强盗通气的呵,所以花钱雇我们的俄罗斯人做他们的保镖,他们以为比较靠得住些。”
“工钱很多吗?”我又问。
“还可以。七八十块洋钱一月。”
忽然我的脑筋中飞来了一种思想:这倒也是一条出路。为什么白根不去试试呢?七八十块洋钱一月,这数目虽然不大,但是马马虎虎地也可以维持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了。于是我带着几分的希望,很小心地问她道:“请问这种差事很多吗?”
“我不知道,”她摇一摇头说道,“这要问我的丈夫洛白珂,他大约是知道的。”
于是我也不怕难为情了,就将我们的状况详细地告知了她,请她看同国人的面上,托她的丈夫代为白根寻找这种同一的差事。她也就慨然允诺,并问明了我的地址,过几天来给我们回信。这时正是六月的一天的傍晚,公园中的游人非常众多,在他们的面孔上,都充满着闲散的,安逸的神情。虽然暑气在包围着大地,然而江边的傍晚的微风,却给了人们以凉爽的刺激,使人感觉得心旷神怡。尤其是那些如蝴蝶也似的中国的女人们,在她们的面孔上,寻不出一点忧闷的痕迹,我觉得她们都是沉醉在幸福的海里了。我看着她们的容光,不禁怆怀自己的身世:四五年以前我也何尝不是如她们那般地幸福,那般地不知忧患为何事!我也何尝不是如她们那般地艳丽而自得!但是现在……现在我所有的,只是目前的苦痛,以及甜蜜的旧梦而已。
可是这一天晚上,我却从公园中带回来了几分的希望。我希望那位俄国夫人能够给我们以良好的消息,白根终于能得到为中国人保镖的差事……我回到家时,很匆促地就这把这种希望报告于白根知道了。但是白根将眉峰一皱,无力地说道:“丽莎,亲爱的!你须知道我是一个团长呵……我是一个俄罗斯的贵族……怎么好能为中国人保镖呢?这是绝对不能够的,我的地位要紧……”
我不禁将全身凉了半截。同时我的愤火燃烧起来了。我完全改变了我的过去的温和的态度,把一切怜悯白根的心情都失掉了。我发着怒,断续地说道:“哼!现在还说什么贵族的地位……什么团长……事到如今,请你将就一些儿罢!你能够挨饿,如猪一般地在屋中睡着不动……我却不能够啊!我还能够,我不能够再忍受下去了,你晓得吗?”
他睁着两只失了光芒的,灰色的眼睛望着我,表现着充分的求饶的神情。若在往日,我一定又要懊悔我自己的行动,但是今天我却忘却我对于他的怜悯了。
“你说,你到底打算怎样呢?”我又继续发着怒道,“当年我不愿意离开俄罗斯,你偏偏要逼我跑到上海来,跑到上海来活受罪……像这样地生活着,不如痛痛快快地被波尔雪委克提去杀了还好些呵!现在既然困难到了这种地步,你是一个男子汉,应该想一想法子,不料老是如猪一般睡在屋中不动……人家向你提了一个门径,而你,而你说什么地位,说什么不能够失去团长的面子……唉,你说,你说,你到底怎么样打算呢?”
鼻子一酸,不禁放声痛哭起来了。我越想越懊恼,我越恼越哭得悲哀……这是我几年来第一次的痛哭。这眼见着使得白根着了慌了。他走上前来将我抱着,发出很颤动的,求饶的哭音,向我说道:“丽莎,亲爱的!别要这样罢!你不说,我已经心很痛了,现在你这样子……唉!我的丽莎呵!请你听我的话罢,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不过我请求你,千万别要提起过去的事情,因为这太使我难过,你晓得吗?”
女子的心到底是软弱的……我对他生了很大的气,然而他向我略施以温柔的抚慰,略说几句可怜的话,我的愤火便即时被压抑住了。他是我的丈夫呵,我曾热烈地爱过他……现在我虽然失却了那般的爱的热度,但是我不应当太过于使他苦恼呵。他是一个很不幸福的人,我觉得他比我还不幸福些。我终于把泪水抹去,又和他温存起来了。
我静等着洛白珂夫人来向我报告消息……
第二天晚上洛白珂夫人来了。她一进我们的房门,我便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因为我在她面孔上已经看出消息是不会良好的了。她的两眉蹙着,两眼射着失望的光芒,很不愉快地开始向我们说道:“对不住,我的丈夫不能将你们的事情办妥,因为……因为保镖的差事有限,而我们同国的人,想谋这种差事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无论你到什么地方去,我的丈夫说,都会碰到我们的同国人,鬼知道他们有多少!例如,不久以前,有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招考俄国人保镖,只限定两个人;喂,你们知道有多少俄国人去报名吗?一百三十六个!一百三十六个!你们看,这是不是可怕的现象!”
她停住不说了。我听了她的话,也不知是哭还是笑好。我的上帝呵,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
半晌她又继续说道:
“我听了我的丈夫的话,不禁感觉得我们这些俄侨的命运之可怕!这样下去倒怎么得了呢?……我劝你们能够回到俄罗斯去,还是回到俄罗斯去,那里虽然不好,然而究竟是自己的祖国……我们应当向彼尔雪委克让步……”“唉!我何尝不想呢?”我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悔恨我离开了俄罗斯的土地,我……就是在俄罗斯为波尔雪委克当女仆,也比在这上海过着这种流落的生活好些。但是现在我们回不去了……我们连回到俄罗斯的路费都没有。眼见得我们的命运是如此的。”
白根在旁插着说道:
“丽莎,算了罢,别要再说起俄罗斯的事情!你说为波尔雪委克当女仆?你疯了吗?我……我们宁可在上海饿死,但是向波尔雪委克屈服是不可以的!我们不再需要什么祖国和什么俄罗斯了。那里生活着我们的死敌……”
白根的话未说完,米海诺夫伯爵夫人进来了。她呈现着很高兴的神情,未待坐下,已先向我高声说道:“丽莎,我报告你一个好的消息,今天我遇着了一个俄国音乐师,他说,中国人很喜欢看俄罗斯女人的跳舞,尤其爱看裸体的跳舞,新近在各游戏场内都设了俄罗斯女人跳舞的一场……薪资很大呢,丽莎,你晓得吗?他说,他可以为我介绍,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已经决定了。怎么办呢?我已经什么都吃光了,我不能就这样饿死呵。我已经决定了……丽莎,你的意见怎样呢?”
我只顾听伯爵夫人说话,忘记了将洛白珂夫人介绍与她认识。洛白珂夫人不待我张口,已经先说道:“我知道这种事情……不过那是一种什么跳舞呵!裸体的,几乎连一丝都不挂……我的上帝!那是怎样的羞辱!”
伯爵夫人斜睨了她一眼,表示很气愤她。我这时不知说什么话为好,所以老是沉默着。伯爵夫人过了半晌向我说道:“有很多不愁吃不愁穿的人专会在旁边说风凉话,可是我们不能顾及到这些了。而且跳舞又有什么要紧呢?这也是一种艺术呵。这比坐在家里守着身子,守着神圣的身子,然而有饿死的危险,总好较好些,你说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