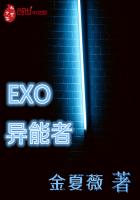王国维作为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最早突破文字考释的范围,将其作为原始的史料,用以探讨商代的历史、地理和礼制。他第一次证实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的可靠程度,并根据卜辞加以纠正,又提出对商周之际礼制截然不同的独到看法。运用甲骨文治商周史,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前无古人的创举,不仅是王国维个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突出成就,更为近代学术史上一大盛事。
虽然《殷周制度论》是王国维在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研究方面的结论之作,但由他和罗振玉开创的“罗王之学”刚刚兴起,即使后来因为甲骨材料大增,后世学者所取得的成就要超过王国维和罗振玉,但他们的研究方向依然没有偏离王国维和罗振玉当初筚路蓝缕之途。
四、备受学者推崇的“二重证据法”
王国维一生在治学上,注重新发现,采用新方法。特别在甲骨文研究中,他将西方的科学方法,与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考据方法成功地相结合,创立并命名了“二重证据法”。这与他年轻时就注重西方之学并两次东游日本,甚至在日本与罗振玉共同整理“大云书库”藏书不无关系。他不仅强调治学要将地下的新材料与文献古籍并重,古文字古器物之学要与经史之学相互表里,“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而且又以阙疑的态度,谨慎地对待学术问题,对甲骨文、金文的考释,力求形、音、义都能说通,因而有较多的创获。这也使他取得了前辈学者和同辈学者所不可比拟的成就。
他对古代历史独到的科学见解,源于其科学的治学方法。陈寅恪将之归结为三条:“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轨则”。
不仅如此,王国维还是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所著“二考一论”和《流沙坠简序》等,均被学界称为划时代之作。其史学论文几乎篇篇皆有创新,后汇编成《观堂集林》20卷。他把历史文献与出土资料密切参证的治史方法——二重证据法,受到国内外学术界推崇。对于王国维在学术上所做的贡献,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与罗振玉研究甲骨文相比,王国维在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从一开始就显得技高一筹,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历史成就最大的是王国维,是他把甲骨文从“文字时期”推向了“史料时期”。因为罗振玉偏重于对甲骨文字的考释和解读,而王国维则以甲骨文字为切入点,利用甲骨文而开始展开对殷商历史进行划时代的研究,这在王国维后来完成的《殷周制度论》中有最深刻而完整的体现,从而使人们更清晰地再次看到公元前1300年,商代第20任帝王、英明的盘庚带领他的臣民摆脱危机从山东“奄”地西渡黄河,经过一次和平的长途迁徙,来到安阳洹水河畔,开始力强图治建立了崭新的都城,并在此传8代12王,经历255年之久。
可以说,“罗王之学”既是甲骨学发展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1928年殷墟科学发掘甲骨文以前,以罗振玉和王国维为代表的研究甲骨学的方法论。这就是:“(1)熟习古代典籍;(2)能承受有清一代考据小学音韵等治学工具;(3)以此整理地下的新材料;(4)结合古地理的研究;(5)以二重证据治史学经学;(6)完成史料之整理与历史记载之修正的任务。”可见“罗王之学”继往开来,影响和造就了几代甲骨学者。
五、王国维之死
由于王国维在国学上的突出成就和贡献,1925年,胡适、顾颉刚等人邀约王国维出任新成立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院长,而他以“时变方亟,婉辞谢之”。胡适又托溥仪代为劝驾,随后,溥仪亲自劝说,并下一道诏书,王国维才接受聘请。
1925年4月17日,王国维举家迁居清华园西院18号,16号是他的书房,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墙全是书。王国维一生的字典里没有“娱乐”二字,他最常去的地方就是琉璃厂和书店,见到自己想要的书,就非买不可。他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就算是休息,随后便马上开始到书房读书写作。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以精深的学识、笃实的学风、科学的治学方法和朴素的生活,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1927年,北伐风声一阵紧似一阵,暑假前校方决定,研究院“学年将满”的第二届学生提前放假。为了酬谢师恩,增进同学情谊,“六月一日正午”为师生叙别会,这也成为王国维与清华师生的“最后的午餐”。叙别会宴席仅有四桌,研究院所有师生欢聚一堂,弥漫着一种喜庆的气氛,而王国维却像往常一样寂然无声,散席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畅谈聊天。当晚,他在家里接待了来访的学生谢国桢和刘节,为两人题写了扇面,然后挑灯批改了学生们的作业,安然入睡。
6月2日,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鱼藻轩昆明湖,面对波光粼粼的湖水纵身一跃自沉而亡,终年50岁。他自杀的原因至今还是令人琢磨不透的一个谜。在他的内衣口袋里有遗书,封面上写着:“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他的儿子。《遗书》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王国维之死可以说是中国近百年文化史上难解之谜。如罗振玉的“殉清”说,陈寅恪的殉传统文化说,杨荣国的悲观厌世说,郭沫若的被逼自杀说,梁启超的恐惧北伐革命说等等。虽然都在努力自圆其说,但又都无法自圆其说。当时的清朝遗老还把王国维比作屈原怀忠而自沉汨罗江,《清史稿》还为他立了个“忠义传”。
1929年夏,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6月3日是王国维逝世二周年忌日,经研究院师生共同努力筹备,“王静安先生纪念碑”在清华园内落成。碑集各方家之大成,梁思成勘定碑址、设计碑式,陈寅恪撰写碑文,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李桂藻刻石。陈寅恪撰写碑文如下: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辞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斯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中华民国十八年六月三日,二周年忌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
现在依然耸立于清华园内第一教室后面的这座纪念碑,也是近代中国文化学术的标志性丰碑。而碑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两句话,也成了公认的对王国维“五十之年”一生的盖棺定论而被学界广泛传诵至今。陈寅恪不仅否认了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殉清或其他的什么原因,还着意阐明了他的死是“独立自由之意志”的体现。也许这应该就是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真正原因。
第三节彦堂董作宾
一、生平
董作宾(1895~1963年)字彦堂,又作雁堂,别署平庐。他是“甲骨四堂”中唯一的河南人。
1900年,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也是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殉国的那一年,董作宾入私塾,并从此断续读过近十年私塾。1915年春考入南阳县立师范讲习所。1921年冬赴北京求学深造。次年在北京大学作旁听生,遍读了沈兼士和钱玄同教授的各年级文字学,课余时间极有兴趣地用油纸影摹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中的甲骨文拓片。1923年至1924年,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作研究生和助教,兼任国学门歌谣研究会的刊物《歌谣周刊》的编校。董作宾在北京大学深造期间,加入了新成立的考古学会,在考古学会的收藏品中见到了甲骨文原片。1924年冬与庄严一起参加了点查故宫文物工作,这进一步丰富了他金石古物的鉴赏知识。1925年至1927年,董作宾先后任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教授、中州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干事、中山大学副教授等职。
董作宾不仅亲自参与殷墟小屯的田野考古挖掘,还主编有《殷墟文字甲编》(1948年)和《殷墟文字乙编》(1948~1953年)二书,共选录抗日战争以前第1~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文13047片,为甲骨文的著录与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甲编》和《乙编》二书,开创了著录科学发掘所得甲骨文的新体例,不仅为以后科学发掘甲骨文的著录树立了典范,也为甲骨文的考古学考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董作宾是我国甲骨学和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知识渊博,广泛涉猎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文学艺术等,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学术著作。由他发端的殷墟科学发掘,奠定了我国田野考古学的基础,培养了一大批考古专家。
董作宾对甲骨文的自身规律和不少基本问题,诸如甲骨的整治与占卜、甲骨文例、缀合与复原、辨识伪片等方面,都做出了不少发凡启例的开创性工作。他用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全面整理甲骨文,为复原商代的占卜和文字契刻规律奠定了基础,使我们今天具有严密规律的甲骨学,比甲骨学“金石文字时期”的“罗王之学”大大前进了一步。
1949年,董作宾随“史语所”迁至台北市,除任“史语所”研究员外,还被聘为台湾大学教授。1951年至1955年8月曾接替傅斯年担任“史语所”所长。1963年病逝,终年68岁。
二、“小屯考察”及殷墟田野科学发掘
1908年,罗振玉确定甲骨文出土地为小屯,他经过多次派人和自己亲自前往小屯考察,最终,他得出“甲骨已尽”的结论。1927年秋,联合顾颉刚等人创立了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并自任所长的傅斯年,认识到对于考古特别是甲骨文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知道小屯这个地方到底还有没有甲骨文,毕竟离甲骨文的发现已经过去近30年了,地下的宝贝还会有吗?傅斯年强调学术研究要尽可能地占有材料,甲骨文以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而受到他的重视。他选聘当时因母病回南阳的董作宾为通信员,使命为调查洛阳三体石经及殷墟小屯甲骨文出土情况。
董作宾赶赴安阳,亲自去小屯考察。他先是用三块大洋购买了百余块甲骨片,看到卖甲骨的多是妇女和小孩,并得知古董商到小屯收购甲骨文,多是高价收大片而不要小片的,一片大的要四五块大洋。随后,他又以铜元十枚为酬金请村中霍氏子女为向导,来到了小屯村北边经常出土甲骨文的地方,经过仔细查看,也捡到几片没有刻字的甲骨。
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董作宾得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的结论,完成《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邮寄给傅斯年。报告中写道:“甲骨既尚有遗留,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之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他将自己经过思考的计划,和“分区”、“平起”、“递增”等挖掘方法以及“用工、经费、工具、时间”等安排一并函致傅斯年。他的报告得到傅斯年的认可和赞同。
正是董作宾的这次安阳小屯殷墟调查之行,开启了中国近代大规模田野科学考古的新纪元,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天地,也促成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自1928~1937年历时10年之久、先后15次进行的大规模科学发掘工作,而寻找甲骨文是殷墟科学发掘的直接诱因,同时宣告了殷墟甲骨文“盗掘时期”的结束,而开始了由国家学术研究机构有组织进行的殷墟甲骨文“科学发掘时期”。
安阳小屯殷墟发掘应该是真正意义上中国考古学诞生的标志,李济、董作宾、傅斯年三位学者共同努力促成了这一盛举。最早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后来成为甲骨文分期断代和殷商天文年历研究的主要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