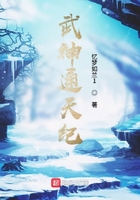柳七苦着脸掸背后的灰:“力道不小,想来这几日,你们两只肥羊是被人好吃好喝供着呢。”
“你还说。”若冰作势捶他,“我这两天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是吗?”柳七笑得别有深意,“前些个是地方不好,昨儿软香玉枕的,怕是做春梦了吧?”
“你——”若冰一惊,不由生出几分挫败感。怪不得这厮今儿见了她半点惊讶也无,敢情昨儿晚上是在徐府蹲点呢。“你怎么就知道……哎,我说你也太神了。”
这回轮到柳七敲她脑袋:“少贫嘴。你也不想想,君凌逸什么人。虽是微服,可好歹是个钦差,钦差在西陵地界出了事,徐寿还要命不要?再说,以君凌逸的性子,他身边会什么人没有?还有那秦宝,这都多少天没见人了。——卿卿,你家夫君,可不是个好相与的主。他那心思,深着呢,谁知道这回又唱的哪出。这看戏和入戏的,不定是谁呢。你就瞧着吧,这些个匪类,纵是千年道行,孙猴子再生,他也翻不过如来佛的五指山。”
柳七料得不错。十日后,衙门有了消息,说除了一人在逃,其余全部落网。
君凌逸因堤坝竣工在即,诸事繁忙,故略略看了几眼,交代了句按规矩办,便没再过问。
这态度令若冰生疑。虽说内情她不甚知晓,但可以肯定,如此缜密的计划,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想的出来的,所谓的掳人劫财不过是个幌子,用来“留住”君凌逸的幌子,且极有可能,那五万两的狮子大开口,是禁不住诱惑的临时变更之举。问及柳七,对方却只是神秘莫测地笑:“别急,晚上带你去个地方。”
入夜,两道黑影先后没入一条小巷,然后七拐八拐进了巷底落了漆的朱门。秋风萧瑟,不知是错觉还是别的什么,若冰只觉寒意沁人,空气中混杂着令人作呕的腐朽的味道。“这是——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看着满屋横七竖八的棺木,若冰心里打了个突。
柳七没理她,径自摸到最靠里的那个,然后冲她招手:“你过来,看看他这儿。”
若冰依言上前检视。——剑伤,伤口细窄,长不过两寸,且几近心脏,粗略看来,该是致命之处。
“怎么样,有没有什么不对?”
若冰摇头:“我毕竟不是仵作。——对了,这人哪儿来的?”
“前些天从衙里运出来的,据说是重伤不治。”说着,柳七指了指他伤处,“再看看,觉没觉得眼熟?”
若冰恍然想起那日打斗柳七的一剑:“原来是他!怎么,你怀疑他的死有蹊跷?”
柳七点头:“那天我下手虽狠,但不至于要了他的命。我就不信,他早死不死,偏这会儿人逮着就咽气了。还有那天,衙门的人才过去,那边就跑了个干净,只留了这个半死不活的,动作也忒快了。”
“你的意思是……”
柳七作了个“嘘”声:“佛曰‘不可说’。搞不好,是‘那边’的。”
“那你预备怎么办?”
“怎么办?还能怎么办?!人都死了,我又不能到阴曹地府去问。算他倒霉。再说,君凌逸都不急,我急什么。”柳七打了个呵欠,“走走走,回去睡觉,困死了。”
若冰复看了眼棺木,举步跟上。
夜,正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