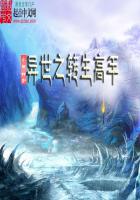咣当咣当......
压在井口上的石板,剧烈频繁地晃动起来。
地面上也是震颤起来。震感穿透鞋子,震得脚底板麻乎乎的。从井里传来咕咚咕咚,像是重物砸水时发出的声响。
我和二伯面面相觑,神色恐慌,不知所措。
到后来,石板不再是抖晃了,而是一下一下地往上跳了。不禁令人担心它突然翻个滚,从井口上弹到旁边去了。
“快点儿跑吧,摇头棒子要钻出来了!”二伯突然大吼。
我还没来得及拔腿,那只怀孕的母狼狗拖着大肚子奔过来了,一双本来褐黄色的眼睛变得猩红似血染,一下子跳在那块跳动不止的石板子上。
说来煞是奇怪,不知是狗太重,或是其它的缘故。那块厚重的石板子停止不动了。竟然让母狼狗给压得死死的。
连井里发出的“咕咚咕咚”砸水声也消失不见了。地面上亦无了震感。
母狼狗正在大张着嘴巴,急促地喘气,透明的口水顺着舌尖一颗一颗地滴淌下来,应该是汗水而非涎夜,虽然地上散落着酱油涂大肉块的供品,但它应该不会是在这个时候犯馋吧,瞧它样子,明显处于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二伯见它镇压有功,捡起一块酱色大肉扔到它嘴下,它果然是不吃的。
“这条狼狗可真邪性,连摇头棒子都能吓跑!”二伯看起来像是发自内心肺腑地赞叹道,盯着母狗的两只眼睛开始发光。
他是个特别喜欢狗的人。家里养着一条血脉很纯的藏獒。曾有人出重金要收购他的藏獒,无论给多少钱,他都不舍得卖。
可惜,他那条藏獒是公的,下面的生殖器官不知让谁给偷偷地阉割了。本来市场价值十八万,被骟了之后,连两万都卖不到了。把我二伯给气得躺在床上,用被子闷了好几天,不吃不喝的。一提起这事儿,就会令他恼得将牙齿咬得咯噔咯噔作响,发誓若知道是谁将他的藏獒给害的,自己一定会拿刀子将对方捅了。
“这狗的肚子可真大,一定怀了不少于七八个崽!”二伯语气肯定地说道。
见那狼狗眼珠子上的猩红已渐渐褪下去了,不再张口急喘,恢复了往日的柔态,甚至有点儿疲倦和颓废。我才敢上前去,探手抚摸着它的脑袋,对我二伯说:“你可能还不晓得,这条狗已经怀孕了两三年,肚子里面的东西就是产不出来!”
“咋回事啊?为啥它产不出来?”二伯面露惊讶地问道。
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你看它的肚子都胀这么大了,再胀下去恐怕肚皮都要撑破了,实在不行,你带它去看看兽医,说不定里面是个囊肿。如果真是个囊肿,得尽快给它做手术才是,一条狗你既然养了它,就应该好生对待。刚才要不是它将井里的摇头棒子镇压,难保不出啥乱子!”二伯说道。
如果狗能听懂人话,应该会被他这番话感动。
可我家这条母狼狗好像听不懂人话,就算能听懂人话,怕也分不清好话歹话。它倏然往前一扑,一口咬住了我二伯的手掌。将他手掌上的肉给撕下来了一大块子,落个血淋淋的。
疼得我二伯咬住牙,腮帮子乱颤,发出老鼠叽叽一样的声音。我取来一些烂布,一边给他包扎着,一边说你要嫌疼,就叫唤出来,干嘛咬住牙不放。
他说这大年下的不能瞎叫唤,免得惊跑了财神爷。他捡起一块砖头,用力砸向母狼狗。母狼狗没有躲避,也没有害怕,而是站在那里不动,结结实实地挨上了这一砖。二伯气恼得慌,又从地上捡了一块砖头,高高扬起胳膊,准备再次朝狼狗砸下来。
可母狼狗的肚子忽然突突跳动起来,就像一只装满水的气球一样,弹性很足。导致它嗷嗷惨叫起来,前膝一跪,后腿弯曲,慢慢歪倒在地上,四肢乱蹬不已。毕竟我二伯是个爱狗人士,见它这般,觉得可怜,便饶过它这一次。
已经下午了。
太阳沉西。
母亲和我大娘还没有回来。虽然脑子里记得母亲曾警告过我,没事儿不要和我二伯搁一块儿呆着,他就像一条不通人性的疯狗一样,冷不丁就咬你。但最终没能经住二伯一而再三地催促,我又很想念大肉掺葱的味道,就管不住自己的双腿,和他一起回家了。
路上,他一遍遍重复地说要给我下饺子吃,保证管饱。
到了他家。刚进堂屋,一股浓浓的腐臭味道直钻入我的鼻子里,像极了炎热夏天谁家办丧事,尸体没往冰冻棺材里搁放那样。我问二伯这是啥味儿啊,家里是不是有死老鼠了。他没有立即搭茬,阴沉着一张脸,掏出塌扁的烟盒子,揪了一根叼在嘴上抽着,拿眼狠狠瞪了我一下,才没好气地说,你咋恁些王八孙屁事儿呢,等着吃饺子就得了。
见他变成这副样儿,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子,忖道:“糟了,悔不该不听母亲的话,这一家伙转了性子,待会儿还能有我的好果子吃吗?”
二伯扔给我两个大萝卜,说想吃饺子可以,你先盘馅儿吧。怕我逃跑,他用绳子系了一个活套,套在我的脖子上,一拉就收紧了。像牵条狗一样牵着我,手上抡舞着棒槌,命令我给他干活儿。
除了欲哭无泪,我别无他法,将两个沉重的大罗卜抱到院子井上洗了洗,又找个擦菜板,将萝卜擦成丝条状。再将萝卜丝放入大锅里,兑上水。把锅坐到煤炉上,打算把它烧开,使萝卜丝煮熟。
要不就说光棍子过得家不像家。这大年下的,连煤炉上都没个火星子,是完全熄灭的状态。给煤炉子生火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儿。我找些玉米芯点了,扔进炉膛里,再趴下来,高高地撅着屁股,鼓着腮帮子,将嘴巴往煤炉下面的出风口里呼呼吹气。
一连生了好几次,火还没起来。二伯恼了,一脚蹬在我的屁股上,令我身子朝前一冲,额头撞在了用铁铸成的煤炉上,冒出一个大疙瘩。我扭头怒吼道:“你跺我干啥?”“看你这张蠢脸,我跺你能咋!”说着,二伯又抬脚照准我脸上了狠狠跺了一下子。
总算把火生起来了。
烧着锅时,我也没闲着。
二伯从冰箱里掂出两块冻得硬梆梆的猪肉,让我用开水烫烫,择掉上面的毛,然后剁碎。
忙到了天黑。我总算把饺子馅剁好了。二伯又让我和面。
正当我和着面时,听见母亲在大街上喊我了:“杨大宝,你这个鳖孙,死哪儿去了?恁娘都快死了,你还不回家!”
二伯骂道:“这个刁妇,大年下的说死死的,也不怕大年初一突然暴毙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农村人有在自家大门上点火放炮的习惯。
鞭炮声响个不听,烟花冲上天空,美丽绽放。
我却窝在二伯家的厨房里暗自叹息不已,手上不停地揉着面团子,身上汗水泱泱的。二伯正坐在锅灶台上,一手牵着拴在我脖儿梗上的绳子,一手里掂晃粗大的棒槌,正在耷拉着一张脸,虎视眈眈地监视着我。
母亲的咆哮声越来越近了。
很明显,她往我二伯家这边找过来了。
见我二伯的脸上有些慌了。
其实上他不害怕我母亲。他是害怕我母亲带着我大娘一块来。
嘭嘭......
有人在外面使劲拍院大门。
“宝子,你先去床上躺着,蒙上被子别吭声,我去应付一下恁娘。记住啊。别给我乱吭,不然我饶不了你,我不想让这根棒槌因为打爆你的头而溅上血,大年下的,见血不好,你懂不?”二伯一边扯着绳子把我往堂屋里带,一边压着嗓子小声叮嘱我,面目狰狞。
我点了点头。
进了堂屋,再拐入左侧的卧室,他指着床,让我自个上去。
看见我脱下鞋,上了床躺下后,他才出去了。
屋里没开灯,只有窗外烟花爆出的光芒透进屋里,明暗不定的。我所躺的这张床很大,还是铁的。
其实这是我二伯和南宫霞结婚时,专门找铁匠定做的大床,用料很足,价值不菲。
我发现,床的躺着不止我自己,还有另外一个人。而且恶臭的源头,正是来自我旁边这个人身上。吓得我打了一个激灵,赶紧从床上跳下来,顾不上穿鞋子,踮着光脚在墙上一阵胡乱摸。摸到开关将灯打开了。
只见几条宽大的被子将整个床覆盖得严严实实的。床上靠墙位置的那片被子有明显的突起。看这突起的硕大形状,床上应该是躺着一个巨型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