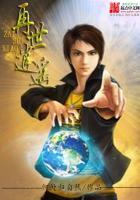克里斯的圣经学习小组没能使我体验到耶稣walk with me,但我在加入小组的一个月之后体验了一把六道轮回:在接下来的六百零六年里不断地转生又逝去,经历了诸天之下的每一个世界,或者按照我手表告诉我的,用了三分钟经历了这一切。
这并不稀奇。任何加拿大人都可以随时获得这种体验,无论是六道轮回还是时空穿梭,甚至更神奇的东西。
因为在这里weed是合法的,而且价格只是比香烟略贵一点点。
如果你走在温哥华的主要街道是总会闻到weed味,难免不会想去尝试一下,就如同来到云南就会想尝一尝当地的米线一样。
按照官方的讲法,这东西对人身体的害处比啤酒还小,成瘾性甚至略低于辣条。它可以在短时间内把人内感中的时间与空间两条刚性坐标轴熔化成麦芽糖丝那样的东西。
我能证实此言不虚。
但是在我看来,这东西对人的损害极大——我似乎永久性地失去了时间感。比如,我此时此刻真切地认为《阿凡达》是在四百五十年前的2009年上映的,但Win10桌面右下角的时间栏显示此时此刻是2017年12月28日。
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比人类的理智更重要.如果伊曼努尔.康德的内感时空坐标轴熔化了,他便无法写出《纯粹理性批判》这样伟大的旷世奇作,至多仅能以格言体出名,成为十八世纪的尼采,去主张永恒轮回什么的。我不擅长格言体,而且想完成启蒙运动未竟之伟业,所以吸食weed的经历仅此一次。当时是黑色星期五大酬宾,我买了两克,买二送一,获得了总共三克Hybrid(比Sativa和Indica稍微高级一点),税前价值28刀。吸了零点三五克就进入了迷幻状态。第二天早晨就发誓戒掉了。剩下的两点几克还保存在我的书架上。这个玻璃瓶与《加拿大刑法典》,《合同法》,《移民法》,《法律研究方法》,《刑事程序法》以及斯若干本蒂芬金的英文原版小说堂而皇之地放在同一层,一推开屋门就可以进入视野。
15路公交车上只有我和基督徒克里斯这两个乘客,这对于加拿大的公交车来讲已经算是很拥挤了。15路沿着纵观温哥华的坎比街一路向南,驶过了百老汇城市中心站之后,进入了毗邻伊丽莎白公园的别墅区。在新的市政规划之下,这个别墅区的物业被一个街区一个街区的整体买下,很多已经被推平。从地基的深度看,废墟之上将要建起的是高层公寓,因为有伊丽莎白公园作为景观,一定价格不菲,均价百万加币以上。回想唐人街,实在是阴阳殊途。
公交车在东西向的35街车站停下,马路对面就是我租住的坎比街5070。这幢别墅自从Eric徐和他的弟弟徐堂接手之后,已经有三百七十九年没有修剪过院子里的树木了。这些树木在雨林气候的温哥华就像基因突变一样恶性地,疯狂地生长,把5070号别墅吞噬在绿色怪兽的腹中。没有任何缝隙的厚重的松树针叶与枝条,遮挡住了阳光,形成了一个洞窟搬的林荫道。黑暗与疯狂,以及令人窒息的漫无目的不知所往的生命力,是我每次步入这个宅院时所首先经历的。
但此时此刻,这种黑暗却被刺眼的光划破了。几排警灯,刺眼地转动着。坎比街5070的植物洞窟入口被四辆警车团团围住,黄色警戒线圈起了四面院墙。
“Fuck me,WTF is going on here?”
警车的确围堵在坎比街5070号门口.是我的住所出事了.克里斯加快了脚步,想尽快搞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则放慢了脚步,因为我觉得这事恐怕和我有关。
是不是那里面掺杂了其他违禁毒品?不可能,即便可能,谁能发现呢?有谁会进入我的房间打开我书架上的玻璃瓶然后检查里面那堆干草团的化学成分呢?或者是被徐堂三岁大的女儿误食了?那门口应该是救护车才对。到底是怎么回事?失窃?不可能。这幢老旧别墅里的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一文不名的屌丝,丢掉笔记本电脑和公交卡不能能招来这么多警车。抢劫就更不可能了,坎比街5070从Eric徐兄弟搬进来之后就从没有锁过门,前门和后院木门,还有连通后院的地下室全都没有锁过。这里的治安就是好到这种程度。
到底是为什么?啧,只可能是weed!妈的,我当时应该早点扔掉这些weed才对。
我是不是搞错了?没有!是合法的!我也是在拥有政府经营许可的分销店合法购买的高级Hybrid,被称为Blue Dream的品牌货。这事情应该与我无关。我必须坚称:我把这两克多一点的weed放在我二楼的房间里, Eric二弟一家生活在一楼,没有任何理由上二楼,而且我把那个玻璃瓶放在了书架的最上层,一个三岁的小孩子根本够不到,所以即便他的女儿误食,我也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风险,所以我是没有过错的。而且吞下三克weed也不至于对人体产生致命的影响,即便是三岁大的小孩、不!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会产生影响么?
Oh,fuck!是《死侍》,因为我非法下载了这部电影!加拿大对非法下载极其敏感,动辄罚款六七千千刀。也许《死侍》的种子引来了第一辆警车,然后他们打开我未加密的移动硬盘看到其他六万部好莱坞电影之后叫来了大队人马。这恐怕是加拿大本世纪最大的犯罪事件了。
无论如何,我不能转身就走,我们已经出现在警察的视野中了。我跟在基督徒克里斯的后面,来到了房门口。一个印度裔的漂亮女警拿着一个定制的三星平板电脑,迎向我们。
“Officer, may I ask what happened here?“虽然我站在克里斯后面,但抢先问话。我很后悔,因为这给人一种做贼心虚的感觉。
“有人死了“,女警用流利的美音答对着,然后核实了我们的身份。
“Detective Schrute,the tenants...”女警向房内的同事示意,然后重新面向我们。
“到底是谁死了?“
“你们的室友,有三个人死了。“
“三个人!?出什么事了?煤气中毒?“
“不。“
“那是什么事故?”
“不是事故。”
“那是怎么回事?”
“尚无确切结论。我建议你此时不要问太多。”
“到底是谁死了?“我一边问一边向别墅里张望。我看到Eric唐裹着毛毯,失神地坐在台阶上,接受着警察的盘问。Eric还活着,我的确不希望他死掉。
“是堂.徐,以及他的太太和女儿。“
我没有看到救护车,一定是已经开走了,这说明此时距事发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两个离开的时候他们还好好的。我听到他们在房间里嬉闹,好像很开心似的。”克里斯说,“我们一天都不在这儿,我们去了唐人街。”
“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信息,还要继续核实。”女警打着官腔,这真是个消极攻击性的典型案例,她就是不说“我知道你们一整天都不在这里,你们没有任何嫌疑,放心吧。”
“我可以进去么?我猜不行吧?我只是问一下。”我不知为什么说出这么一句。
“你们最好待在这儿,和我一起。”
“愿上帝保佑这些可怜的灵魂“。基督徒克里斯垂下双目,状若菩萨,为他们絮絮叨叨轻声祷告。女警连眼睛都没抬起来一下。
这时候,Eric徐失神地走出来了,我们二人目光交错,我能看到他瞳仁深处灰蒙蒙的恐惧的余烬。我想对他说点什么,但引领他的刑警摆手,轻蔑地阻止了我,并且在扶着Eric肩膀的手指上轻微施压,以使他更快速地通过。这是一个年轻的白人刑警,便装,穿着登山鞋和North Face的防雨夹克,浅蓝色的瞳仁,皮肤薄的像肠衣,下颚留着金色的短须。此时我尚不知晓,直到几个月后的人类灭绝事件为止,我都会和这个家伙纠缠不清。
“他们上吊自杀了,美娜也死了,被勒死了。他们都死了。” Eric钻井警车前忽然回头对我喊了一声,然后就像熄灭了的灯泡,消失在黑暗的警车里。
“Daughter, not his daughter....“我望着Eric的背影,语带哽咽,转向女警。“This is insane,it's crazy.....“。女警的注意力显然被Eric吸引了。当Eric按指示钻进警车之后,男刑警回头对她示意,她心领神会。
“刘先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希望你能和我们走一趟。还有你,魏先生。”这是基督徒克里斯的姓。
“Please call me Chris,and,can I get my laptop and charger? I have work to do tonight.”
“No, you can't.“
克里斯随后按照指示钻进了另一部警车。我表示需要几秒钟调整一下呼吸。女警冷淡地点点头,然后掐起腰,用这个肢体语言表示“我可不打算给你很长时间”,而那个白人刑警,此时正扶着敞开的车门看着我。他敞开的North Face防水夹克在往来车辆造成的气流中摆动着。
他能看到了什么?一个无辜的人,有着完美的不在场证明,正在为自己的室友一家的突如其来的灭门惨事深深震撼,呼吸紊乱,不知所措地回身,扶住离自己最近的一课松树的树干,剧烈地呼吸,消化着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他没有看到的是我狰狞的笑容。
这笑容根本不是表情,而是一种体态,是除了表情之外的一切身体特征,这些征象中的每一个都轻微到难以被人察觉:背部躬起,足尖略向内收缩,扶着树干的那只手微微握成拳,双瞳虽然被悲哀充盈,但余光却审视着周围的一切。
真不敢相信,我成功了。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待续
下次更新:2018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