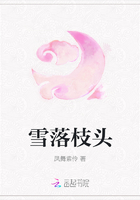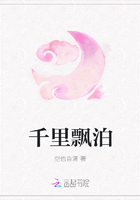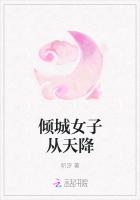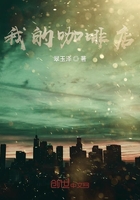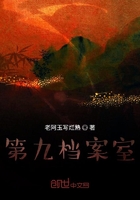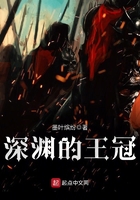曹伟能怔怔的看着王政君,又怔怔的看了刘骜,竟不敢相信只手遮天的太后无能保全自己和孩子。她所有的幻想转瞬变成了泡影,静静缓了片刻后才能正视这个事实,整理了情绪向刘骜与王政君行了大礼,道:“奴婢懂陛下和太后的难处,奴婢有幸与陛下相遇已属万幸,奴婢很满足,不敢再奢求什么。”
“既然你想通了,明日就启程,明哲保身,让你走是为你好,出宫以后切莫透露孩子的身世,说话也得谨慎些,否则就会招至杀身之祸。”除了这些事宜要警告她,刘骜还担心她的品行是否能教育好孩子,叮嘱道:“你即为人母,就当有人母品行,须蹲守妇道、三从四德,不可再入风尘。”
“奴婢知道了,一定会把他培养成为一个正直孝顺的人,”曹伟能心里失落,捧着肚子心酸的乞求道,“孩子既然不能入帝皇宗庙,还请陛下为孩子起一个名字,有了父亲起的名字,孩子就不会是野孩子。”
刘骜思索了片刻,“逸字甚好,愿他一生安逸无忧,自由自在。”
“谢陛下赐名。”
刘骜安慰道:“你也不必灰心,待永巷安宁下来,依旧接你回来,你去收拾吧。”
“奴婢告退。”
曹伟能离开后,刘骜坐到王政君身旁,王政君见他神色不佳、默不作声,似乎有了种陌生的景意。王政君:“骜儿你还在生母后的气。”
刘骜淡淡的摇头,“母子之间还有什么气不气的,母后可怪儿臣杖毙了淳于长?”
“是他咎由自取罢,只可惜了阿娥……”王政君欲言又止,本想教他好好待班恬,班恬亦是不可多得的贤惠女子,虽然班恬口上说不念他,但王政君知道她一直在等他回头,可他一心在不古身上,劝也是无奈。
“阿娥的事原是朕不好,事已至此,母后便不要再沉浸在痛苦当中,母后未来的路还长着……”刘骜也欲言又止,苦涩的味儿卡在咽喉,不古说他绥和二年殁,时下正是绥和元年,在生命被限制的时光里,他无时无刻不忧心,却只能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王政君察觉刘骜眉心重重的心事,疑惑问:“陛下想说什么?”
刘骜:“儿臣想,大汉一天不立太子,前朝后宫就不会有一天安宁,现在细细看着母后,才发现母后衰老了很多,为母后不再担心受怕,儿臣想早立太子。”
王政君:“那陛下意下如何?”
刘骜斟了一杯热茶,端起茶杯低头细细闻着茶香,“令中山王和定陶王入京,册立太子。只有朕无立太子之人选,俩太后才会转移她们的矛头,指向她们彼此,我们只管作壁上观。”
王政君苦口婆心:“骜儿你不了解俩太后,一旦立她们子孙为太子,她们下一个计划一定会是逼你退位,为巩固政权,只怕她们会杀害你。”
“母后不必担心,儿臣自有对策。如今大司马王根已老,王莽胸怀大志、血气方刚,儿臣欲改立王莽为大司马,让他掌朝廷大权,到时无论谁为太子,我们依旧大权在握。”
王政君颇感诧异,骜儿居然给王氏放权,隐约感觉不对,“陛下……的意思是不仅令他们一人做太子,还纵他们做皇帝?”两王在封地尚且害得龙嗣无一幸存,莫说封了太子留在京城,骜儿岂不是断送自己的后路。
刘骜饮一口茶,他时间不多了,希望在这有限的时间里为母亲善后,“母后不担心,无论他们谁做天子,你都是独一无二的太皇太后,只尊您为母后,儿臣退位后就可去过自己的生活。”
王政君捶着胸:“骜儿你为何这么蠢,你以为他们会放过你吗?”
刘骜没有回答王政君的话,“母后认为儿臣还有别的选择么,儿臣已过了而立之年,如今市井议论纷纷,百姓急盼着太子,大臣纷纷上奏,与其到时候百姓联合言劝朕立太子,朕还不如主动招封王进京竞选,以示我们让贤之意。日后他们敢动母亲一丝一毫,便是忘恩负义,必招天怒人怨,就可令王莽名正言顺把他们蹿下台。母后,时下我们要做的是笼络民心,只要民心所向,母后才会后顾无忧。”
王政君无力反驳,“请陛下三思而行,再与大臣们细细商议。”
刘骜冷静了情绪,“儿臣饿了,母后可愿陪儿臣一齐用膳。”
“好好好,”儿子的一句话总能令母亲忘乎烦恼,王政君喜不自胜,难得骜儿不计前嫌,如此顺心顺意,“骜儿想吃什么?”
“陪母后用膳,吃什么都香,儿臣日后每日都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