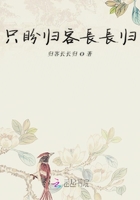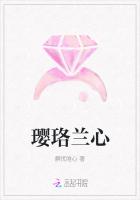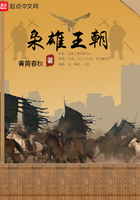莘县属于运东、卫东地区。冀南部队已经在这里打开了局面,站稳了脚跟。宋任穷率领部分军区机关人员,于六月中旬转移到了莘县王寨乡杨庄村。
该村有“三多”,即沙荒地多、树多、苇子多。全村五百口人,三千亩地,其中大都是一人多高的苇子地。杨庄村四周全是三丈多高的土围子,设有东门和西门。这种环境非常有利于八路军开展抗日工作。
“五·二六”大扫荡后,冀南党政军机关所处的环境更加恶劣。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灾情持续发展。继一九四二年大旱,粮食欠收后,一九四三年一至六月,仍然滴雨未下。不仅夏粮收成无几,秋粮也播种不上。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绝境。二、日伪军到处抢粮,甚至见什么抢什么。这更加重了老百姓的苦难。三、八路军队伍严重缺粮。出去征粮的同志,常常是奔波一天,仍然空手而归。四、冀南党政军机关的活动范围被严重压缩。目前,只能在邱县北部和元城一带的两小块根据地内活动。而且,敌人最近的扫荡重点逐渐从北向南转移,兵力也大多向南部集中。这就更加重了这一带的恶劣环境。……
以上这些情况,宋任穷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经过和其他干部研究,做出一项决定:向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申请,将冀南党政军机关的部分人员,转移到相对形势较好的冀鲁豫第三军分的莘县一带。这样就将冀南党政军机关的活动范围扩展到了运河、卫河以东,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回旋余地。
宋任穷来到杨庄后,住在夏少增家。钟月林负责司令部的无线电联络。天线就设在宋任穷所住的院子外面的一棵大槐树上。村民看到大槐树上缠满了电线,很是好奇。钟月林就解释说:“这是电鸟用的。”
宋任穷工作之余,最大的一个嗜好就是踢足球。因杨庄缺少场地,他就改为踢毽子。他踢得既高又准,还次数多、时间长,村里的人都甘拜下风,赢他不过。
宋任穷在抓好军事工作的同时,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在杨庄村建立了党支部,夏少增为党支部书记兼村长,夏云龙、夏炳银、王景贤三名党员为党支部委员。村里成立了妇救会、儿童团和民兵连。在原有四名党员的基础上,又发展其他五名积极群众为党员,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在杨庄的影响下,武家河、余庄、尧头等十几个附近的村庄,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发展党员20多名。
七月上旬,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做出决定,将原来由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管辖的堂邑、冠县、莘县、清平、朝城、卫东六县,划归冀南军区管辖。冀南军区以上述六县成立了第七军分区。赵健民任分区司令员,肖永智任政委兼地委书记。同时将冀南三军分区的第二十二团调归第七军分区做主力团。
此时,钟月林已经怀上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很快就到临产期。当时,农村有个很迷信的说法,让外人在家里生孩子不吉利。宋任穷为了尊重群众风俗,扶着大腹便便的钟月林,准备到村东头的窑洞中生产。
走到街上,村民郭文清的母亲拦住他们问:“这是干嘛去?”
宋任穷说:“她已经到了临产期,我们到村东头的窑洞里去住。”
老人不解地问:“到了临产期,为什么要到窑洞里住?”
宋任穷说:“咱们这里不是有一种说法吗?让外地人在家里生孩子不吉利。我们要尊重群众的风俗习惯。”
老人一听,立刻瞪大了眼睛:“这怎么能行!哪有在窑洞里坐月子的!什么不吉利啊?我不怕!你们到我家去住吧。”说完,不容分说,拉住钟月林的手,硬是把她拽到自己家里。
就这样,老人整整照顾了钟月林一个多月。宋任穷夫妻俩非常感动。临分别时,钟月林激动地跪在老人面前,认老人为“干娘”。
老人也含着眼泪说:“闺女,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娘家!……”
……
冀南区的旱灾持续发展,直到八月仍然滴雨未下。许多水井干涸,河水断流,土地干裂。一专署的大名、成安等县夏粮几乎颗粒无收,秋收亦是寥寥;六专署的冀县、二专署的巨鹿等县,入秋后仍是白地一片;灾情较轻的南宫县在二百三十一个村子中,也有一百零七个村庄属于“无苗区”。全冀南有八百八十四万亩耕地没有下种。有些地方掘地三尺也难看到一点湿气,使人的饮水都成了问题。
特大旱灾尚未结束,又发生了大面积的蝗虫灾害。蝗虫开始起于太行区,使太行区受到严重危害。八月,大批蝗虫飞抵冀南区。蝗虫飞来遮天盖地,最大的蝗群方圆几里,它们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吞食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
接着大旱、蝗灾之后,冀南地区又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水灾。自八月下旬以来,冀南阴雨连绵。九月初,连降七天大雨,暴雨成灾,洪水泛滥,滏阳河、卫河两岸尽成泽国。水势稍退后,群众冒着连绵霭雨,火急地进行补种、抢种,以期晚秋能收获一点粮菜。然而,敌人又于九月下旬,先后在临清县的大石桥、武城县的渡河驿、夏庄等处将运河掘开了口子。在漳河县南上村掘开了漳河河堤,在鸡泽县境内破坏了滏阳河堤,河水漫溢,平地积水一尺多,使大片肥沃的土地,再度陆沉,受灾地区多达三十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馆陶全县百分之六十四的村庄成了水村,武城县被淹一百一十个村庄,淹地面积占全县五分之三,清河县被淹面积占四分之三。故城县也大部被淹。任县和隆平县简直成了滏阳河的储水湖,房屋坍倒,人畜漂没,仅剩一片半浸在水中的断壁残垣。
在遭受旱灾、水灾之后,冀南部分地区还遭到了冰雹的严重袭击。冰雹大者如鸡蛋,群众在水旱灾之后抢种、补种的一点晚苗和蔬菜,全被砸毁。
祸不单行。冀南军民在连续遭受了旱灾、水涝、蝗虫等灾害后,又遭到了一场可怕的霍乱等瘟疫流行,广大群众灾病交加,苦不堪言。传染病的猖獗流行,夺走了千百万人的生命。
严重的自然灾害,无情的瘟疫疾病,使富饶的冀南平原杂草丛生,满目荒凉。人们不得不以树皮、树叶、花生皮、棉花籽充饥。有些地方连树皮、树叶也吃不到。许多人被饿死。巨鹿县饿死五千多人,因患霍乱而死亡三千多人;曲周县东王堡村在一百五十户人家中,死亡几百人,其中因传染病死亡者占五分之四;该县北辛庄村四百户中,饿死四百多人;在八月五日至十月十七日,不到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威县南胡帐村一百七十户中,死亡二百三十多人;邱县梁二庄村三百户中死亡四百多人。瘟疫流行最严重的垂杨、枣南、清河等县死亡人数更多。清河县王世公村曾在一天内死亡四百多人,黄金庄死亡二百多人。垂杨县段芦头一个集日因饥饿倒街而亡者三十人。……很多地方几乎是“无家不戴孝、村村有哭声”。
除了饿死的,病死的外,还有许多人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外地。一些村庄成了“无人村”。
面对如此严重的天灾人祸,冀南党政军干部并没有被吓倒,更没有退缩。他们一方面紧急从冀鲁豫军区调来小米三百万斤,麦种五十万斤,救济灾民。并请求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向冀南区发放贷款一百三十五万元(冀南票),贷粮四十五万斤。一方面号召大家富济贫,穷帮富,团结互助,共渡难关。并积极带领大家打井挖渠,开展生产,进行自救。
鸡泽县孟贯庄村有个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连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因为她的儿子叫荣林,大家都叫她荣林娘。荣林娘在村里找了几位农村妇女,成立了一个纺织小组。他们贷棉花纺线织布,织一匹布可挣二十二斤谷子。很快,由一个组发展到十四个组。在她的带领下,全村妇女都组织起来了。她还在村里组织了二十二个生产互助组,一边种地,一边熬哨盐,进行生产自救。由于荣林娘带领妇女生产自救,取得显著成就,被评为冀南区劳动模范。
为了减轻群众负担,冀南区领导机关继续精减机关人员。军区司令部只保留了四个科,十一名干部,军区直属队工作人员共一百六十一人。团直属队占全团人数十分之一,军分区机关人数占分区部队的九分之一。同时,继续减少部队人数。截止到八月,骑兵团、七七一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五个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他们又抽出大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
当时,只留下宋任穷、王任重、王蕴瑞和朱光,在冀南坚持工作,群众称“咬牙干部”。区党委,行署以及军区的后勤机关都转入了地下。他们都穿便衣,干部、战士都睡在一个屋子里,都打地铺。
那时,作为八路军的指挥员,不仅要带头吃苦,在感情上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考验。宋任穷的三个女儿就先后被寄养在老乡家里。
大女儿宋小琴,一九四零年出生在山西省辽县羊角村一二九师医院里。一个月后就被放进一个筐里,由战士用扁担挑着,随父母回到冀南平原。当时形势严峻、战事频频。尽管钟月林舍不得,还是在宋任穷的劝说下,将五个月大的女儿送到老乡家寄养。
二女儿宋小平,一九四一年出生在邱县北部的军区机关医院里。由于形势更加严峻,孩子生下不久,就被寄养在邱县北部南辛店村的一户老乡家里。
三女儿宋适荒,被寄养在故城县一位老百姓家里,由于又饿又病,接回来没几天就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