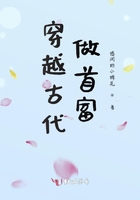永夜抛人何处去?绝来音。
香阁掩,眉敛,月将沉。争忍不相寻?
怨孤衾。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
——《诉衷情》
【壹】
黑色的轿车一路疾行,惹得行人纷纷避让。琴潋低头走着,似乎在想什么事情。等她察觉到身后有车,是因为一阵急促的刹车声,以及一只将她拉到路边的手。
“谢谢。”琴潋惊魂未定地向男子道谢。
他点点头,俯身拾起落在地上的书本,可书页已染上了点点水污。他把书递给琴潋,似是有些叹息,“字形雅致,字里行间又不缺风骨。真是可惜这些字了。”
“先生谬赞了。”琴潋刚合上书,险些撞了她的车子竟按起喇叭来,司机探出头喊了句,“还走不走了啊。”
男子回过头去,“你撞了人不道歉,还有理了?”
“理?这年头皇帝都两个了,谁还管理不理啊。”
琴潋拉了拉他的衣袖,“先生,算了。”男子却依旧站在车前。
“怎么回事啊。”车主人摇下车窗,才懒洋洋地问了一句,便立刻住了嘴。打开车门走了下来,对那男子点头哈腰地道,“不知是叶少,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叶熙川一挑眉,道:“不是我,你们就这样横行霸道了?”
“不是不是。”他边赔着礼,边对车里招了招手,“还不快出来给这位小姐道歉。”
过后叶熙川便离开了,琴潋回到戏院,在旁人的闲谈中终于明白过来,他们口中的叶少,说的便是苏州城里最负盛名的少将叶熙川。
他那么有名,倒不是兵法习的多好,而是因为他长着一张颠倒众生的脸。都说上过战场的人,见过枪林弹雨里的血腥气,身上总有股阴冷的意味,可叶熙川脸上始终是轻松戏谑的,眼神里又夹带着一丝穿透人心的光。被他望过一眼,便不知不觉就失了心。
琴潋也一样逃不过。
可她在那条长街来来回回走了许多次,都没能再遇上叶熙川。
【贰】
戏园子里响着锣鼓快板,台上演姬光的老生长须一捋,抑扬顿挫地唱着:“浣纱女心好善,一饭之恩前世缘。眼望吴城路不远,报仇心急马加鞭。”
谢缇听着拍手叫了声“好”,转而对坐在一侧的叶熙川道:“这姑娘可是宝庆班的台柱子,她唱老生啊,比男伶还厉害。”
叶熙川正抿了一口茶,“总听人说起她,”他缓缓地放下茶盏,“不过我看,那个弹琵琶的琴师才是真的有本事。她这一手琵琶,若是不用配合着唱词转,绝对是苏州城的一绝。”
谢缇向舞台右侧望了望,可他们的位置在二楼雅间,根本看不到琴师们的面目。谢缇便打趣了一句,“你这是打哪看的?”
“呵。用耳朵。”叶熙川笑了笑,“不过这姑娘倒真是难见一面。”
“难得有人能入了你叶少的眼,那散了场,可得找她出来见见。”谢缇笑道,“说起来,除了这老生,宝庆班里这弹琵琶的姑娘可是引了不少人欢喜。听说她模样一点不输人,琴也弹得是妙得很,若是肯出来唱个曲什么的,那肯定是红透苏州城啊。可惜人家清高,就爱躲在这帷幕后头,都不愿意出来见人。”
谢缇说完,叶熙川一旁的副官便插话道:“其实叶少早托人问了,那师傅果真傲气得很,说只弹琴不见人,要听曲,再加一出戏就是了。”
“那你一定是没告诉人家,是我们叶少请。”谢缇笑嘻嘻地看向叶熙川。
叶熙川不置可否,笑了一下,没接话。
她能在苏州城里红起来,还多亏了一位贵公子。
那时候他在园子里听了《玉簪记》里的一出,就听出后头弹琵琶的姑娘指法不凡,想邀她单独加个琵琶曲《汉宫秋月》。这上台唱戏的,但凡有些妙,都会有人捧,可这后头弹琴奏曲的,是千百年也出不了一个红的,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这小姑娘也不知道是倨傲呢还是害羞,回话说“没练过《汉宫秋月》,不会,公子若是喜欢,就再点一出《琴挑》吧。”
一句话,既没有回绝也没有答应,最后还是躲在幕布后面和唱陈妙常的旦角合了出暧昧无比的《琴挑》。
听说一曲将完时,那位公子还抢了巾生的词过来,跟着合了句“妙常,你一曲琴声,凄清风韵,怎叫人不断送青春。”
后来这句话传了开来,那凄清风韵的琴音也就红彻了苏州城。
叶熙川向来喜欢琵琶,有人请他谈事时,就想着请这个琴师过来弹一曲,却是怎么也请不动。
他听说了之后,想着人各有志,也就作罢,却终归是十分遗憾的。
两人叶熙川和谢缇一起用了晚餐,谢缇这次却破天荒得没有劝叶熙川喝酒。他便早早回了家,却见府宅门口停着辆车,司机正斜靠在车门边。见叶熙川来了,他赶紧站直了身子,“叶少。”
“什么事?”
“宝庆班那个琴师,谢司令替您请来了。”他说着开了车门,而搭着他的手下车的,正是琴潋。
可叶熙川像完全不认识她似的,兀自地笑了起来,“那也该是请姑娘吃个饭,哪有把人往家里请的道理。”
“谢司令已经替她从宝庆班赎了契,琴潋姑娘如今是您叶府的人了,您想听曲,就带姑娘回去听吧。”
琴潋福身做了个礼,低低地道:“见过叶少。”
叶熙川点了点头,“外头风大,赶紧进来吧。”
叶府还是旧式的园林,亭台水榭建的满目琳琅。叶熙川指了一处院落,让下人去收拾。又道今日太晚了,明天再带她认认园子。琴潋便随他进了他住的梯云楼,为他弹了一曲《汉宫秋月》琵琶。
果真如他所说的那般,没了要合的唱词,琴音便愈发灵动了。
可第二天一早,叶熙川什么也没说便急急地出了门。琴潋闲的无聊,就在园子里随处逛着。秋末的季节,本是枯了草木,园子四处倒都收拾得深浅有致,只有那离梯云楼几步之遥的涵碧山房,门上的铜锁都落了锈,外头还堆着一地的落叶,打扫的花匠似是故意避开了它一圈。
琴潋瞧着好奇,正要上前看看。“姑娘干什么呢?”厨娘远远地叫住了她。
琴潋缓了缓脚步,“没什么,随处看看。”
“姑娘还是上别的地方转悠去吧,”厨娘走了过来,似乎为着熟悉这个宅院而分外得意,“这涵碧山房可进不得。”
“为何?”
这一问正合了厨娘的心意,她故意扬了扬头,讳莫如深地道,“这你就别问了,哪个大户人家没点秘密呢。”
【叁】
琴潋看到面前的一大束玫瑰花时,一下子捂住了嘴。虽然知道表现的太惊吓会显得很没见识,她确实被这一大捧艳丽惊住了。不过叶熙川没给她惊讶的时间,就把花束递到了她手上。
“早上有事着急出去,看你还在睡就没告诉你。”叶熙川温和地解释道,“还住得惯吗?”
“挺好的。”琴潋低着头笑了笑。
“缺什么就让下人么去添上,不要不好意思。”叶熙川说着便很自然地拉过了琴潋,“走吧,吃饭去。”
晚餐准备的是西餐,整个餐厅就对面对坐了他们两个人,不过比起这个,琴潋看着面前的刀叉才更加不知所措。他们一坐下,厨师便端上了牛排,琴潋偷偷地瞄了一眼叶熙川,想学他的样子,拿起刀又觉得别扭的很。
叶熙川很快察觉了她的尴尬感慨,起身走到她身后,“这样,”他握着琴潋的手拿起刀叉,“拿这个摁住,然后拿这个切。”
“好……”琴潋应了一声,手里的动作却全由叶熙川带着,她只感到他温暖又厚实的手掌带着她一点一点地切下小块牛排,他说“就像拉胡琴一样,你学过胡琴吗?”
“学过几日,不过师傅说,女孩子还是学琵琶好。”
叶熙川点点头,道:“他说没错,刘铭传不也说‘琵琶音最好’吗?”
但是叶熙川到底是公务繁忙,早出晚归是常有的事。可这几日到处都太平的很,又没有仗打,不知道他们整天都在谈些什么。
“这么晚才回来,吃过饭了吗?”琴潋接过叶熙川递来的军大衣。
“没呢,刚才在同福里怀致他们家谈事情,楼下做菜可香了,我们都说去买桌饭菜来,吃完了再谈,谢缇偏要说我们扰民,让我们饿着,真是的。”叶熙川摇着头道。
“同福里啊。”琴潋想了想说,“我记得他们巷口那家馄饨铺子特别好吃,你没去吃真是可惜了。”
“是吗?”叶熙川停住了换鞋的动作,“那我们再过去吃啊。”他说着就披上了大衣,兴致勃勃地拉着琴潋出了门,随兴的样子一点也不像个带兵打仗的人。
可还没出门,便被管家拦了下来,“叶少,夜里露重,还是别出去了,姑娘想吃派人去买回来就是了。”
“那还有什么味道。”叶熙川说着就拒绝了他。
“可是待会……”
“回来再说。”叶熙川拉着琴潋,绕过了他。
老管家自叶熙川小时照顾他至今,甚至算得上当了父母的责任,平日里他要是劝句什么,叶熙川从来没有驳过他的面子。
为了琴潋,这是叶熙川第一次没理会老管家。
很多年以后,叶熙川再想起这一次的冲撞,才最终明白过来,原来早在这时候,他心里就已经做出了选择。
“你先把车开回去吧,我们等会走回来。”叶熙川交代了司机一句,就和琴潋下了车。
大冬天的,夜里果真冷得很。这个时间过去,铺子已经歇了业。叶熙川敲开了门,说是特意过来的,老板就答应给他们重新做两碗。
说着便切了料开始包馄饨,琴潋站在一边盯着看,跟老板唠起嗑来,“我一直不知道这种方形的馄饨是怎么包起来的,今天终于有机会看你包啦。”
“好好学学啊,”老板说着减慢了手中的速度,让琴潋看得更清楚些,“学会了就可以回家给你先生做啦。”
“啊?”琴潋听着愣了一下。叶熙川倒是很快接过话来,“她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哪里会做饭。”
“谁说我不会啊。”琴潋回过头去,“你敢吃我就敢做啊。”
【肆】
虽说叶熙川待琴潋极好,得了空便带她去听戏,或在府里对弈共饮。可一旦叶熙川不在,琴潋在府上总觉得尴尬。
叶府除了司机、厨娘,也就一个管家和几个杂役,统共没几个下人,更没有女主人。叶熙川是风流成名,身边名媛、歌女来回换,却也没见哪家小姐能和他定上亲,那一两个在外头置了院子的歌女,就是顶顶上脸的了。
这能进叶府门的,琴潋还是第一个。不过到底是谢缇的意思,而叶熙川把她接来的。他一直没提过琴潋算是姨太太还是丫鬟,下人们也就不咸不淡地喊她一声琴潋姑娘,丝毫没觉得她能成叶府女主人。
都说琴潋的琵琶是宝庆班的半根台柱子,以前在戏园子里众人也是给足她面子。虽说谢司令的话,这苏州城里没一个人敢不从,可这事到底是问过她的意思,是她自己点头应承下来的,如今落得这不明不白的境地,实在叫琴潋难受。
她总以为叶熙川是记着她,才托谢缇来宝庆班打听的,可不管她怎么旁敲侧击,叶熙川都说不记得见过她,只当她是谢缇送来的人。
那以后,琴潋也给叶熙川的画题过词,他却再没能夸她一句。她不得不觉得,叶熙川对她的宠爱,是碍着谢缇的面子,或只是因着她有几分姿色,才有的那肤浅的欢喜。
琴潋整日闷在屋里,东想西想的,总觉得叶熙川心里还有别的什么,她想着想着,便想到了涵碧山房。
叶熙川这些天不知忙些什么,整日把自己关在梯云楼,还关了院子的门,不叫人打搅。琴潋等了好些天,才等到他出门。她便一会嚷着要喝薏仁粥,一会要喝花茶,打发了厨娘和花匠,偷偷溜进了院子。
走近了才发现,那铜锁虽是多年未动的模样,其实根本没上锁,只是随便地插在门环上。琴潋赶紧拿下了铜锁,推开门。
里头种了梧桐,如今这季节,正好落了一地的叶,都抹过了脚踝。照理琴潋推门时,得一并把落叶从门后推开去,有几分吃力,她却没什么感觉,甚至那木门都没发出年久失修的“吱呀”声,院子和没人闯入时一般,静得诡异。
琴潋没顾念这么多,她踩着梧桐叶子进了门,四处一望才发现涵碧山房后头的石台正好对着院子里的水榭,这屋子该是叶府位置最好的了,却为何要闲置起来?
琴潋想着往山房走去,完全没注意自己脚下踩的落叶,在她进来之前,就已经被踏出了一条小径似的形状。
门上没有上锁,琴潋正要推开,却见铜门环闪着光,干净得很。琴潋有着诧异,又回头望了望,见院子里摆着的两张石凳,也是光滑的很。可地上的梧桐叶稀疏得堆着,除了她踩出的那道印子,并没有有人来过的迹象。
琴潋皱了皱眉,先推开了门。屋里和整个叶府都截然不同,一副西洋的做派。墙边立着架钢琴,桌上还摆着摞书,上头隔着钢笔。琴潋略一抬头,便瞧见了墙上挂着幅大照片。照片上的姑娘就立在院子里那棵梧桐树下,巧笑倩兮。
她就是涵碧山房的主人,也可能是叶府曾经的女主人。
琴潋不是没想过这种可能,但见到这个女子时,她着实有些惊讶。她总以为叶熙川还是喜欢古旧的东西的,这女子却穿着浅色的洋裙,斜戴着顶宽沿的帽子,笑得自信又爽朗。
琴潋看得出神,完全没注意到院子里已经进了人。她正有些失落地低下头,随手拿起桌上的书,翻了起来。
“你在找什么?”
听到问话,琴潋吓到一下子松了手,回头就见到了一脸冷峻叶熙川。
“我问你在找什么?”
“没……没什么……”琴潋赶紧俯身捡起了书。
“没人告诉你这里不许进来吗?”
“我就是好奇……”琴潋被他盯着的心里发毛,低着头就要出去,“我不再来就是了。”
叶熙川却站在门口,一点没有要让她的意思。
“我以为避了那个老生,总能落个清净,没想到你也是谢缇的人。”
“你在说什么……”
“难道不是吗?”叶熙川走上去,一把抽出了琴潋手中的书。
【伍】
叶熙川再没见过琴潋,下人们便也愈发冷淡了,像是因为猜准了琴潋不是个长久的人,更有了几分得意。往后的日子,叶熙川回府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晚。府里没人管琴潋,她便偷偷出了门,去宝庆班找人叙叙旧,她们一见琴潋却打趣道:“你怎么还有闲心出来玩?”
琴潋不解,便听她们说,“如今城里都在传谢司令嫌手下那些将领功高震主,前几日开酒宴,想学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结果那些人都不买账,谢司令出来的时候,脸都黑了。”
“谢司令和他们几个都是一同打天下的兄弟,这才进了苏州城多久,怎么就想着分权了?”琴潋问道。
“你也知道,现在北平乱得很,谢司令又和段总司令关系好,总想到北平分一杯羹。可南边也一样乱得很,不说远的滇系、桂系,就是隔壁的皖系,又有哪个不想自己做皇帝。那几位觉得要先安定周边,这关系不就僵了吗。”
琴潋听了忙笑道:“别乱嚼舌根了,被人听了去可不好。谢司令和几位将军关系那么好,就是有些分歧,也不至于闹上的。”
“也是。”马上有人应和了起来,“你每日见着叶少,自然最明白了。”
琴潋似是不经意地笑笑,一副对时局了如指掌的模样,可这宝庆班倒是去的更勤了。
叶熙川虽是懒得搭理她,琴潋也远远见着他好几回,来去匆匆,看起来恼的很。
直到有一天叶熙川喝得醉醺醺回来,管家喊她帮忙照料,琴潋才得了机会好好见见他。
都说当今这几个将领,就数叶熙川最有贵族气,从没失了风度。果然他如今醉的站都站不稳了,也只是由管家扶着走,不闹腾什么。琴潋让厨娘去做了醒酒汤,自己去打了水给他洗脸。管家一走,琴潋便没好气地瞪了叶熙川一眼,“如今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居然还喝成这样。”
没想叶熙川居然迷迷糊糊地回了一句,“不是有你吗?”
琴潋蓦地转头看他,见他半眯着眼躺在床上,分明是醉得不轻的模样,便又听他咕哝了一句,“还要别人做什么。”
原来他说的是“盯着”,琴潋苦苦一笑,替他擦了擦脸,“我又能盯着你什么。”
叶熙川似乎嫌水太凉,想打开琴潋的手,随便一挥刚好触到琴潋的手腕,他便顺势握住了琴潋的手,扣向床沿。喃喃地说着,“我就是什么也没有啊,不是说好一起打天下的吗,谁要来打你啊,自作多情。”
叶熙川说完竟然就睡了过去,没松手。
叶熙川第二天一醒来,刚见琴潋端了早餐进来。“我给你煮了馄饨,你尝尝看。”
叶熙川没应和,自顾自地问:“我昨天说什么了吗?”
琴潋边放盘子边道:“说谢司令自作多情。”
叶熙川有些尴尬,“我喝多了,这事就别告诉他了。”
“说什么呢,谢司令那样的大人物,我怎么够得上。难不成你以后去赴宴,愿意带上我?”
“行了,别装了。”叶熙川瞥了她一眼,“我这府里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你是谁的人又有什么关系。”
“可我谁的人都不是,我去涵碧山房只是想知道那个女人是谁,”琴潋咬着唇,“熙川,你心里的那个人,她到底什么样?”
“她呢,就是一个不会算计我,更不会算计了我还死不承认的人。”叶熙川披上外套,瞥了她一眼,“我出去了,你自己吃吧。”
【陆】
琴潋自知身份低微,便是进叶府做妾她也没什么怨言,心里却终归是希望叶熙川能有几分真心待她的。可她没想到,只是闯了一次涵碧山房,一切都变了。或是说,一切假象都被揭开了。叶熙川只当她是与谢缇周旋的一颗棋子,即便是一颗或许能反为他所用的棋子,她在叶熙川心里都及不上那一张照片。
而谢缇那边,原以为他只是不悦,提醒他们几句。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动了气,找了个由子,先办了平日里对他意见最大的一位叔伯。
那之后,叶熙川便再没出过府,琴潋在园子里,常听见外头有卫兵列队走过的声响,皮靴踢踏踢踏的。每当这声音响起,叶熙川都会停下手中的笔,朝院门那望一眼。
琴潋只能每日瞧着他那副样子,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等了几天,也没见动静,便打算偷溜去宝庆班打探打探。
琴潋走后门出去,才没几步,一只手便拍上了她的肩,吓得她差点叫起来。
叶熙川懒洋洋地道:“你一个做细作的,胆子这么小怎么行。”
琴潋本想辩驳一句的,想想也没什么意思。
“去找谢缇?”
琴潋瞥了叶熙川一眼,没说话。
“要和他说什么?”
琴潋没好气地道:“说我如今吃醋的紧,怪他拉错了红线。”
“琴潋。”叶熙川忽然很认真地喊了她一声,“我确实没这心思对付谢缇。如今哪里都乱,我们要是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就只能等着被别人一口吞了。”
“你们的国家大事,我可不明白。”
“这次如果能躲过去,你就是叶府的女主人。”叶熙川看着她,“我不会再娶。”
“说的好像你娶过我似的。”琴潋依旧是满不在乎的语气。
“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给你一个全苏州最盛大的婚礼。”
他说“如果你想要”,即便心知肚明这是交易,又为何一定要说得这么明白呢。明明是最想要听到的一句话,真的从他口中说出来,竟然这般滋味。在达官显贵眼里,她们这些戏子歌女,就是再心高气傲,想要的也不过是个名分。琴潋叹了口气,转身离开叶府。
叶熙川猜得没错,琴潋确实是谢缇的人。
虽说谢缇是最看中那个老生的,不过整个宝庆班,其实都是他的人。叶熙川也知道谢缇和他提老生是别有他意,就故意夸了琴潋。谢缇只能顺理成章地让琴潋进了叶府,他告诉琴潋一定要进涵碧山房里头看看。
其实那铜锁、石凳足够琴潋明白,是有人常翻墙进来,然后踩着石凳进了屋子,就不会留下脚印。她虽是没去在意,不过经过多年的训练,这些细节她一眼望过去就明白了。可她就是当作没看见,只告诉谢缇那是个姑娘的房间,叶熙川看起来珍视的很。谢缇问她叶熙川是不是经常去,她也只道那铜锁是虚的,或许是经常吧。
一个人经常去,和一群人经常聚,那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谢缇问她:“叶熙川最近在忙什么?”
“关在房里,练字、作画。”
“没了?”谢缇看了她一眼,“涵碧山房里找到东西了吗?”
“没有。”琴潋道,“叶少那样的人,看着就是喜欢安逸日子的,司令大可放心。”
“没错。”谢缇点着头,却忽然冷冷地道,“我也没指望你能从他身上找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秘密,却没想到你那么不成器,还口口声声地帮起他来。”
琴潋冷静地接道:“叶少确实没什么可疑的,他那天喝醉了还说‘不是说好一起打天下的吗,谁要打你,自作多情’。”
“他有没有醉,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琴潋低着头没说话,她自然是看得出来的,叶熙川脸色好得很,一点也不像喝多了的模样。千方百计地装醉就是想告诉她,他没打算反谢缇,让琴潋好把这话告诉谢缇,免得他疑心。
谢缇的脸冷了下来,“你要搞清楚,替我办事,以后有的是荣华富贵,可你要是跟了他,他败了你就是死,他要是赢了,也不会感激你什么。琴潋,这世上,最不值得的事情,就是情爱。”
琴潋只是不动声色地回答,“跟着叶少,不就是跟着司令吗?”
【柒】
琴潋回了叶府,也没和叶熙川多说什么,反正他也是整日整日的忙,都不见人影。
那天厨娘做了青团,趁热就拿到琴潋房里来了,琴潋看到她就问了句:“我包的馄饨,你煮给叶少吃了吗?”
“煮了,叶少没吃,看了一眼就出门了,说他不爱吃这些路边摊的东西,让我以后别做了。”她说完就拿着木案出去了。
琴潋那颗随着书本一起落下的心,好像一瞬就回到了原来的地方,死寂死寂地躺着,一点声响都没有了。
直到那天一早,琴潋听见叶熙川出门的动静,不知怎么的就心慌起来,她跑出去问叶熙川要去干吗。他只说是公事,就打发了他。
可那天叶熙川没有回来。
来的是一队包围了叶府的士兵,直到晚上换了一批人,琴潋才听说是几个将领拿枪进了宅子,要逼谢缇撇清和北边的关系。他们说谢缇早就知道了这些人的计划,柜子里都躲着卫兵,一齐开枪结果了那几个将领。可谢缇早先不确定究竟是谁要反他,便让人把所有将领的宅子都围了起来。
他们大抵是想着,以叶少和谢缇的交情,必然不会参与其中,也就不忌讳告诉琴潋。可琴潋一听到这些,心便沉了下去。
她果真再也没能见到叶熙川,再见到的,只有谢缇。
“他死了。”谢缇把一叠信件扔给琴潋,上头全是叶熙川的字迹,是他寄出的信件。“他收到的那些,应该都藏在涵碧山房。”
琴潋看着那些字,没说话。她早就知道叶熙川要反,涵碧山房那本书里就夹着他收到的信。琴潋看见了,所以无论她怎么辩驳、怎么装傻,叶熙川都不会再信她,不会再给她哪怕一点儿一点儿的爱情。
可她那天确实想去是宝庆班,但是叶熙川一句话,她便来谢宅做了伪证。明知道他就是利用,明明心里恨的很、不甘的很,终归还是要帮他。
可谢缇对叶熙川,早不仅仅是怀疑了。他抓的其他人,供出了这些信和涵碧山房,琴潋还依然信誓旦旦地证明着叶熙川的清白。
谢缇的枪已经顶在了她的脑袋上,“背叛我是什么下场,你很明白。”
她终是明了了叶熙川对她说那些话的缘由。不是为了向谢缇澄清自己,而是让琴潋出面,让谢缇消除几分戒心,他想要的,不过是谢缇那一两日的不注意。
可谢缇毕竟是谢缇。
他说的很对,叶熙川败了,她就是死,叶熙川赢了,她连利用的价值都没有了。
从她爱上叶熙川的那一刻起,她便已经走上了死路。
谢缇瞧着琴潋这副绝望透顶的模样,反而露出满意的表情来,“你们这几个人啊,总让我花那么多心思教。”他说着收起了枪,“明白了的话,过几天有新的任务给你。”
【捌】
几日后谢缇设了宴,想为前日的事扫清阴霾,琴潋在席间弹了一首古琴。而后便被谢缇冠以新的名字与身份,送给了新的人。
那个人叫怀致,他年纪比谢缇和叶熙川都小,留过洋,曾是谢缇最信任的军师。可如今,谢缇对谁都不放心了。
怀致没那么老成,口无遮拦地就对谢缇说:“可我不喜欢听古琴,我喜欢琵琶。刘铭传不是说琵琶音才最好嘛。”
琴潋笑着接过话来,“可刘铭传也说了,‘琵琶音最好,解说别离难。多山伤情事,曲终和泪弹’。说明这琵琶啊,太凄苦了。可古琴多好啊,高山流水,永不止息。您说是不是?”
怀致喜欢读书,比起那些将领来,单纯得很。琴潋也不愿寻他的错处,也偶尔帮衬几句,却终归没了对叶熙川时的那份维护。
可她怎么也没想到,竟然在怀致的书房看到了和涵碧山房里一模一样的照片,“这是谁?”琴潋问。
“哦,熙音啊。”怀致抬头看了一眼,“叶熙音,她是叶少的妹妹。”
“叶少还有妹妹?”
“是啊。”怀致应了一声,“不过她已经不在了。”
“是因为前些日子的事吗?”琴潋故意问。
“不是。是当年一次晚宴,叶少带了熙音去,”怀致说着叹了口气,“结果被紫禁城里那一位看上了,那时候谢司令也不过是少将,别说是叶少了,就是他自己的亲妹妹也一样得送过去。”
“那一位,不是很快就倒了台吗?”
“是啊,谢司令也终于拿下了苏州城,算是盘踞了一方。叶少就想去北平接熙音回来,可谢司令不同意。”
“为什么?”
“那时候局势那么乱,大家都赶着去北平分一杯羹,谢司令是支持段总司令的,自然不会让自己的人再进北平去凑热闹。”
“可叶少又不是去……”
“这世上拿来做幌子的事情多了,很多真事就会被人当作幌子。”怀致道,“总之那段时间,他们闹得很凶,谢缇还封了火车站,就是不让叶少出城。叶少没办法,就托北边的朋友有机会把熙音带回来,可回过来的电报说,熙音自尽了。”
“啧。”琴潋忍不住叹了一声。
“那天叶少闯进谢宅,都拿枪指着谢司令了,后来也不知是顾全大局,还是顾念多年同生共死的情分,终归是没开枪。司令也不计较,两人的关系看起来还和以前一样,其实心里面都变了。”
“所以叶少这些年,一直是存了心思要报仇的吧。”
这事叶熙川明白,谢缇也明白,而她琴潋,便是这棋局里,多出来的那一个卒。
“怀致,帮我去街口叫碗馄饨吧,我饿了。”
“过去吃不行吗,总叫人送来,多不好意思啊。”
“我懒嘛。”琴潋笑笑,把学过的那些妩媚全都融进了眼角。
【玖】
北平的戏园子里,正热热闹闹地演着《鱼肠剑》。伙计端着茶水一路穿过大堂的座,“让一让啊”。
“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坐过这样的位置。”坐在其中的少年忍不住抱怨起来。
“我如今是个无名无姓的人,能有闲钱听个戏就不错了。”答着话的人一身粗布长衫,面目却令人过目不忘的清俊,分明就是叶熙川。
“爷,你当真不回去了?”
“回去做什么?”
“等了这么久,终于部署周全了,事到临头怎么就放弃了呢?”
叶熙川淡淡地道:“我就是真杀了他,熙音也回不来,何必再赔上琴潋的性命。”
“爷,你心里头是有琴潋姑娘的吧,我跟了你这么多年,都没听你夸过谁一句。见到琴潋姑娘,又夸她字写得好,又夸她琴弹得好。”
叶熙川依旧是那副勾人心魄的笑,不说话。
他怎么会不记得她。
那个传闻中点不上一曲《汉宫秋月》,只能合了一声“你一曲琴声,凄清风韵,怎叫人不断送青春”的公子,就是他。
那时候,他就已经对琴潋的琵琶着迷了。
堂堂的叶少,居然也做出了偷偷到戏院后门等着琴师出来的事,一路小心翼翼地尾随,想近近地看一眼她的样貌,又怕唐突了人家。最后,还是那辆飞驰的轿车给了他机会。
以至于当时谢缇问“你这是打哪看的?”时,他慌神得差点露了馅。
他是记得琴潋的,可他并不知道她是宝庆班琴师。而后琴潋阴差阳错的地进了府,他心里自然是欢喜的,却没想到头来她也是谢缇的人。
他看得出她和所有卖艺为生的女子一般,想要摆脱贱籍,想要脱胎换骨。她不似她们谄媚,却也步步为营地故作清高,想换上一个名正言顺。
他明白她微薄的心愿,可是他给不了。为了和谢缇周旋,他只能像宠一个歌女一般要宠她,却不能给她夫人的名分,又不能显得太在乎她。
他这般周全地待她,到头来,她竟然还是谢缇派过来的人。在涵碧山房里看到琴潋的叶熙川,那么那么的失望,却还是狠不下心来毁了她。
于是他就劝琴潋去谢宅,若是除去了谢缇的疑虑便正好,若是没有,也让谢缇知道他只是在利用琴潋。最后,还是留了一条活路给她。
他以为自己演得很好,可最懂他的人竟还是谢缇。
那天早上琴潋来拦他的时候,他犹豫过,可在谢宅的内应说谢缇这天没什么异常。他便依计划去了。进了谢宅,果然谢缇没有防备。
可他的枪指着谢缇时,他这过命的兄弟只是冷冷地嘲讽他,为了一个女人要杀兄弟也就罢了,还要一个女人给他当挡箭牌,他说叶熙川啊,你这辈子就是毁在女人上,哪怕今天杀了我,你的江山也坐不长。
谢缇说谢宅确实没有防备,因为他的人已经包围了叶府,他说你一开枪,琴潋面前那把也一样。
有那么一会,叶熙川没有动作,他觉得一个琴潋是比不上给熙音报仇的,可扣动扳机的瞬间,他还是放弃了。
他以为自己把这段感情掌控的游刃有余,可最后,终究是舍不得。
也或许,在那个本该议事的晚上,他抛下一大屋子人,陪琴潋去吃了馄饨,就已经在复仇和她之间,选择了后者。
叶熙川觉得,这之后,谢缇反而会更信任琴潋了吧。因为再好的训练,都及不上一个死了心的女人。琴潋那么聪明,自己一个人,总能好好活下去的。
他便答应了谢缇离开苏州,从此再不做叶熙川。
走的时候谢缇请他一起喝杯酒,说想起他们当年打算一起打天下的时候,也没什么契约凭据,喝了一杯酒,就成了生死之交。总以为不是一同风光富贵、潇潇洒洒地活,就是一同死在战场上、马革裹尸地还,却没想到,就这么寡淡地各安天命了。
台上演姬光的老生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一事无成两鬓斑,叹光阴一去不回还。日月轮流催晓箭,青山绿水长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