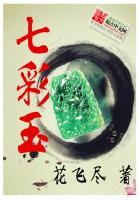所以,一直以来,我本能地想要避开这个人,但是现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可能是心里太急,我们每个人都显得有些暴躁,还没等我将心底的想法说出来,一场有针对性的争吵就已经爆发了。
第一个挑起事端的人居然是鸭子。一直以来,他和何勇的关系最好,同样与何勇说话态度最随意的也是他:“勇鸡巴,你搞什么麻皮?一天到晚只晓得打打打,打出这么些事来,拉屎了又擦不干净。老子看你现在怎么搞。”
委靡不振地瘫在凳子上的何勇瞟了鸭子一眼,嘴巴张了一张,却没有说话,刚抬起的头立刻又低了下去。
“勇哥,鸭子也说得对唦。我们和八宝的事还没有了难,又出了这么件事,哎,真是越冷越吹风。”当北条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空气中几丝微妙的味道。要知道,北条以前绝对不会在我的面前说何勇半个不字,哪怕些微的质疑都不曾提出。
当然,现在他说出这些话主要是因为心里着急,并不是真的要怎么样,但是不管如何,起码证明他的潜意识中不再视何勇为不可侵犯的对象,也不再视我为外人。
何勇还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先发言的鸭子反倒是有些不爽了,将手里的半截烟灰一弹,转过头来看着北条说:“哎,我说北条,你就他妈的有意思啦?看着我说了一句,你也跟着来神(方言,凑热闹,耍脾气)了是吧?你还好意思说八宝,八宝的事,是为了哪个?姚义杰被你害成这样,你还在这里啰里啰唆。”
北条脸色一变。
“哎呀,莫吵,莫吵,个人屋里几兄弟,吵什么吵?而今我们是商量怎么搞钱,吵翻天哒有个屁用啊。这件事,勇哥也是为了帮铁明唦。未必真的不想他好啊?”
在我们兄弟里面,夏冬是后来加入的,也是个子最小、最沉默寡言的一个。一直以来,他都不能算是受到大家重视的一位。可是,那次在彤阳义薄云天地救我之后,这种情况被改变了,我们发现了他值得尊敬的一面。无形中,我们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分量。所以,在他的话出口之后,鸭子与北条稍稍争辩几句,也就停了下来。但是,我的心底也感到了一丝别扭,我意识到自己好像有些不太喜欢这样的情况发生。
何勇的头还是低着,但是胸膛起伏得越来越明显。所有人都陷入了尴尬的沉默当中。猛然,他一把推开面前的茶几,站了起来,也不看任何人,径直就向门外走去,边走边说:“铁明这件事是我害的,也不再害其他人哒。这笔钱我们哪一个都拿不出来。不要再七想八想。这件事,铁明没得错,是被那个杂种冤枉。他没得办法,老子一个跑社会打流的,屁都不是!下一次老子还是要这么搞。老子个人来帮铁明摆平,不关你们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明白何勇发火了,也当然能够想通他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很简单,只有两个字:砍人!
顿时之间,所有人都被何勇的举动吓得呆在了原地,尤其是北条与鸭子两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我明白,我的机会到了。
我快步上前,一把抓住何勇的肩膀,看着他说:“何勇,你是不是觉得屋里面只有你可以提得起刀?你还想要拉几个人一路去坐牢?要担,老子陪你一路担!”
当初,因为何勇无心的这句话,我坐了牢,这已经成了他心里一道抹不去的印记。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我将这句话还给了他,他承受不住,只能愧疚。
故意咳嗽了一声,待众人都看向我之后,我的语调变得轻柔,说:“你们先莫急,其他的钱我试一下,想下办法,可能弄得来。你们就在这里等我,我等下去一趟市里。”
“你想什么办法?市里可以捡钱啊?”何勇的口气还是不怎么好,但是对话本身就已经代表着一种妥协,这就够了。拍了拍他的肩膀,我非常轻松地说道:“我坐牢的时候,认得一个朋友,关系蛮好的,在市里混得也相当不错。”
出来之后,我没有与里面的朋友联系过,也很少提起自己坐牢的事情。首先,这件事让我觉得非常羞耻。而大家也应该了解我的想法,一直以来,谁也没有问过;其次,我并不想将海燕的事情说给别人,也不想让其他人认识海燕。这种想法很荒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就是我自己内心的直觉。我只是选择了跟着感觉走。所以,第一次听到我在牢里还认识了一个市内的大哥,每个人都感到有些惊奇,纷纷抬起了头,默默地看着我。
我知道他们需要我的解释,可是我一点都不想多说,只得装作没有看到大家的表情一般,拉着何勇又走了回来,若无其事地继续说道:“他比我出来得早,三四个月前就出来了,而今跟着一个老板做事。我们那个时候关系还不错,我去找他帮我想想办法,应该没得蛮大问题。”
何勇显然没有注意到我的刻意回避,他叹了口气,也不看我,自顾自地说:“借得到吗?”
“试一下,应该可以。”
“算哒,义杰,还是莫去了。”
“……”
何勇的眼神有些复杂,说话的口气中也隐隐有着一丝恼怒急切,我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一时无法回答,默默地看着他。
“两三千块不是一笔买几包烟、搞几口槟榔的小钱,别个一世也搞不到这么多工资。哪个会随便借给你?如果关系真的这么好,为什么出来这么久也没有看见你们联系?义杰,算哒,莫去哒。不丢这个人。”
我终于明白了何勇的意思。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鲁莽而起,所以,比起其他人,他心里面更为愧疚,也更加着急,但是他不愿意牵连到我,不愿意我遇到被拒绝的尴尬与丢人。
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温暖。那一刻,我几乎都要脱口而出地告诉他们,我和海燕之间的关系,但是不知为何,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另外一句:“你们都莫管那么多,等着我就是了。我晚上回来,记着等我啊。”
将何勇按回到了座位上,轻轻地拍了一拍他的肩膀,我转身向着门外走去。背后,没有挽留,没有阻拦,每个人都定定地坐在原位,鸦雀无声。
出门那一刻,我毫无保留地露出了自己的笑容。
因为,我确实很喜欢这种一锤定音的感觉,而就在不久之前,同样在这些人里面,享受这个权利的还不是我。
天马行空的何勇
找海燕借钱,本来应该没有太多的问题。
可惜只是没有太多问题,而不是完全没有问题。问题不多,只有一个:那个年代,没有手机。
我无法得知海燕现在所处的位置,海燕也同样不晓得我要来找他。所以,当我坐了两个多小时的班车,从九镇赶到市内,再转公共汽车,一路寻找,来到海燕当初告诉我的那个家庭地址的时候,他却并不在家。开门的是一个老头,他穿着一身洗得有些发白却依然整齐的深蓝色中山装,他是海燕的父亲。
当听说我是来找他儿子的时候,这位老人脸上并没有表露出礼貌的表情,甚至都没有让我进屋。他只是一手扶在墙上,一手扶住门,上上下下如同看贼般打量了我半天,说:“不在屋里。”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不晓得。”
“那你晓不晓得,我到哪里去找他?”
“不晓得,不晓得。你们天天和他在一起玩,你都不晓得,我怎么晓得?”
“哦,那好。搭帮你哒!”
老人点了点头,“呯”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城市太大,我也不太熟,没有其他的选择,只能守株待兔,等在海燕家门口,期待他回家的时候,我能遇见他。
从下午三点多开始等,站累了,就在路边一个花坛上坐一下;坐累了就四周走两步,却还不敢走得太远。一包烟都快要抽完,抽得嘴里又苦又涩,几乎没了感觉,我还是没有看到海燕。
无数次,我都起身想要走,却又不甘心,害怕自己刚走,海燕就会回来。
于是,一等再等,前前后后等了大约五个小时,看着人们归家,看着人们做饭,再看着人们家里的电视响起。直到天色全黑,我才完全说服自己,等不到了,海燕今天不会回来。
海燕确实不会回来了。因为就在我百般不愿千种不舍地离开他家时,他却在千里之外的广东陆丰。前一天,他就跟着他的大哥,一个叫做廖光惠的人到那里进货去了。
命运就在这里错开。如果我能够提前一天来,或者海燕能够晚一天走。那么后面的许多事情就不会发生。我们几兄弟也就不会卷入到日后那场九死一生,涉及我市江湖顶级大哥位置之争的巨大漩涡当中。
21世纪的现在,交通非常发达,通往各市区、乡镇的班车,巴士不说是通宵达旦地营业,至少也会工作到很晚。就算没有班车了,还能打的,但是那个年代和现在完全不同。
20年前,公共交通虽然刚刚开放了私营,也仅仅只是小猫两三只。大部分的车都还是属于国营单位,司机们都拿工资吃饭,规定了六点下班那就是六点下班,晚一分钟也不干。
所以,当我走到我市专门停放通往九镇方向班车的城北汽车站时,看见的只是一个黑灯瞎火的停车坪,连根人毛都没有。
我又恨又急,彻底崩溃。恨自己为什么那么傻逼,一整个下午居然一点都没有想到过坐车的时间问题。
我实在是太了解何勇这个畜生了。所以事先我就再三交代今天晚上一定要等我回来,到时候再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确实没有借到钱,再想其他的办法。但是现在我回不去了,市内离九镇有六七十公里路程,不可能步行回去。那么等了一天,心急火燎的何勇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呢?
无论多么着急,我也没有任何办法,只得在车站旁找了间小旅社睡下。一整晚,我都在祈望菩萨保佑,在赶上明天五点最早一班车回去之前,莫要发生什么大事。
好不容易熬到天色发白,我赶紧起床,坐上了五点钟的头班车往九镇赶,下车就直接去了何勇家,没有找到人。意识到大事不好的我一家家地去找,直到敲开夏冬家的门,看见了横七竖八、埋头酣睡的他们,这才放下心来。
不过,我的心情并没有轻松太长时间。片刻之后,当何勇睡眼惺忪却面带兴奋地将几沓面额不同的钞票摆在茶几上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昨晚一定发生了某件超乎我想象的事情。
果然,接下来他告诉了我一个让我瞠目结舌、冷汗直流的故事。虽然,何勇与我有着共同的成长经历,彼此之间还亲密到形影不离,但我们绝对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刚开始认识何勇的时候,他洪亮而中气十足的嗓门,大开大合的手势,虎头虎脑的外表,不计后果的做事风格,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我认为他仅仅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粗野匹夫。
但他不是,绝对不是!
2004年还是2005年的时候,一位和我关系匪浅的已经退出江湖的大哥在喝得有些醉意之后和我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呵呵,义色,我不怕哪个,但是我不想惹的人有,不太多,你算一个。”
“哈哈哈,大哥,你就喜欢开玩笑。我算什么?你莫说这些。”
“还有一个是廖光惠。”
“哦,我就猜到有他。何勇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