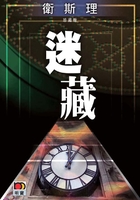九月份,树叶开始掉落,营地迁到更高的山上,躲在针叶树林的遮蔽之下。到了十月份,夜间变得寒气逼人,但打猎还是很容易,矮种马吃完最后一批草料,然后才会转去吃地衣、苔藓和树皮。罗斯巴德已经像周围的矮种马那样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克雷格时常下山去草原,带回一袋新鲜的青草,用猎刀切细了喂它吃。
假如轻风有母亲,那么她也许会与高麋商量此事,但问题是,她没有母亲,所以当她最终亲自去告诉父亲时,他顿时勃然大怒。
她怎么能去想这种事情?白人摧毁了她的家庭。这个人将会回到他自己人那边去,而她在那里不会有容身之地。更何况,在小大角河畔肩部中弹的那位印第安战士,现在差不多已经痊愈。断裂的肩骨终于接合了,不是局部,而是完全愈合。他是“走鹰”,也是一位优秀而又勇敢的战士。他将成为她的未婚夫。这事第二天就要宣布。就这么办。
高麋心绪不宁。很可能那个白人也是如此。从现在起,必须不分日夜地监视他。他不能回到白人那里去;他知道他们扎营的地方。他要留在这里过冬,但得有人看管着。就这样。
克雷格突然被安排住到了另一户家庭的帐篷里。有另外三名战士与他合住同一间屋子,他们警惕地注视着他在夜间的一举一动。
十月底的时候,轻风来找他了。他睁着眼睛躺在帐篷里,心中正思念着她。这时候,一把刀子缓慢而悄无声息地划破了圆锥形帐篷的一边。他轻手轻脚地爬起来,钻出破洞。她站在月光下迎视他。他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炽热的爱在他们之间流动。
她挣脱开来,后退一步并招了招手。他跟了上去,一起穿过树林来到营地视野以外的一个地方。罗斯巴德已被挂上马鞍,一件野牛皮睡袍卷好了放在马鞍后面。他的步枪挂在马肩上的一只长筒枪套里。鞍袋里装满了食物和弹药。一匹白斑色矮种马也已经配上缰绳。他转过身来,和她吻在一起。寒冷的夜晚似乎在他周围旋转。她在他耳边轻声说:“带我去你的山里,本·克雷格,让我成为你的女人。”
“现在,直到永远,轻风。”
他们跨上马轻轻地穿越树林来到一片开阔平地,然后一路下坡经过孤山,朝着平原疾驰而去。日出时,他们回到了山脚下。黎明时,一小队克劳人远远地看见他们,然后转向北方,沿着博兹曼小道朝埃利斯堡前行。
夏延人来追他们了;一共六个人,速度很快。他们轻装出发,肩上斜挂着步枪,腰里插着斧子,屁股下垫着手工编织的毯子。他们接到的命令是,走鹰的未婚妻要活着带回来,那个白人则应该去死。
克劳人小分队朝北骑行,走得很艰苦。其中一人夏天时在军队里当过侦察兵,知道蓝军部队已经贴出布告,重金悬赏捉拿那个白人叛徒,赏金多得足以购买许多马匹和物品。
他们最终没有去博兹曼小道。在黄石河以南二十英里处,他们遇上了由一个中尉带领的巡逻小队,一共有十个人。克劳人解释了他们所看到的情形,他们基本是在用手势比划,但中尉能明白。他让巡逻队去南面的山区,要克劳人充当向导,在前面探路。
那年夏天,卡斯特及其部下遭屠杀的消息如同冷空气般横扫美国。在遥远的东部,国家领导人于一八七六年七月四日在费城聚集,庆祝一百周年国庆。来自西部边疆的那条消息令人难以置信。当局下令要立即展开调查。
那次战斗之后,特里将军的士兵们已经清理了那片不祥的山坡,期望能找到对这场灾难的解释。苏人和夏延人已于二十四小时之前离去,特里也没有心思追击。雷诺少校的残余部队已被解救出来,但除了当时看着卡斯特率领官兵骑马走出视线进入山丘后面以外,他们什么也不知道。
在山坡上,每一片证据都被收集并保存了起来,正在腐败的尸体要赶快掩埋。在收集到的物品中,有夹在草丛中的几张纸片,其中有库克上尉所作的笔录。
当时站在卡斯特身后参与审问本·克雷格的官兵们,没有一个活下来,但上尉副官所记录的内容足以说明一切。对于这场灾难,军队需要一个理由。现在他们有了一个:那些野蛮人预先得到了警告,并已做好准备。毫不知情的卡斯特中了大埋伏。而且,军方有了一个替罪羊。经验不足不能作为理由被接受,但背叛可以。悬赏一千美元捉拿侦察兵克雷格的布告贴出来了,不论死活。
叛徒克雷格已失去踪迹多时,直到这一小队克劳人看见了这个逃亡者,后面还跟着一个印第安姑娘,两人在十月最后那几天里骑马跑出了普赖尔山区。
中尉部下的马匹在夜里休息过,而且已经吃饱喝足,现在它们精神饱满。于是,他率领战士们骑上马朝南方奔去。他的职业生涯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
日出后不久,克雷格和轻风抵达了普赖尔山口,这是夹在主山脉和西普赖尔峰之间的一道低矮的隘口。他们越过隘口,策马慢跑穿过西普赖尔山脚来到荒野之中。崎岖的山区里都是长满荒草的山脊和隘谷,向西绵延达五十英里。
克雷格不需要太阳来指引方向。在清冷蔚蓝的天空中,他能够看到远处的目标在早晨的阳光下熠熠发亮。他正在朝阿博萨洛卡荒原行进,那是他孩提时与老唐纳森一起打猎的地方。那个地方很荒凉,只有一片荒芜的森林和岩石裸露的高原,很少有人能追来,而且,从那里可上行通往熊牙山脉。
即使相隔那么远,他也能看到山上的几座雪峰——雷山、圣山、药山和熊牙山。在那里,一个人只要有一支上好的步枪就能抵挡一整支军队。他稍作逗留,让浑身冒汗的坐骑喝上几口水,然后继续向着仿佛把大地与天空连接起来的那些山峰进发。
在他身后二十英里处,六个印第安战士边仔细察看地上留下的马蹄铁痕迹,边策马飞驰,这样既能节省矮种马的体力,又能长时间奔跑。
北面三十英里处,骑兵巡逻队正南下寻找踪迹。他们于中午时分在西普赖尔峰以西处找到了。几个克劳人侦察兵突然勒住缰绳让马绕起圈来,他们双眼盯着被太阳晒干了的一块土地,朝下指了指那些铁蹄印迹,以及紧跟在后面的未钉铁掌的一匹矮种马的踪迹。
“嗯。”中尉轻声说,“我们有了竞争对手。没关系。”
尽管马匹已经有点疲倦,他仍下令继续西行。半个小时后,他爬到平原的一个高坡上,取出望远镜观察前方地平线上的动静。逃亡者倒是没看到,但他见到了一丛飞扬的尘土,下面是六个微小的人影骑坐在白斑色矮种马上,向着山区快步跑去。
夏延人的矮种马也累了,但他们知道,前方逃亡者的坐骑肯定也一样。战士们在布里吉村下方的布里吉溪旁让马匹喝水并休息了半个小时。一位战士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到后面传来一阵马蹄声,于是他们上马继续前进。一英里之后,他们的领头人拐到一边,把他们带到一个小山包后面躲起来,然后爬到山顶瞭望。
他看到了三英里之外的骑兵队。夏延人不知道山坡上的什么记录纸,也不知道对那个流亡白人的悬赏。他们认为,肯定是因为他们逃出保留地,那些蓝军官兵才会追来。因此他们一边观察一边等待。
骑兵巡逻队在抵达土路的分岔点时停了下来,克劳人侦察兵下马察看地面。夏延人看到克劳人一直在指西方,骑兵巡逻队也继续朝那个方向跑去。
夏延人与他们齐头并进,保持平行,如同小狼当时尾随卡斯特沿罗斯巴德河北上那样尾随着这些蓝军战士。但在下午三四点钟时,克劳人发现了他们。
“夏延人。”克劳人侦察兵说。中尉耸耸肩。
“没关系,让他们打猎去。我们有我们的猎物。”
两路追捕者持续行进,直至夜幕降临。克劳人跟随那些踪迹,夏延人尾随巡逻兵。当太阳落到山峰后面,两路人都意识到,他们得让马匹休息了。如果他们非要接着往前走,身下的坐骑会累垮的。此外,地面变得越来越崎岖不平,追踪也变得越来越困难。他们没有带马灯,在黑暗中,没有马灯根本不可能赶路。
在他们前方十英里处,克雷格也明白这一点。罗斯巴德是一匹高大、强壮的母马,但它已经载着装备和一个人在高低不平的路面上跑了五十英里。轻风不是一个熟练的骑手,她也已经疲惫不堪。他们在雷德洛治镇东边不远的熊溪旁扎了营,但不敢点火,唯恐被发现。
夜幕来临后,气温急剧下降。他们蜷缩在那件野牛皮睡袍里,轻风姑娘很快就睡着了。克雷格没有睡觉,他可以之后再睡。他钻出睡袍,把自己裹在一条红色的手工编织毯里,注视着他钟爱的姑娘。
没有人来,但他在黎明前就起来了。他们拿出风干的羚羊肉,和她从自己的圆锥形帐篷里带出来的玉米面包,和着溪水匆匆咽下,然后便离开了。当第一道曙光照下,小径显露出轮廓的时候,追捕者也起来了。他们落后了九英里,但正在逼近。克雷格知道夏延人会追来;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可饶恕的。但他对骑兵追捕队则一无所知。
地面更崎岖了,前进的速度也更慢了。他知道追捕者会追上来,他需要布下假的踪迹来拖延他们的时间。在马背上骑行两小时之后,逃亡者来到了两条溪水的交汇处。左手边从山上翻滚流淌下来的是罗克溪,根据他的判断,这条路无法通到荒野。正前方的是西溪,水更浅,石头也更少。他跳下马,把矮种马的缰绳拴到他自己马匹的鞍子上,然后牵着罗斯巴德的马勒在前方领路。
他带领这支小小的马队以一个朝向罗克溪的角度离开岸边,进入水中,然后折回来走另一条水路。他的双脚被冰冷的溪水冻麻了,但他踩着溪底的砾石和卵石坚持行走了两英里。接着他转向左边的山区,牵引着坐骑走出溪流,进入到一片浓密的森林里。
在此地,树林底下的土地变得陡峭起来,太阳也被遮住了,树林里阴森森的。轻风用毯子裹住身体,骑在矮种马的光背上以步行的速度前进。
在后方三英里处,骑兵巡逻队抵达水边停了下来。克劳人指的方向似乎是朝罗克溪而去。中尉在与中士商议以后,命令巡逻队朝那条假踪迹追去。当他们消失之后,夏延人来到了两溪会合处。他们无需踏入溪水来掩盖足迹,但他们选择了正确的溪流,快马加鞭上了岸,打量着远处马儿出水的痕迹,朝着上山的方向进发了。
两英里之后,他们发现了溪水对面一块软土上的痕迹。他们骑着马大步踏过溪流,进入到那片山林之中。
中午时分,克雷格抵达了记忆中多年以前打猎时经过的地方。那是一个很大的岩石高原,叫银径高原,可以直接通往山区。他和轻风不知道的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来到海拔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山上了。
站在岩石边缘俯视,能看见他曾经沿着走来而后又离开的那条溪水。在他的右边,下方有人影。那是两条溪流的分岔处。他没有望远镜,但因为空气很稀薄,能见度特别好。半英里之外的那些人不是夏延人,而是十名士兵,还有四个克劳人侦察兵。他们这路巡逻队在发现自己走错路之后,从下面的罗克溪折返了回来。这个时候,本·克雷格方才明白,因为他放走了那个姑娘,部队仍在追捕他。
他从皮套里取出那支夏普斯步枪,塞进一颗子弹,找到一块可以卧倒的岩石,举枪瞄向下面的山谷。
“干掉马。”老唐纳森以前总是这么告诫,“在这种地方,一个人失去坐骑的话,只能掉头回去。”
他瞄准了军官坐骑的前额。子弹射击时发出一声爆响,声音如雷声般在山峦间回荡许久。子弹擦过马的脑袋,射中右肩上部。战马颓然倒地,军官也跟着跌倒了。中尉倒下去时,扭伤了一只脚踝。
骑兵们四散逃入林中,但中士没有逃跑,他冲向身后倒在地上的战马,试图去帮助中尉。那匹马已经受了致命伤,但还没死。中士用手枪了结了它的痛苦,然后把中尉拖进树林里。枪声没有再次响起。
夏延人在山坡上的树林里下了马,停留在落满松针的土地上。他们之中,有四个人带着从七团缴获的斯普林菲尔德步枪,但与平原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的枪法也很差劲。他们知道那个年轻的白人能熟练使用夏普斯步枪,可以在各种射程内射击。他们开始往上爬行,这使得他们的速度慢了下来。六人中的一人殿后,引领着六匹矮种马。
克雷格把一条毯子割成四片,分别包住罗斯巴德的四只蹄子。夹在铁掌和岩石之间的这些布料很快就会磨破,但能隐藏五百码距离的蹄印。然后他策马朝西南方向去,越过高原向山峰挺进。
过了银径后再走五英里,周围变得光秃秃的。两英里之后,这位边防战士扭头看身后,有一些微小的人影越过山脊到了石梁上。他继续策马前进。他们射不中他,也抓不住他。过了一会儿,人影更多了;骑兵们已经引着马匹穿过树林,也到了那块岩石上,而夏延人在他们东面一英里处。此时,克雷格来到了一个裂口处。他以前没有到过这么高的山上,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裂隙。
这道裂口里有一条又陡又窄的山溪,叫莱克福克溪,两岸长着松树,溪水冰冷刺骨。克雷格沿着溪边行走,想找一处较浅的堤岸跨过去。他在雷山的影子下发现了合适的地方,但这花去了他半个小时的时间。
他引领马匹下到深谷,又上了对面的坡顶,到了另一块也是最后一块岩石上,那是赫尔罗林高原。当他从溪谷中走出来时,一颗子弹从他头顶呼啸而过。在山谷对面,一个骑兵发现了松林里的动静。他这一耽搁,不但使追捕队赶了上来,而且还暴露了他穿越山溪的路径。